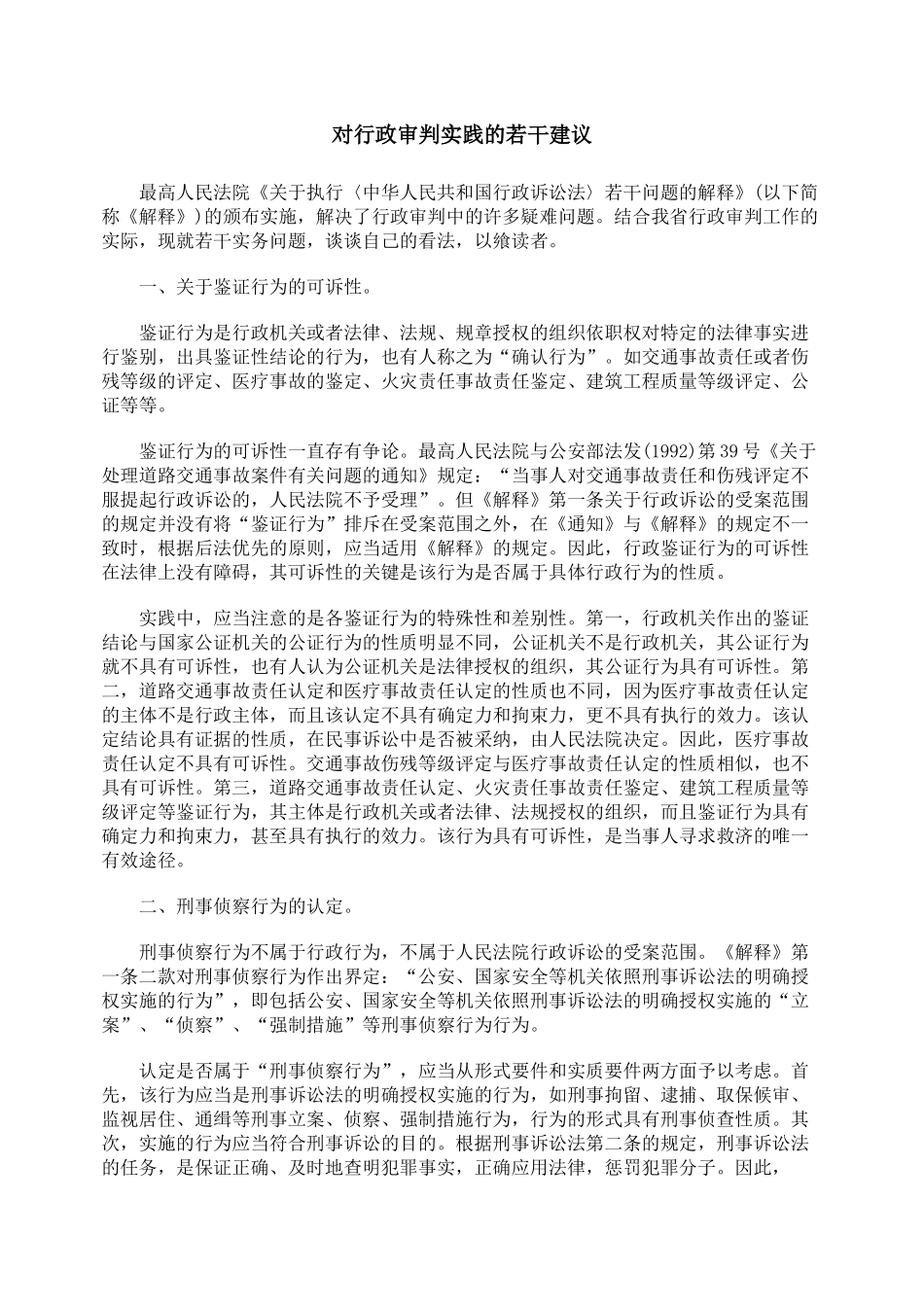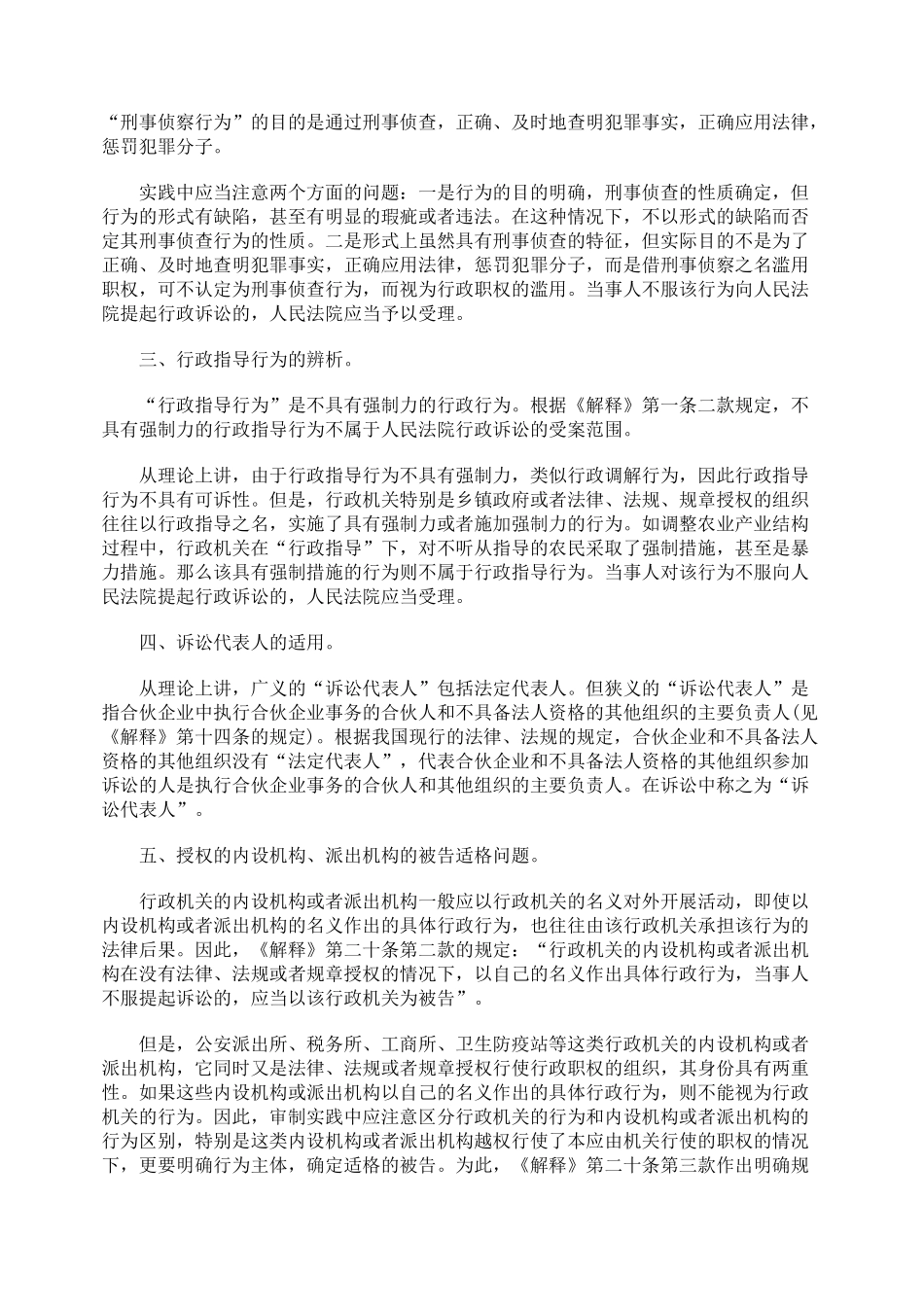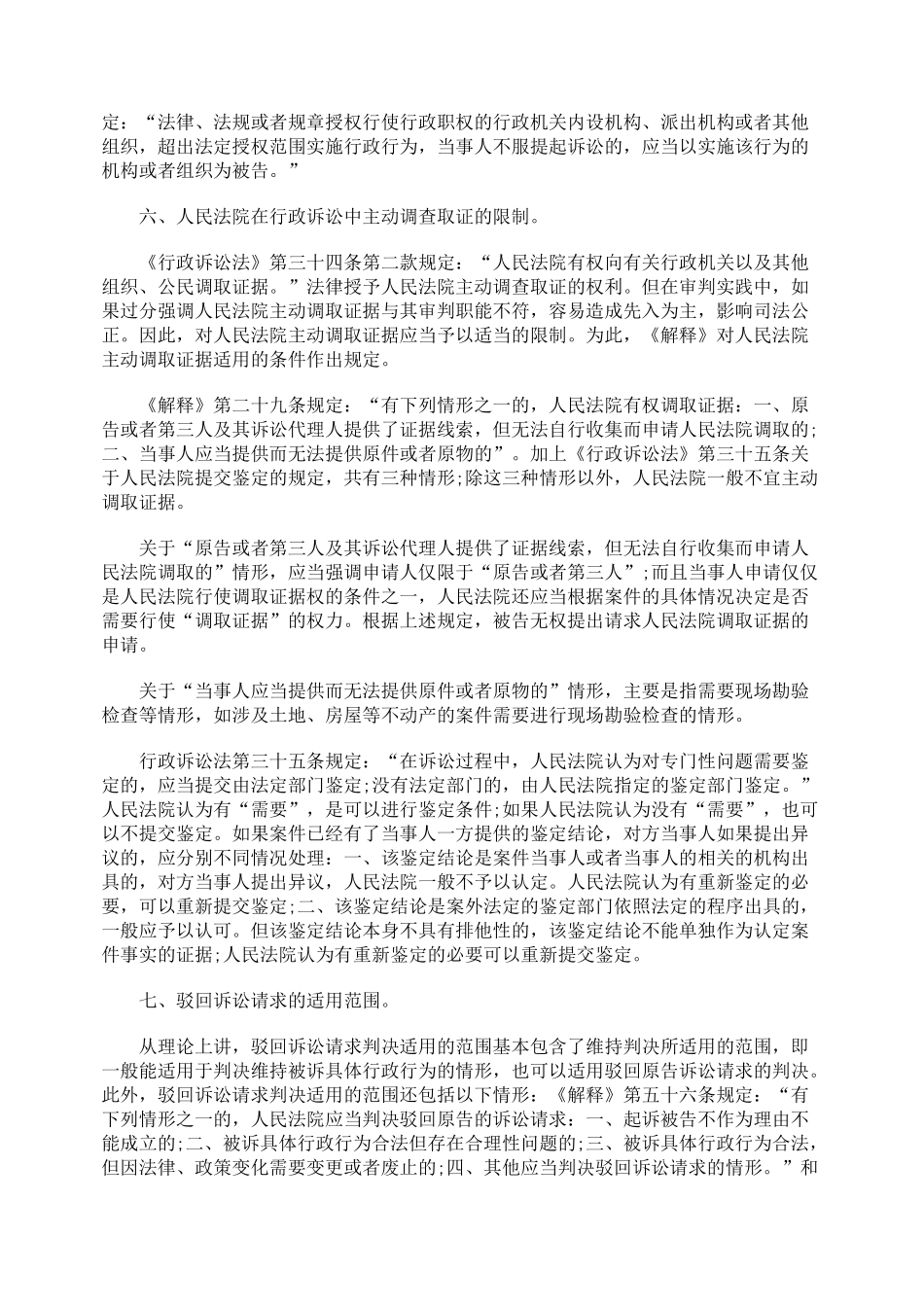对行政审判实践的若干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颁布实施,解决了行政审判中的许多疑难问题。结合我省行政审判工作的实际,现就若干实务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飨读者。一、关于鉴证行为的可诉性。鉴证行为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依职权对特定的法律事实进行鉴别,出具鉴证性结论的行为,也有人称之为“确认行为”。如交通事故责任或者伤残等级的评定、医疗事故的鉴定、火灾责任事故责任鉴定、建筑工程质量等级评定、公证等等。鉴证行为的可诉性一直存有争论。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法发(1992)第39号《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和伤残评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解释》第一条关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并没有将“鉴证行为”排斥在受案范围之外,在《通知》与《解释》的规定不一致时,根据后法优先的原则,应当适用《解释》的规定。因此,行政鉴证行为的可诉性在法律上没有障碍,其可诉性的关键是该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各鉴证行为的特殊性和差别性。第一,行政机关作出的鉴证结论与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行为的性质明显不同,公证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其公证行为就不具有可诉性,也有人认为公证机关是法律授权的组织,其公证行为具有可诉性。第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也不同,因为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主体不是行政主体,而且该认定不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更不具有执行的效力。该认定结论具有证据的性质,在民事诉讼中是否被采纳,由人民法院决定。因此,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可诉性。交通事故伤残等级评定与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相似,也不具有可诉性。第三,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火灾责任事故责任鉴定、建筑工程质量等级评定等鉴证行为,其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且鉴证行为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甚至具有执行的效力。该行为具有可诉性,是当事人寻求救济的唯一有效途径。二、刑事侦察行为的认定。刑事侦察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解释》第一条二款对刑事侦察行为作出界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即包括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立案”、“侦察”、“强制措施”等刑事侦察行为行为。认定是否属于“刑事侦察行为”,应当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予以考虑。首先,该行为应当是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如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通缉等刑事立案、侦察、强制措施行为,行为的形式具有刑事侦查性质。其次,实施的行为应当符合刑事诉讼的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正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因此,“刑事侦察行为”的目的是通过刑事侦查,正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实践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行为的目的明确,刑事侦查的性质确定,但行为的形式有缺陷,甚至有明显的瑕疵或者违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以形式的缺陷而否定其刑事侦查行为的性质。二是形式上虽然具有刑事侦查的特征,但实际目的不是为了正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而是借刑事侦察之名滥用职权,可不认定为刑事侦查行为,而视为行政职权的滥用。当事人不服该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三、行政指导行为的辨析。“行政指导行为”是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根据《解释》第一条二款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理论上讲,由于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类似行政调解行为,因此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但是,行政机关特别是乡镇政府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往往以行政指导之名,实施了具有强制力或者施加强制力的行为。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过程中,行政机关在“行政指导”下,对不听从指导的农民采取了强制措施,甚至是暴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