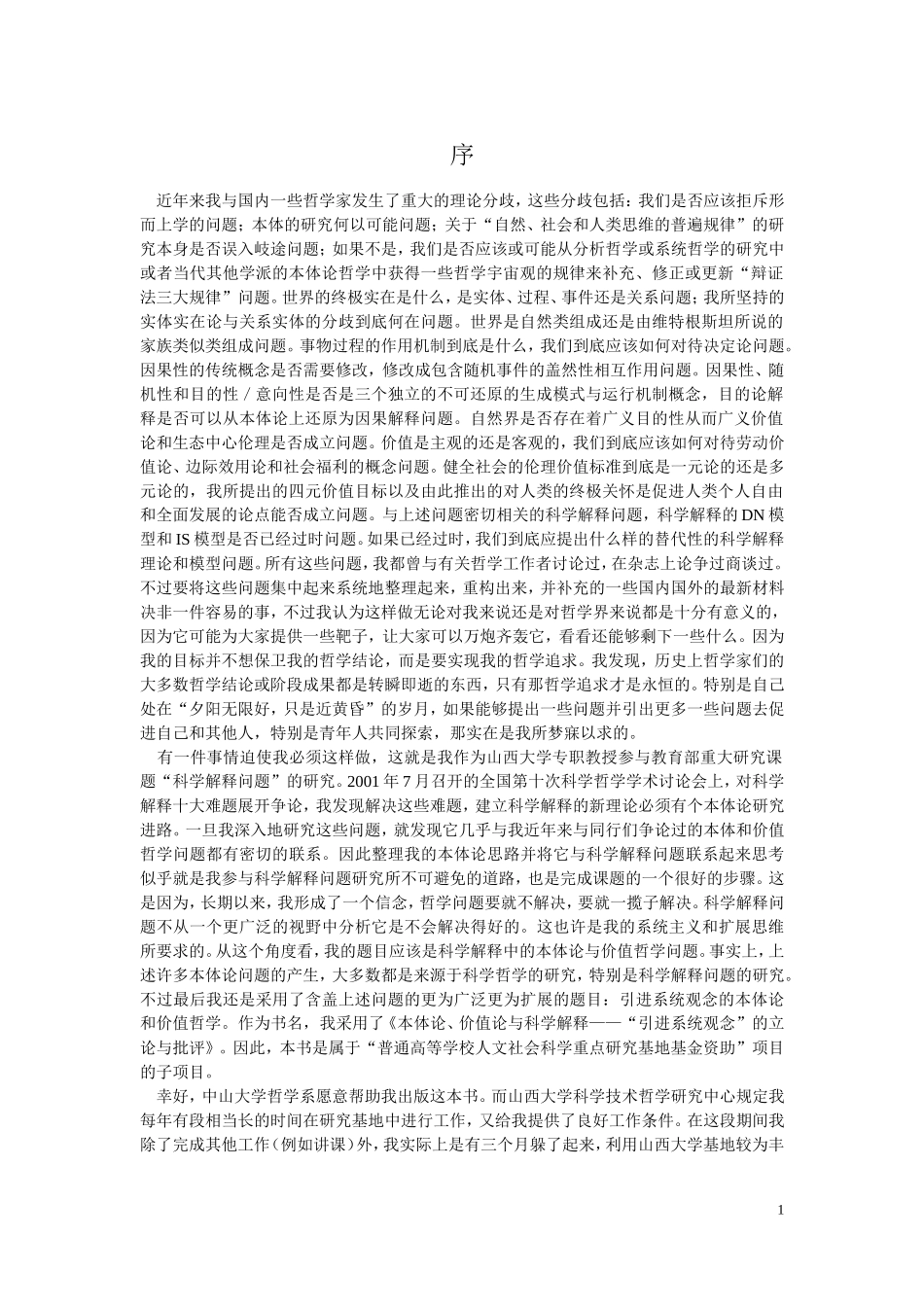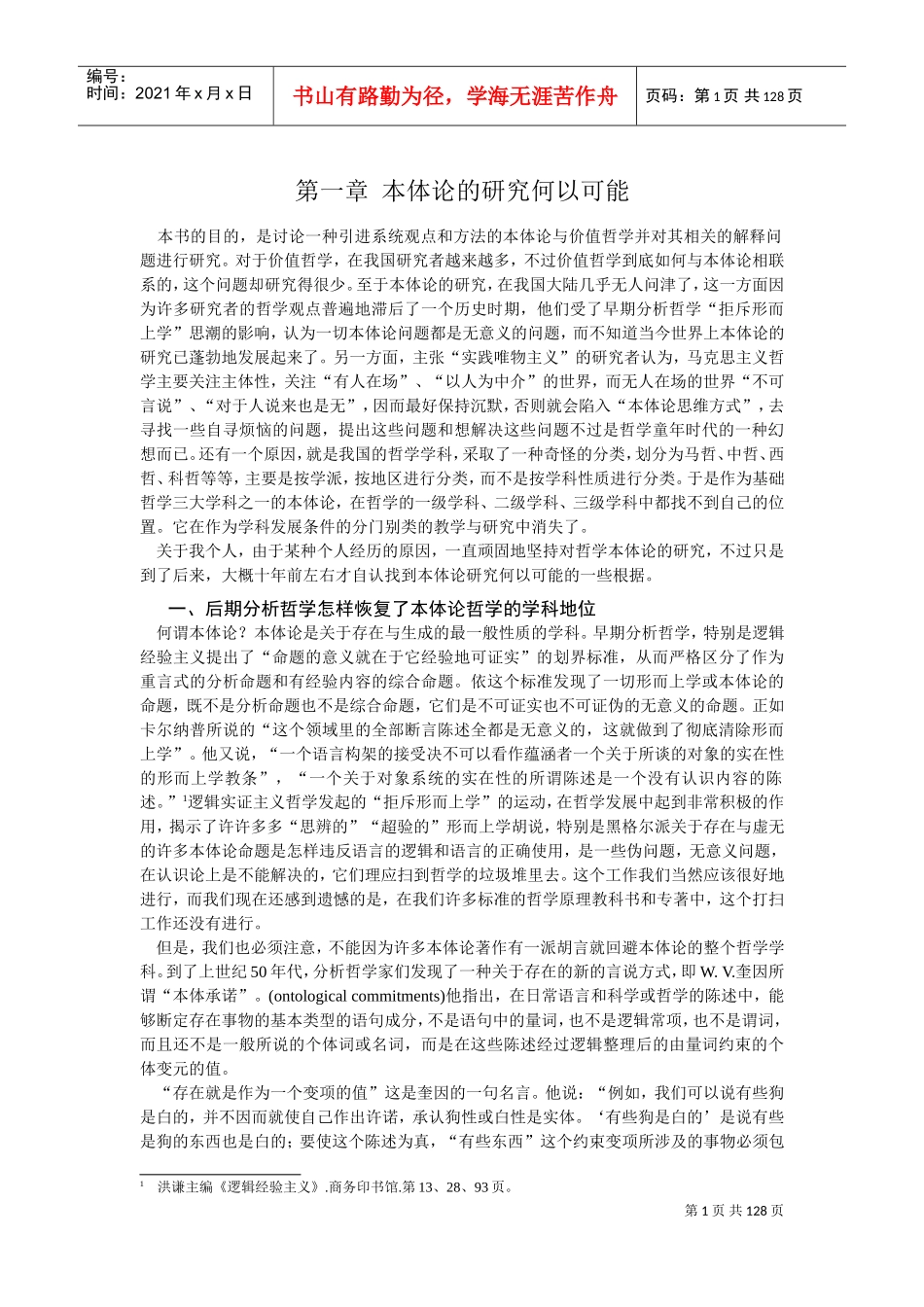序近年来我与国内一些哲学家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这些分歧包括:我们是否应该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本体的研究何以可能问题;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研究本身是否误入岐途问题;如果不是,我们是否应该或可能从分析哲学或系统哲学的研究中或者当代其他学派的本体论哲学中获得一些哲学宇宙观的规律来补充、修正或更新“辩证法三大规律”问题。世界的终极实在是什么,是实体、过程、事件还是关系问题;我所坚持的实体实在论与关系实体的分歧到底何在问题。世界是自然类组成还是由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类组成问题。事物过程的作用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决定论问题。因果性的传统概念是否需要修改,修改成包含随机事件的盖然性相互作用问题。因果性、随机性和目的性/意向性是否是三个独立的不可还原的生成模式与运行机制概念,目的论解释是否可以从本体论上还原为因果解释问题。自然界是否存在着广义目的性从而广义价值论和生态中心伦理是否成立问题。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论和社会福利的概念问题。健全社会的伦理价值标准到底是一元论的还是多元论的,我所提出的四元价值目标以及由此推出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促进人类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论点能否成立问题。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科学解释问题,科学解释的DN模型和IS模型是否已经过时问题。如果已经过时,我们到底应提出什么样的替代性的科学解释理论和模型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曾与有关哲学工作者讨论过,在杂志上论争过商谈过。不过要将这些问题集中起来系统地整理起来,重构出来,并补充的一些国内国外的最新材料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我认为这样做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哲学界来说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它可能为大家提供一些靶子,让大家可以万炮齐轰它,看看还能够剩下一些什么。因为我的目标并不想保卫我的哲学结论,而是要实现我的哲学追求。我发现,历史上哲学家们的大多数哲学结论或阶段成果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只有那哲学追求才是永恒的。特别是自己处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岁月,如果能够提出一些问题并引出更多一些问题去促进自己和其他人,特别是青年人共同探索,那实在是我所梦寐以求的。有一件事情迫使我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我作为山西大学专职教授参与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科学解释问题”的研究。2001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十次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上,对科学解释十大难题展开争论,我发现解决这些难题,建立科学解释的新理论必须有个本体论研究进路。一旦我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就发现它几乎与我近年来与同行们争论过的本体和价值哲学问题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整理我的本体论思路并将它与科学解释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似乎就是我参与科学解释问题研究所不可避免的道路,也是完成课题的一个很好的步骤。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形成了一个信念,哲学问题要就不解决,要就一揽子解决。科学解释问题不从一个更广泛的视野中分析它是不会解决得好的。这也许是我的系统主义和扩展思维所要求的。从这个角度看,我的题目应该是科学解释中的本体论与价值哲学问题。事实上,上述许多本体论问题的产生,大多数都是来源于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科学解释问题的研究。不过最后我还是采用了含盖上述问题的更为广泛更为扩展的题目:引进系统观念的本体论和价值哲学。作为书名,我采用了《本体论、价值论与科学解释——“引进系统观念”的立论与批评》。因此,本书是属于“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的子项目。幸好,中山大学哲学系愿意帮助我出版这本书。而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规定我每年有段相当长的时间在研究基地中进行工作,又给我提供了良好工作条件。在这段期间我除了完成其他工作(例如讲课)外,我实际上是有三个月躲了起来,利用山西大学基地较为丰1富的外文资料,毫不间断地每天工作10小时来完成这个研究与写作任务。当我完成了我的写作工作之时,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十分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以及黎红雷教授和李平教授对我完成这本书的帮助、支持和鼓励。十分感谢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