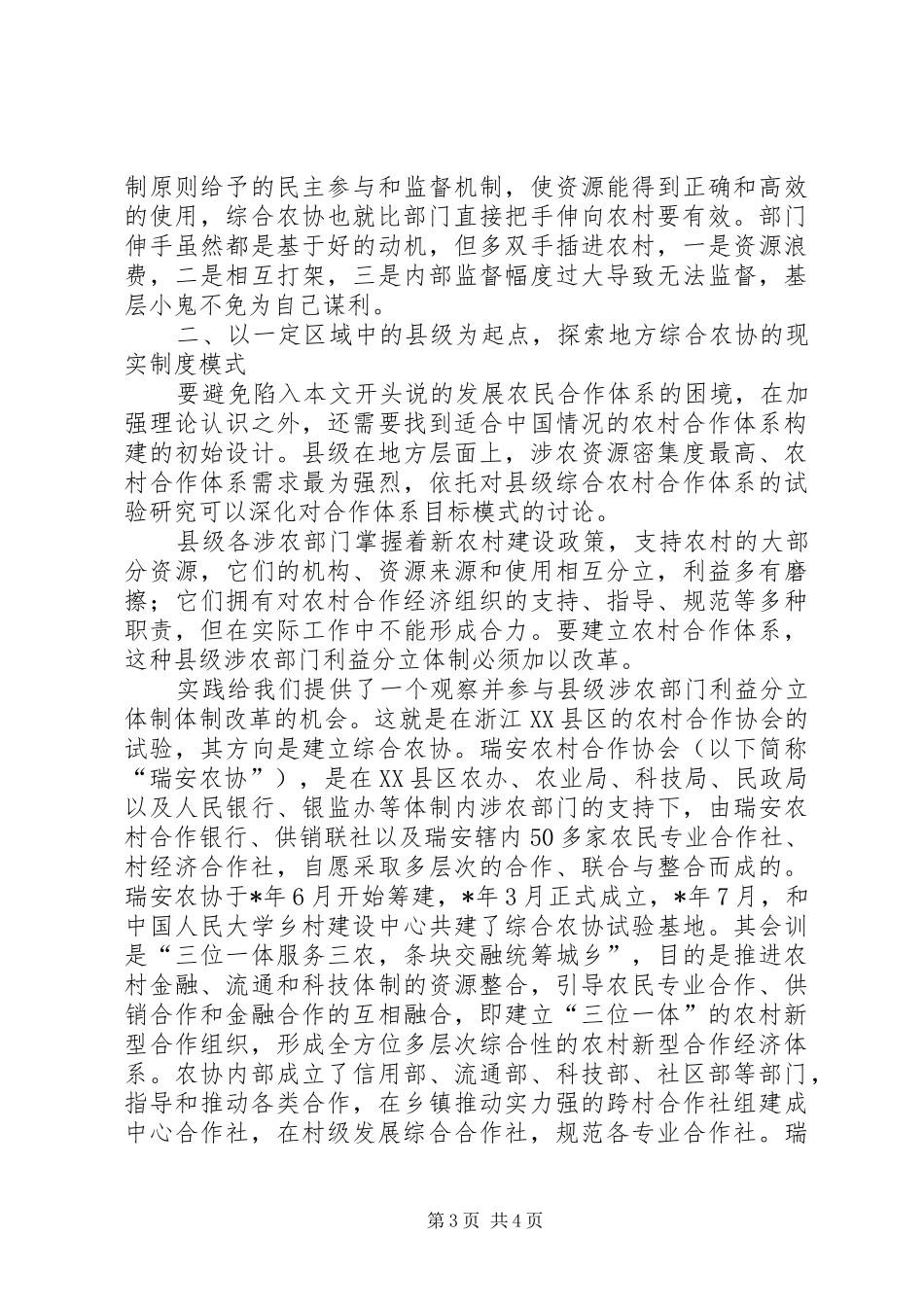农村合作体系构建的综合农协道路上世纪80年代推进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发展一直面临着深层次组织和制度创新任务,其中核心是构建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农村合作体系,以确保小农户在大市场中具有平等地位,分享涉农产业和涉农服务利润。但农村合作体系的组建和发展多年来一直处在目标不明、零敲碎打的困境。对农村合作体系的目标模式,目前理论仍然停留在粗浅了解国外模式上的简单化争论,针对我们自身的特殊的农民合作需求研究不够,对有关的制度创新实例的深度研究不够,对合作体系的具体制度设计的研究则更为缺乏。但就在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政策已经在大幅回应实践中的农民合作体系创建要求。《农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年7月正式推行;各涉农部门为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或扩张部门地位和利益,正在出台和实施大力发展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各级地方政府也在系统制定并开始实施促进合作体系发育的政策。这些政策努力由于不能共享对合作体系目标模式的共识,自觉明确合作体系的功能,其效果不可避免会打折扣。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各涉农部门的有关政策很多是基于争取资金和扩张利益的目标,因而片面强调其专业性,人为割裂合作体系应有的综合性,导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合理的合作体系建立的任务无法提出或实现。一句话,农村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在部门利益分立条件下可能陷于根本无法建立的困境。对让小农在农业生产以及之外的其他涉农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日、韩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已经有了综合农协的经验。这一经验是比较有效的:就是层层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并开放流通、金融、技术推广等领域给这些合作经济组织经营,并将这些领域专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他经济主体不得轻易进入,依照区域大小和专业化程度高低建立纵向体系,直至在全国有统一的农会或农民合作协会。国家对综合农协体系的创建和运作给与资金、人力、法律政策上的扶植。这时候,我们一方面必须从基本理论甚至是常识上确立对第1页共4页综合农协在中国必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必须找准综合农协在中国发展的现实路径。一、综合农协道路不可避免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兼业小农户在市场中的经济和社会福利需要综合农协。中国的农民多数是兼业小农,人多地少的生态和社会约束不会演化出大量的专业化生产的大农户。即使这次农业普查的结构也许会告诉我们,中国农户的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了,但不会改变多数农户生产剩余少、专业化生产水平低的基本情况。过亿的小农户依靠农作物的多品种兼业和半工半农兼业,其产品的商品化率必然低,专业化程度必然低,依靠从市场上获得生产收益的空间必然低。因此,中国小农需要在农业生产之外分享社会平均利润,如此,才能提高其收入水平。这种分享一个是通过针对农户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这方面农村的步伐比城市还要慢,不能期待靠它改变农户处境;另一方面就要靠让农户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领域获得较高收益。后一个方面才是解决农民收入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根本途径。其次,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支农政策需要综合农协作为载体和渠道。现在举国上下支持新农村建设,各部门纷纷出台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计划,其中不乏项目和资金支持。但是,通过行政体系和层层上达的办法并不能有效对接农村需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耗费大量行政成本,媒体广泛质疑的钱能否花在农民身上不是空穴来风。农民合作社法通过的历程,就典型反映了部门利益的现状。由于摆脱了部门立法模式,才使得这部法律最终在争吵中通过,但是,没有金融合作的规定,反映了农业部门力图掌控合作社,领导和指导部门的多元参与的规定,显示各方都想在培育发展合作社中分一杯羹。要进行新农村建设,就要解决支农体系内部互相挚肘、运行的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综合农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综合农协构建的农民合作体系,其基层组织贴近农村,利于反馈农民需求,而且集中使用整合了的资金资源,加上合作第2页共4页制原则给予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使资源能得到正确和高效的使用,综合农协也就比部门直接把手伸向农村要有效。部门伸手虽然都是基于好的动机,但多双手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