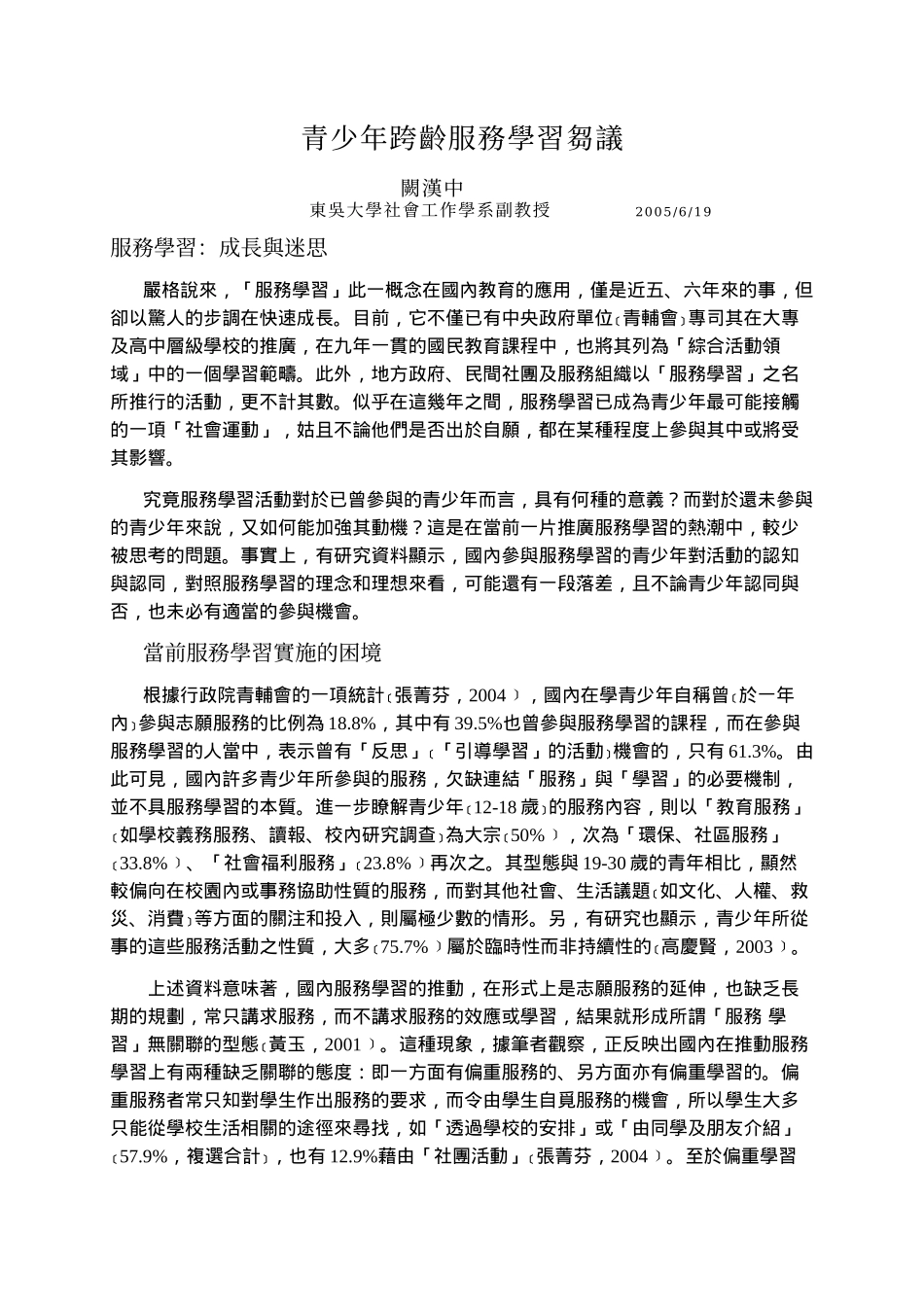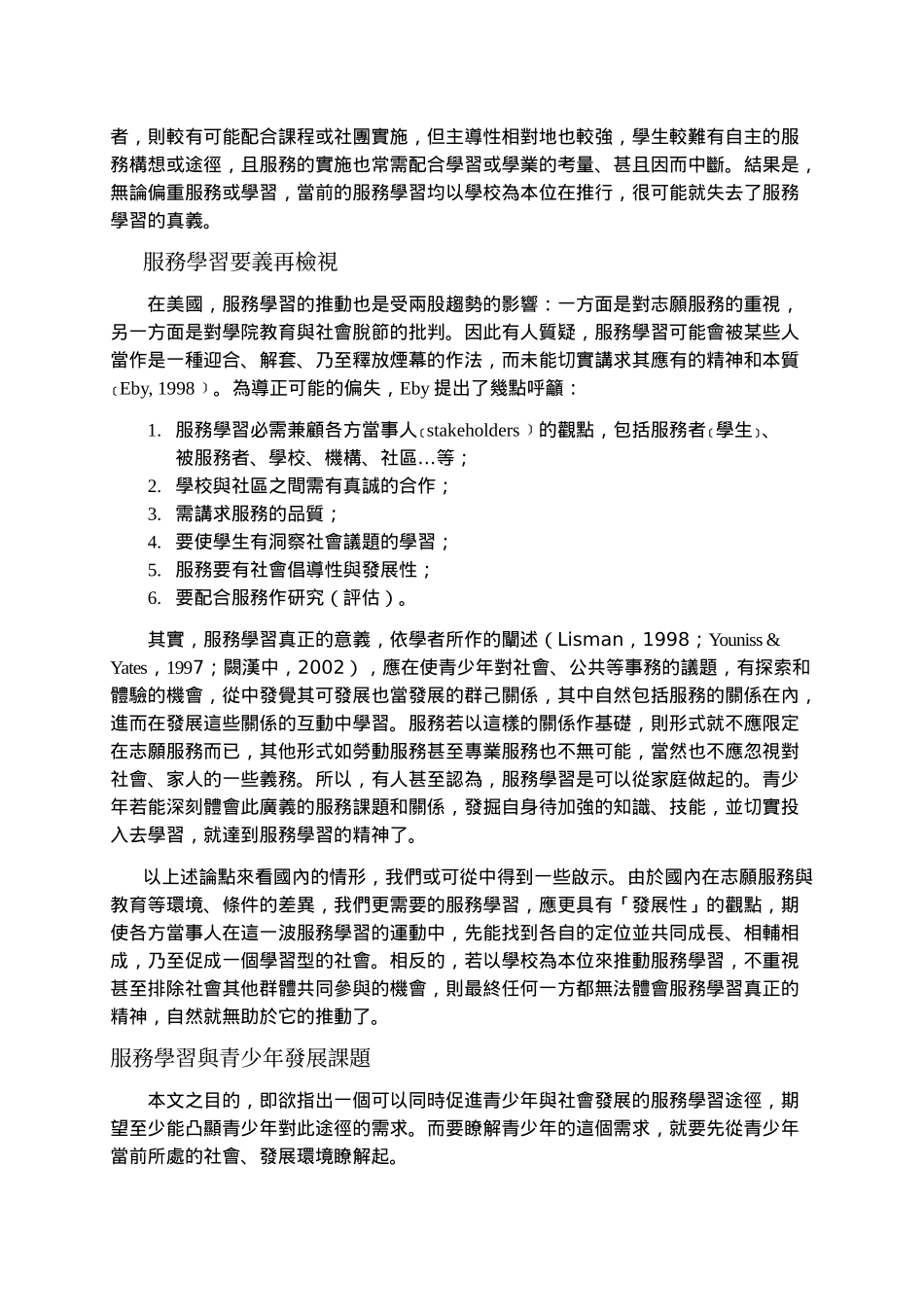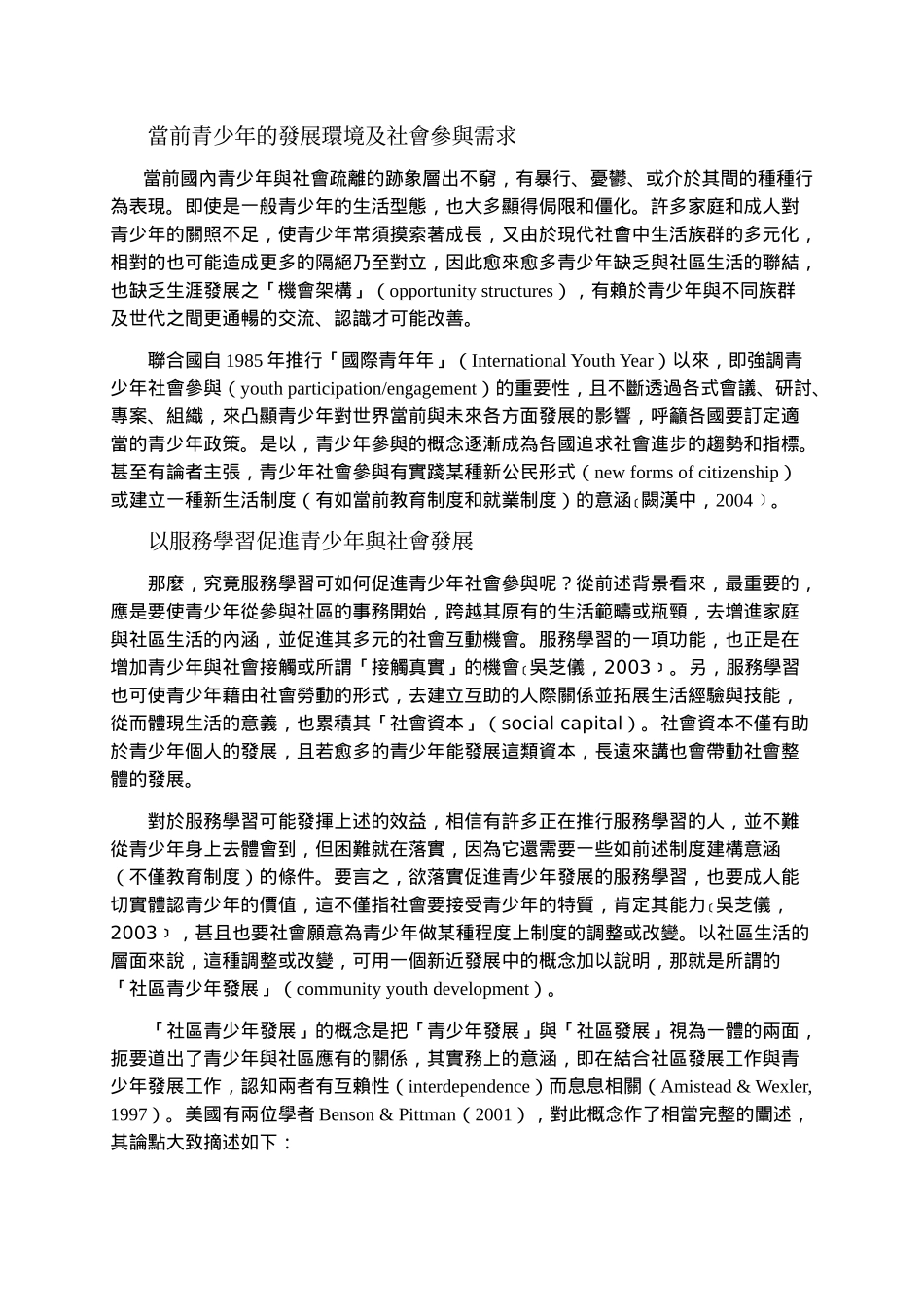青少年跨齡服務學習芻議闕漢中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2005/6/19服務學習:成長與迷思嚴格說來,「服務學習」此一概念在國內教育的應用,僅是近五、六年來的事,但卻以驚人的步調在快速成長。目前,它不僅已有中央政府單位﹝青輔會﹞專司其在大專及高中層級學校的推廣,在九年一貫的國民教育課程中,也將其列為「綜合活動領域」中的一個學習範疇。此外,地方政府、民間社團及服務組織以「服務學習」之名所推行的活動,更不計其數。似乎在這幾年之間,服務學習已成為青少年最可能接觸的一項「社會運動」,姑且不論他們是否出於自願,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其中或將受其影響。究竟服務學習活動對於已曾參與的青少年而言,具有何種的意義?而對於還未參與的青少年來說,又如何能加強其動機?這是在當前一片推廣服務學習的熱潮中,較少被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有研究資料顯示,國內參與服務學習的青少年對活動的認知與認同,對照服務學習的理念和理想來看,可能還有一段落差,且不論青少年認同與否,也未必有適當的參與機會。當前服務學習實施的困境根據行政院青輔會的一項統計﹝張菁芬,2004﹞,國內在學青少年自稱曾﹝於一年內﹞參與志願服務的比例為18.8%,其中有39.5%也曾參與服務學習的課程,而在參與服務學習的人當中,表示曾有「反思」﹝「引導學習」的活動﹞機會的,只有61.3%。由此可見,國內許多青少年所參與的服務,欠缺連結「服務」與「學習」的必要機制,並不具服務學習的本質。進一步瞭解青少年﹝12-18歲﹞的服務內容,則以「教育服務」﹝如學校義務服務、讀報、校內研究調查﹞為大宗﹝50%﹞,次為「環保、社區服務」﹝33.8%﹞、「社會福利服務」﹝23.8%﹞再次之。其型態與19-30歲的青年相比,顯然較偏向在校園內或事務協助性質的服務,而對其他社會、生活議題﹝如文化、人權、救災、消費﹞等方面的關注和投入,則屬極少數的情形。另,有研究也顯示,青少年所從事的這些服務活動之性質,大多﹝75.7%﹞屬於臨時性而非持續性的﹝高慶賢,2003﹞。上述資料意味著,國內服務學習的推動,在形式上是志願服務的延伸,也缺乏長期的規劃,常只講求服務,而不講求服務的效應或學習,結果就形成所謂「服務學習」無關聯的型態﹝黃玉,2001﹞。這種現象,據筆者觀察,正反映出國內在推動服務學習上有兩種缺乏關聯的態度:即一方面有偏重服務的、另方面亦有偏重學習的。偏重服務者常只知對學生作出服務的要求,而令由學生自覓服務的機會,所以學生大多只能從學校生活相關的途徑來尋找,如「透過學校的安排」或「由同學及朋友介紹」﹝57.9%,複選合計﹞,也有12.9%藉由「社團活動」﹝張菁芬,2004﹞。至於偏重學習者,則較有可能配合課程或社團實施,但主導性相對地也較強,學生較難有自主的服務構想或途徑,且服務的實施也常需配合學習或學業的考量、甚且因而中斷。結果是,無論偏重服務或學習,當前的服務學習均以學校為本位在推行,很可能就失去了服務學習的真義。服務學習要義再檢視在美國,服務學習的推動也是受兩股趨勢的影響:一方面是對志願服務的重視,另一方面是對學院教育與社會脫節的批判。因此有人質疑,服務學習可能會被某些人當作是一種迎合、解套、乃至釋放煙幕的作法,而未能切實講求其應有的精神和本質﹝Eby,1998﹞。為導正可能的偏失,Eby提出了幾點呼籲:1.服務學習必需兼顧各方當事人﹝stakeholders﹞的觀點,包括服務者﹝學生﹞、…被服務者、學校、機構、社區等;2.學校與社區之間需有真誠的合作;3.需講求服務的品質;4.要使學生有洞察社會議題的學習;5.服務要有社會倡導性與發展性;6.要配合服務作研究(評估)。其實,服務學習真正的意義,依學者所作的闡述(Lisman,1998;Youniss&Yates,1997;闕漢中,2002),應在使青少年對社會、公共等事務的議題,有探索和體驗的機會,從中發覺其可發展也當發展的群己關係,其中自然包括服務的關係在內,進而在發展這些關係的互動中學習。服務若以這樣的關係作基礎,則形式就不應限定在志願服務而已,其他形式如勞動服務甚至專業服務也不無可能,當然也不應忽視對社會、家人的一些義務。所以,有人甚至認為,服務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