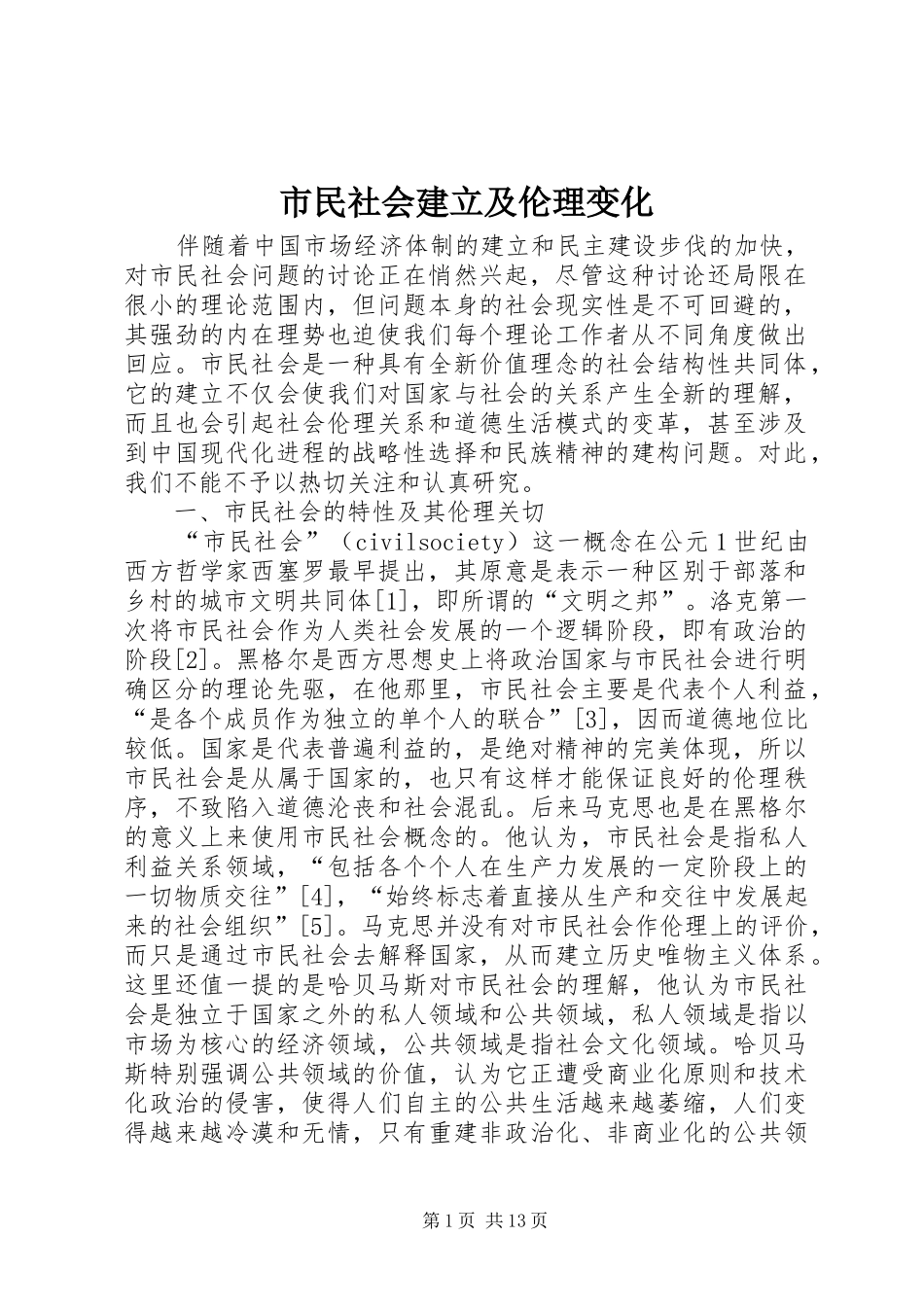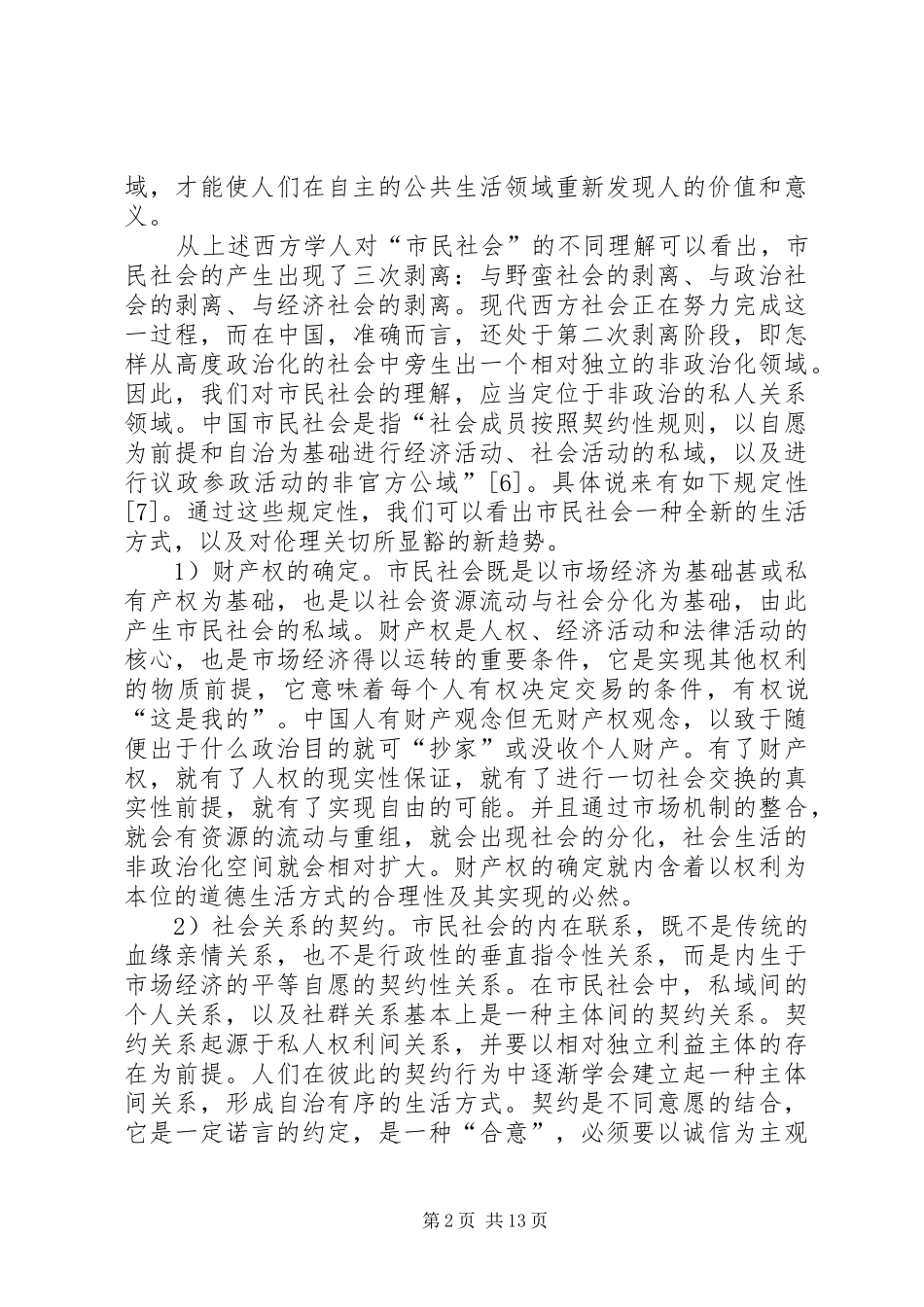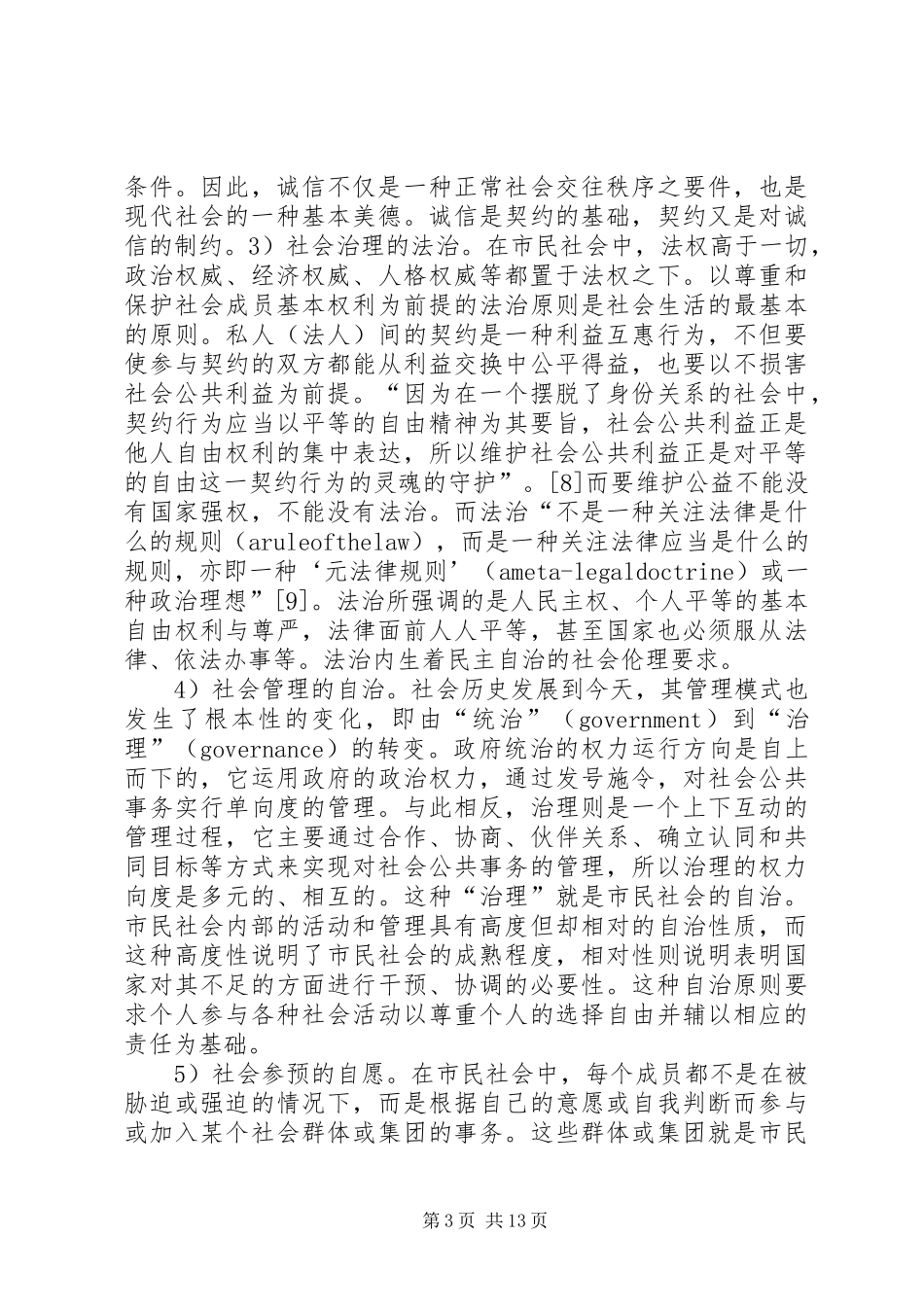市民社会建立及伦理变化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建设步伐的加快,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正在悄然兴起,尽管这种讨论还局限在很小的理论范围内,但问题本身的社会现实性是不可回避的,其强劲的内在理势也迫使我们每个理论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做出回应。市民社会是一种具有全新价值理念的社会结构性共同体,它的建立不仅会使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全新的理解,而且也会引起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模式的变革,甚至涉及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性选择和民族精神的建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热切关注和认真研究。一、市民社会的特性及其伦理关切“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一概念在公元1世纪由西方哲学家西塞罗最早提出,其原意是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1],即所谓的“文明之邦”。洛克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2]。黑格尔是西方思想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在他那里,市民社会主要是代表个人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3],因而道德地位比较低。国家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是绝对精神的完美体现,所以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良好的伦理秩序,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后来马克思也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来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他认为,市民社会是指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5]。马克思并没有对市民社会作伦理上的评价,而只是通过市民社会去解释国家,从而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里还值一提的是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是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是指社会文化领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化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和无情,只有重建非政治化、非商业化的公共领第1页共13页域,才能使人们在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和意义。从上述西方学人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产生出现了三次剥离:与野蛮社会的剥离、与政治社会的剥离、与经济社会的剥离。现代西方社会正在努力完成这一过程,而在中国,准确而言,还处于第二次剥离阶段,即怎样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旁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化领域。因此,我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当定位于非政治的私人关系领域。中国市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6]。具体说来有如下规定性[7]。通过这些规定性,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伦理关切所显豁的新趋势。1)财产权的确定。市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也是以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分化为基础,由此产生市民社会的私域。财产权是人权、经济活动和法律活动的核心,也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它意味着每个人有权决定交易的条件,有权说“这是我的”。中国人有财产观念但无财产权观念,以致于随便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就可“抄家”或没收个人财产。有了财产权,就有了人权的现实性保证,就有了进行一切社会交换的真实性前提,就有了实现自由的可能。并且通过市场机制的整合,就会有资源的流动与重组,就会出现社会的分化,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空间就会相对扩大。财产权的确定就内含着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必然。2)社会关系的契约。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既不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行政性的垂直指令性关系,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愿的契约性关系。在市民社会中,私域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社群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间的契约关系。契约关系起源于私人权利间关系,并要以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人们在彼此的契约行为中逐渐学会建立起一种主体间关系,形成自治有序的生活方式。契约是不同意愿的结合,它是一定诺言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