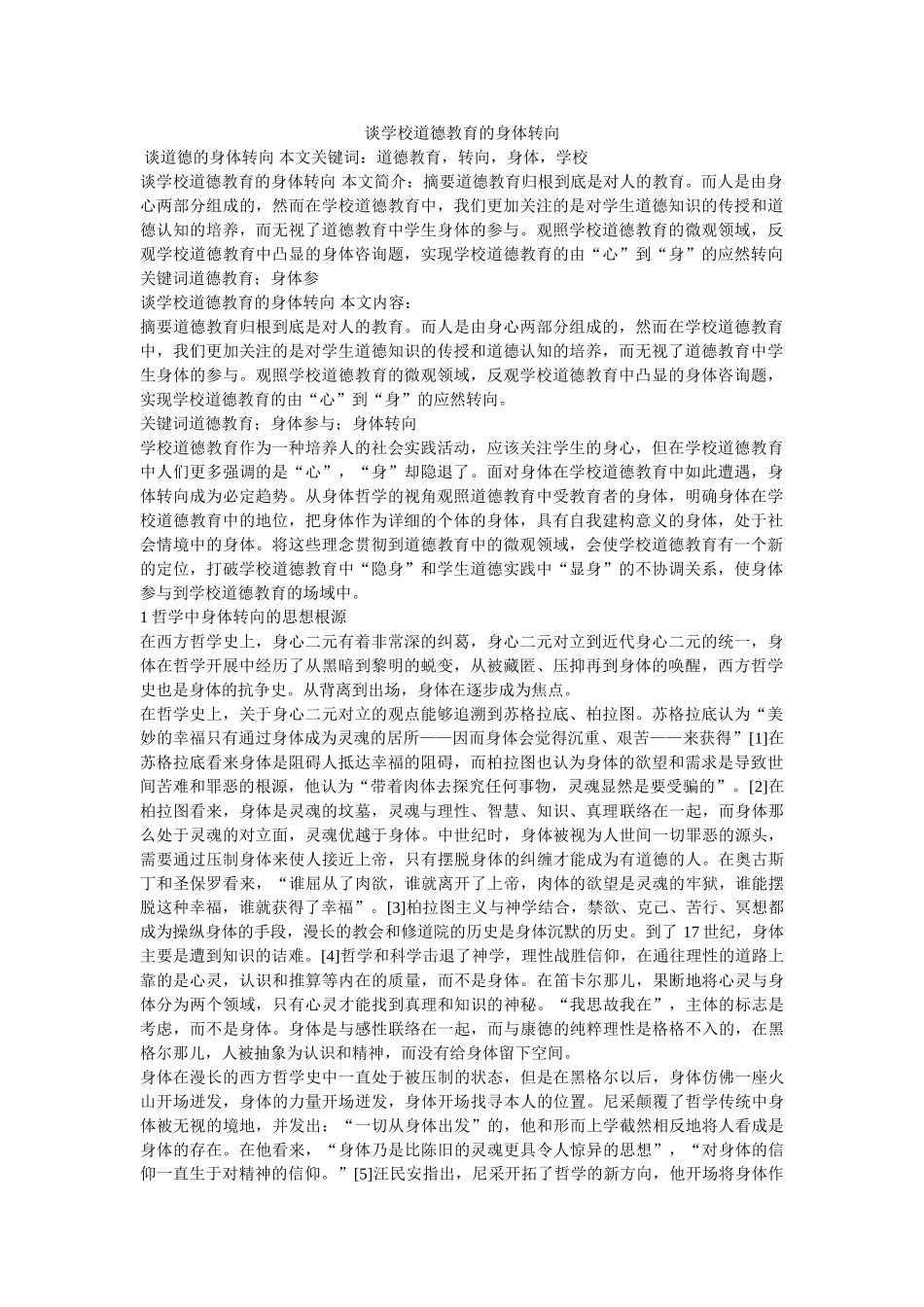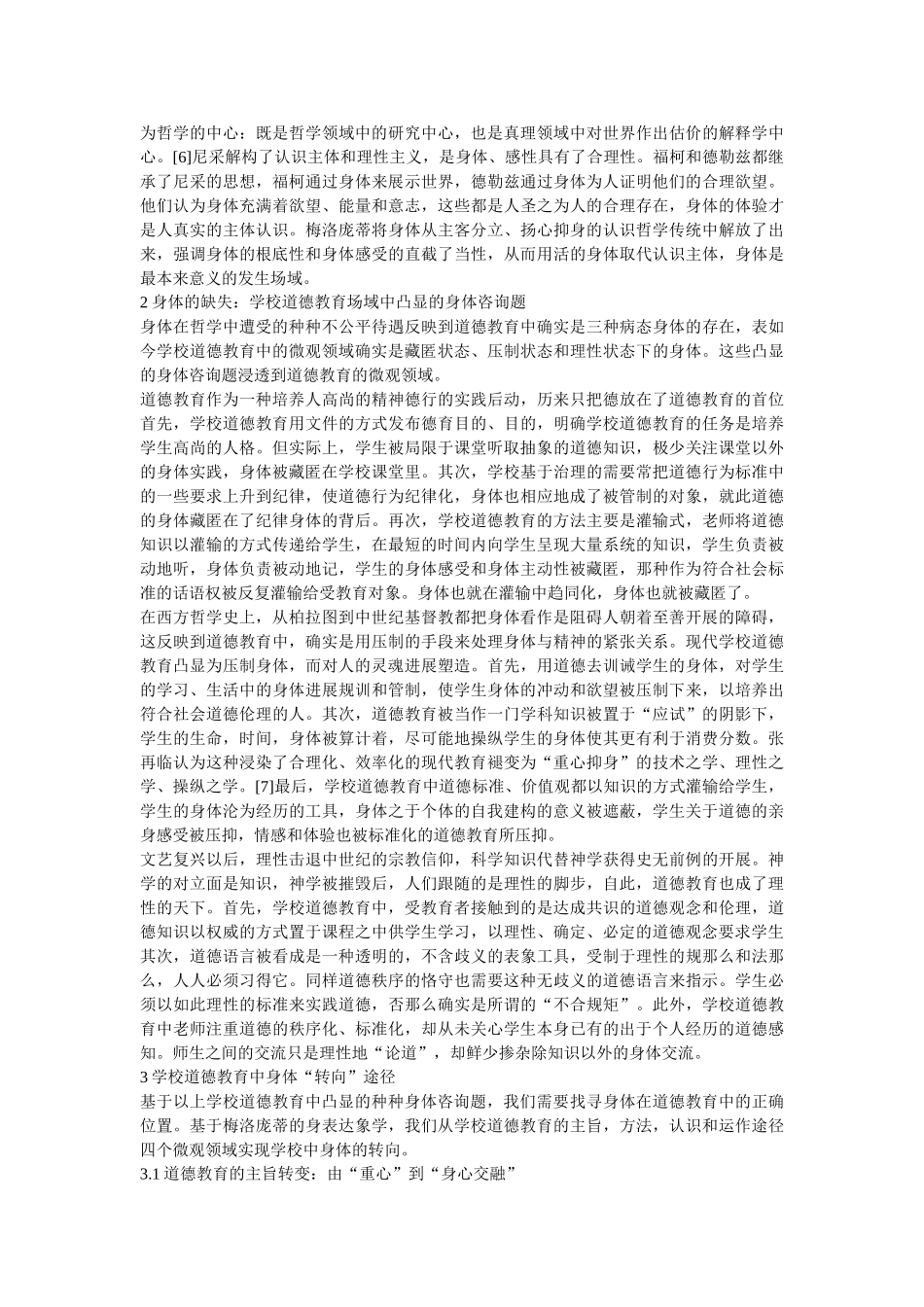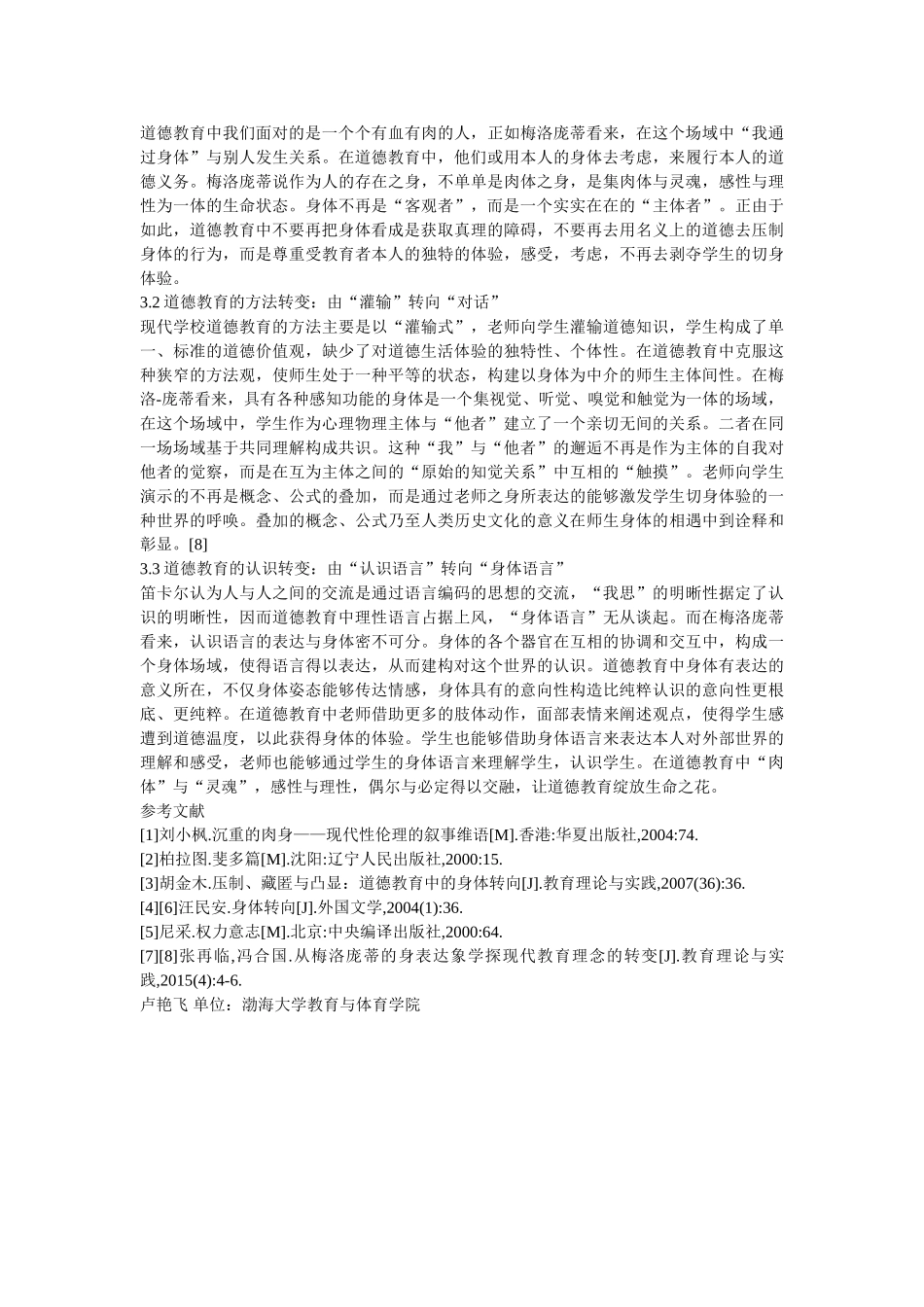谈学校道德教育的身体转向谈道德的身体转向本文关键词:道德教育,转向,身体,学校谈学校道德教育的身体转向本文简介:摘要道德教育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教育。而人是由身心两部分组成的,然而在学校道德教育中,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对学生道德知识的传授和道德认知的培养,而无视了道德教育中学生身体的参与。观照学校道德教育的微观领域,反观学校道德教育中凸显的身体咨询题,实现学校道德教育的由“心”到“身”的应然转向关键词道德教育;身体参谈学校道德教育的身体转向本文内容:摘要道德教育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教育。而人是由身心两部分组成的,然而在学校道德教育中,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对学生道德知识的传授和道德认知的培养,而无视了道德教育中学生身体的参与。观照学校道德教育的微观领域,反观学校道德教育中凸显的身体咨询题,实现学校道德教育的由“心”到“身”的应然转向。关键词道德教育;身体参与;身体转向学校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应该关注学生的身心,但在学校道德教育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心”,“身”却隐退了。面对身体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如此遭遇,身体转向成为必定趋势。从身体哲学的视角观照道德教育中受教育者的身体,明确身体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地位,把身体作为详细的个体的身体,具有自我建构意义的身体,处于社会情境中的身体。将这些理念贯彻到道德教育中的微观领域,会使学校道德教育有一个新的定位,打破学校道德教育中“隐身”和学生道德实践中“显身”的不协调关系,使身体参与到学校道德教育的场域中。1哲学中身体转向的思想根源在西方哲学史上,身心二元有着非常深的纠葛,身心二元对立到近代身心二元的统一,身体在哲学开展中经历了从黑暗到黎明的蜕变,从被藏匿、压抑再到身体的唤醒,西方哲学史也是身体的抗争史。从背离到出场,身体在逐步成为焦点。在哲学史上,关于身心二元对立的观点能够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苏格拉底认为“美妙的幸福只有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因而身体会觉得沉重、艰苦——来获得”[1]在苏格拉底看来身体是阻碍人抵达幸福的阻碍,而柏拉图也认为身体的欲望和需求是导致世间苦难和罪恶的根源,他认为“带着肉体去探究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受骗的”。[2]在柏拉图看来,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与理性、智慧、知识、真理联络在一起,而身体那么处于灵魂的对立面,灵魂优越于身体。中世纪时,身体被视为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源头,需要通过压制身体来使人接近上帝,只有摆脱身体的纠缠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在奥古斯丁和圣保罗看来,“谁屈从了肉欲,谁就离开了上帝,肉体的欲望是灵魂的牢狱,谁能摆脱这种幸福,谁就获得了幸福”。[3]柏拉图主义与神学结合,禁欲、克己、苦行、冥想都成为操纵身体的手段,漫长的教会和修道院的历史是身体沉默的历史。到了17世纪,身体主要是遭到知识的诘难。[4]哲学和科学击退了神学,理性战胜信仰,在通往理性的道路上靠的是心灵,认识和推算等内在的质量,而不是身体。在笛卡尔那儿,果断地将心灵与身体分为两个领域,只有心灵才能找到真理和知识的神秘。“我思故我在”,主体的标志是考虑,而不是身体。身体是与感性联络在一起,而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是格格不入的,在黑格尔那儿,人被抽象为认识和精神,而没有给身体留下空间。身体在漫长的西方哲学史中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在黑格尔以后,身体仿佛一座火山开场迸发,身体的力量开场迸发,身体开场找寻本人的位置。尼采颠覆了哲学传统中身体被无视的境地,并发出:“一切从身体出发”的,他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地将人看成是身体的存在。在他看来,“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具令人惊异的思想”,“对身体的信仰一直生于对精神的信仰。”[5]汪民安指出,尼采开拓了哲学的新方向,他开场将身体作为哲学的中心:既是哲学领域中的研究中心,也是真理领域中对世界作出估价的解释学中心。[6]尼采解构了认识主体和理性主义,是身体、感性具有了合理性。福柯和德勒兹都继承了尼采的思想,福柯通过身体来展示世界,德勒兹通过身体为人证明他们的合理欲望。他们认为身体充满着欲望、能量和意志,这些都是人圣之为人的合理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