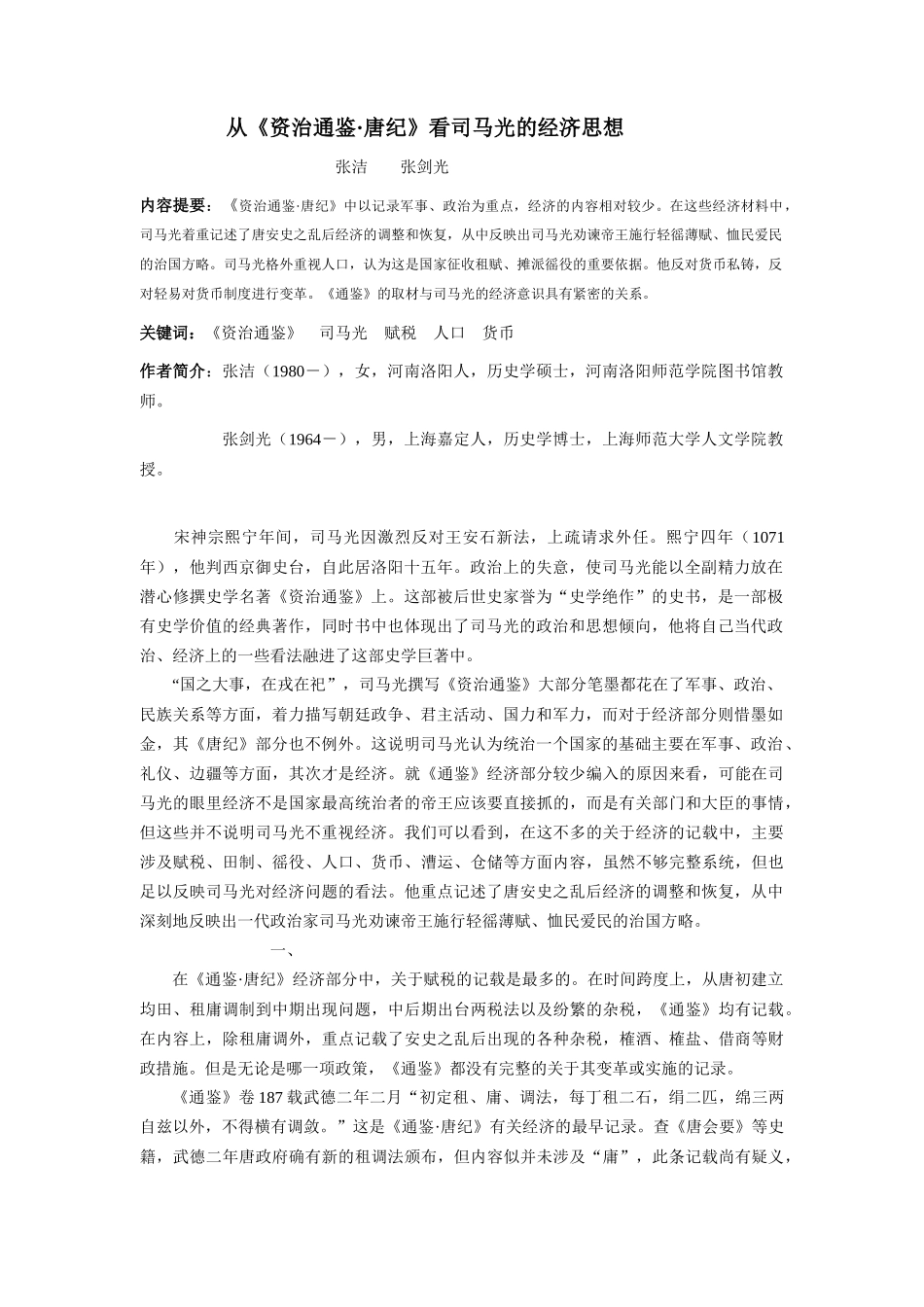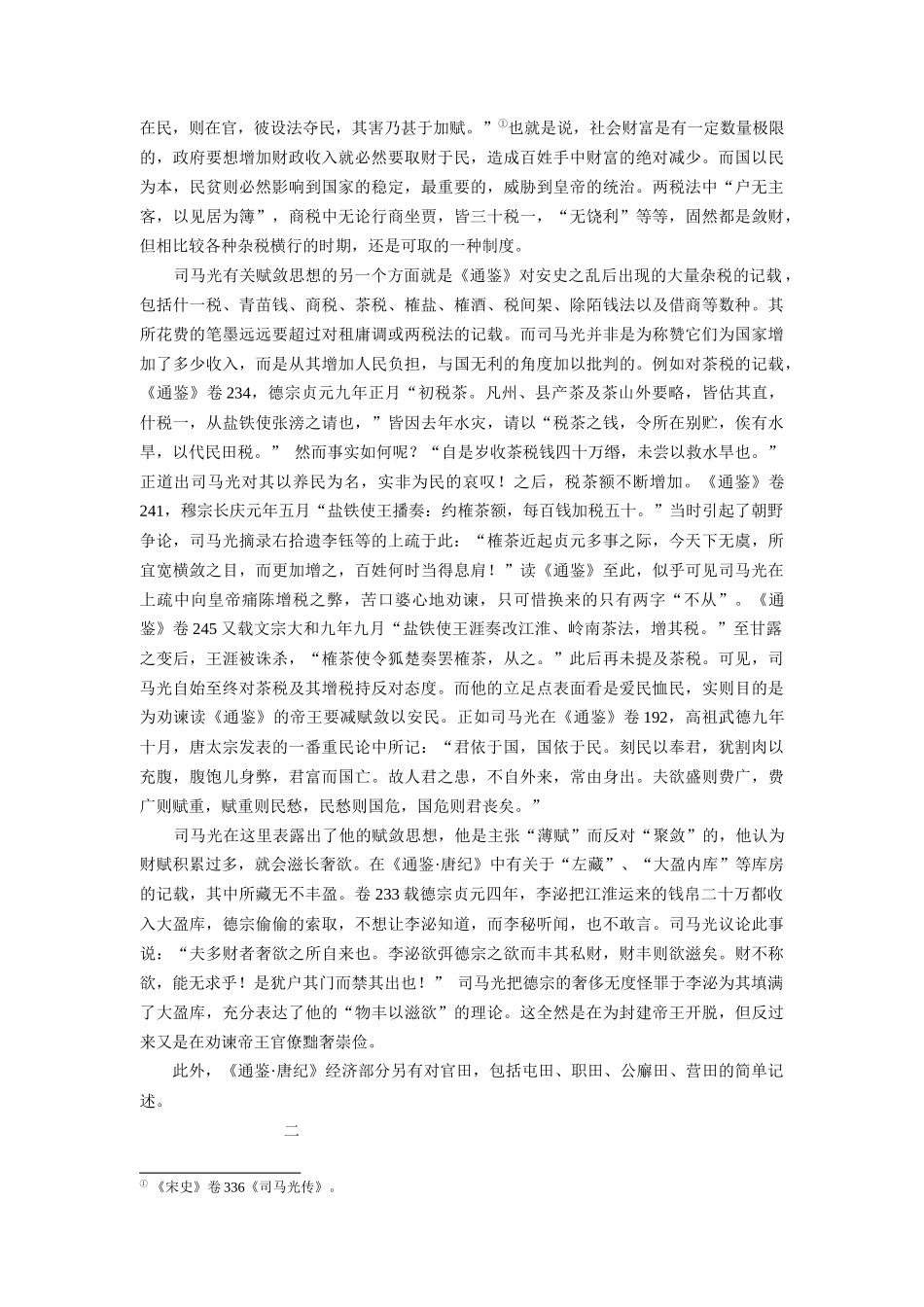从《资治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张洁张剑光内容提要:《资治通鉴·唐纪》中以记录军事、政治为重点,经济的内容相对较少。在这些经济材料中,司马光着重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反映出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司马光格外重视人口,认为这是国家征收租赋、摊派徭役的重要依据。他反对货币私铸,反对轻易对货币制度进行变革。《通鉴》的取材与司马光的经济意识具有紧密的关系。关键词:《资治通鉴》司马光赋税人口货币作者简介:张洁(1980-),女,河南洛阳人,历史学硕士,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教师。张剑光(1964-),男,上海嘉定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因激烈反对王安石新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政治上的失意,使司马光能以全副精力放在潜心修撰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上。这部被后世史家誉为“史学绝作”的史书,是一部极有史学价值的经典著作,同时书中也体现出了司马光的政治和思想倾向,他将自己当代政治、经济上的一些看法融进了这部史学巨著中。“国之大事,在戎在祀”,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大部分笔墨都花在了军事、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着力描写朝廷政争、君主活动、国力和军力,而对于经济部分则惜墨如金,其《唐纪》部分也不例外。这说明司马光认为统治一个国家的基础主要在军事、政治、礼仪、边疆等方面,其次才是经济。就《通鉴》经济部分较少编入的原因来看,可能在司马光的眼里经济不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应该要直接抓的,而是有关部门和大臣的事情,但这些并不说明司马光不重视经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不多的关于经济的记载中,主要涉及赋税、田制、徭役、人口、货币、漕运、仓储等方面内容,虽然不够完整系统,但也足以反映司马光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他重点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深刻地反映出一代政治家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一、在《通鉴·唐纪》经济部分中,关于赋税的记载是最多的。在时间跨度上,从唐初建立均田、租庸调制到中期出现问题,中后期出台两税法以及纷繁的杂税,《通鉴》均有记载。在内容上,除租庸调外,重点记载了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各种杂税,榷酒、榷盐、借商等财政措施。但是无论是哪一项政策,《通鉴》都没有完整的关于其变革或实施的记录。《通鉴》卷187载武德二年二月“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这是《通鉴·唐纪》有关经济的最早记录。查《唐会要》等史籍,武德二年唐政府确有新的租调法颁布,但内容似并未涉及“庸”,此条记载尚有疑义,我们也有不同看法①。继而《通鉴》卷190又载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此条有关租、庸、调,定民资产,造户籍等相关内容的记载较为详细,且与其它史籍所载稍有出入,大致内容是一致的。然而,据《通典》等典籍,唐政府曾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针对均田及租庸调制有进一步的规定出台,但这次重要调整却并未见于《通鉴》,在其下文中也只是有两处零散的资料涉及到租庸调。如《通鉴》卷213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诸州所输布帛有渍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征调始繁矣。”以及《通鉴》卷214载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令租庸调、租资课,皆以土物输京都。”对均田及租庸调制这一唐初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做如此简单的记载,正反映了司马光在整部《通鉴·唐纪》中对经济部分的处理原则:作为政治、军事之辅助角色而有所涉及,但只是描绘一下基本制度的建立,而对这一制度本身进展他并不想过多地描述。推测他的意图,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秩序是要建立妥当的,这样才能用刚纪来治理国家。唐初这两条关于均田租庸调制度创立的记载正说明了司马光也认识到在国家建立之初,百业待兴之即,经济制度建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通鉴》卷191关于武德八年九月统一度量衡的记载:“癸卯,初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亦可为佐证。但对基本制度建立后,还在想着要去完善这种制度,目的是为了这种征收更多的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