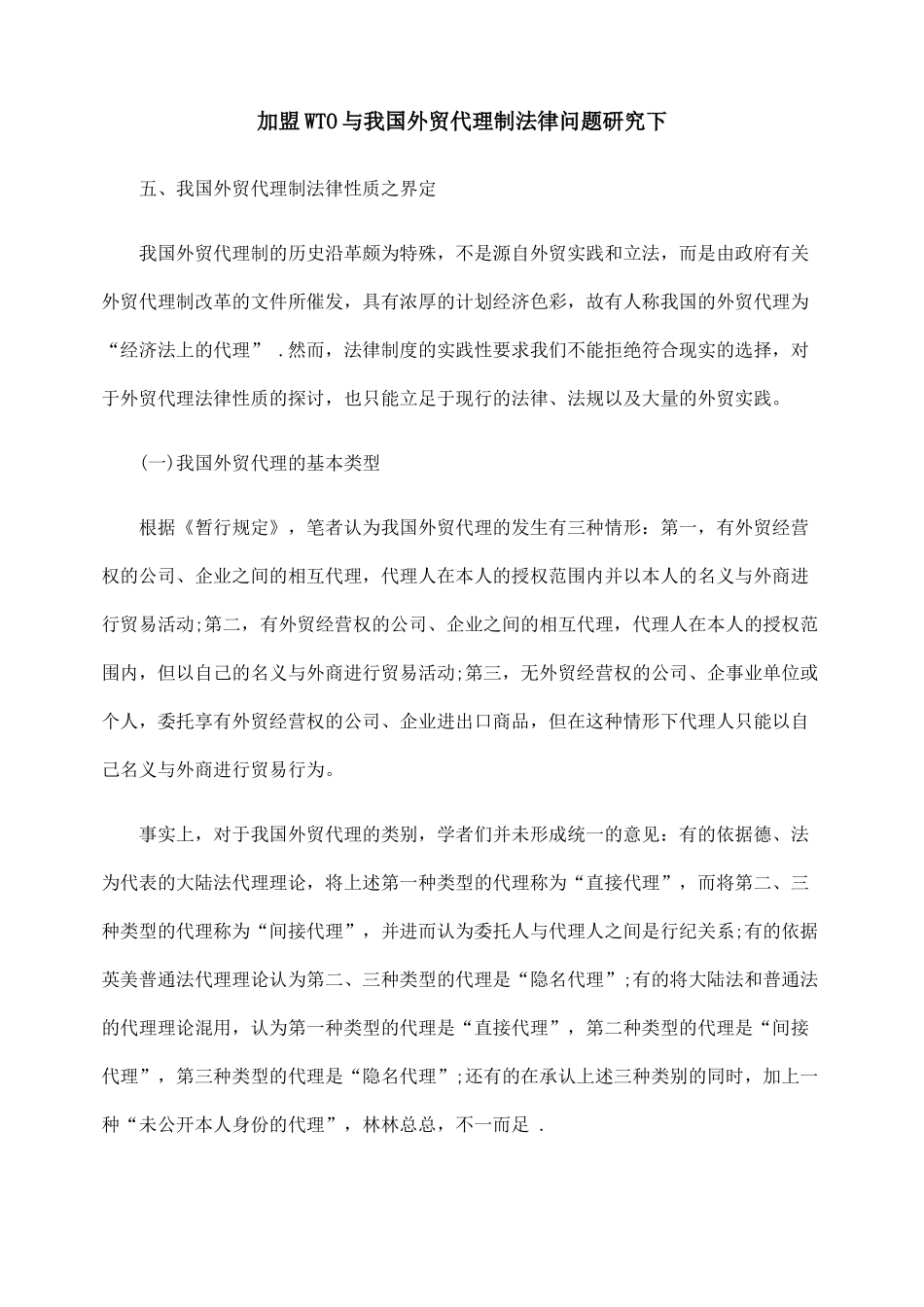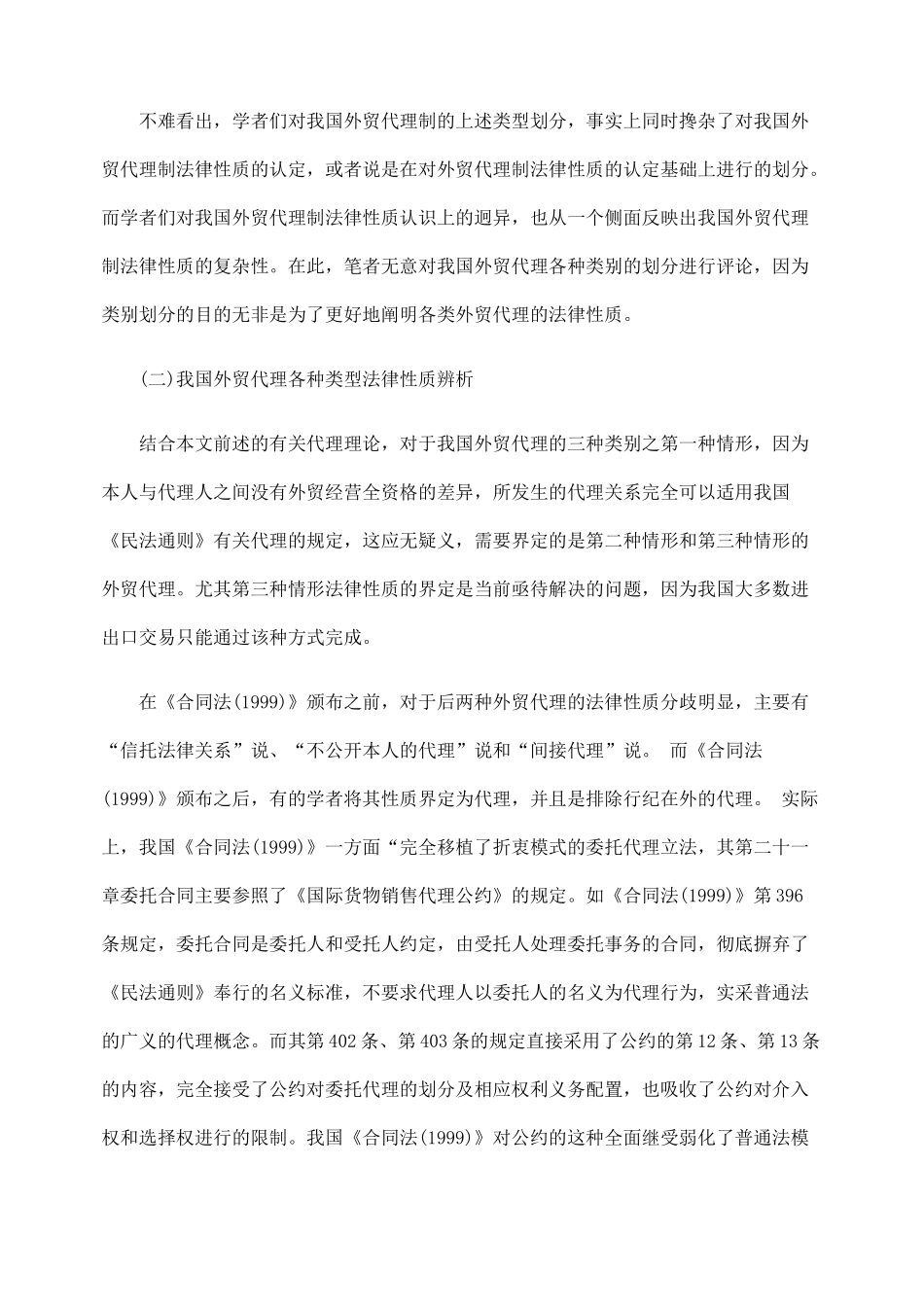加盟WTO与我国外贸代理制法律问题研究下五、我国外贸代理制法律性质之界定我国外贸代理制的历史沿革颇为特殊,不是源自外贸实践和立法,而是由政府有关外贸代理制改革的文件所催发,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故有人称我国的外贸代理为“经济法上的代理”.然而,法律制度的实践性要求我们不能拒绝符合现实的选择,对于外贸代理法律性质的探讨,也只能立足于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大量的外贸实践。(一)我国外贸代理的基本类型根据《暂行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外贸代理的发生有三种情形:第一,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之间的相互代理,代理人在本人的授权范围内并以本人的名义与外商进行贸易活动;第二,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之间的相互代理,代理人在本人的授权范围内,但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进行贸易活动;第三,无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委托享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进出口商品,但在这种情形下代理人只能以自己名义与外商进行贸易行为。事实上,对于我国外贸代理的类别,学者们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有的依据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代理理论,将上述第一种类型的代理称为“直接代理”,而将第二、三种类型的代理称为“间接代理”,并进而认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是行纪关系;有的依据英美普通法代理理论认为第二、三种类型的代理是“隐名代理”;有的将大陆法和普通法的代理理论混用,认为第一种类型的代理是“直接代理”,第二种类型的代理是“间接代理”,第三种类型的代理是“隐名代理”;还有的在承认上述三种类别的同时,加上一种“未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不难看出,学者们对我国外贸代理制的上述类型划分,事实上同时搀杂了对我国外贸代理制法律性质的认定,或者说是在对外贸代理制法律性质的认定基础上进行的划分。而学者们对我国外贸代理制法律性质认识上的迥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外贸代理制法律性质的复杂性。在此,笔者无意对我国外贸代理各种类别的划分进行评论,因为类别划分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阐明各类外贸代理的法律性质。(二)我国外贸代理各种类型法律性质辨析结合本文前述的有关代理理论,对于我国外贸代理的三种类别之第一种情形,因为本人与代理人之间没有外贸经营全资格的差异,所发生的代理关系完全可以适用我国《民法通则》有关代理的规定,这应无疑义,需要界定的是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的外贸代理。尤其第三种情形法律性质的界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我国大多数进出口交易只能通过该种方式完成。在《合同法(1999)》颁布之前,对于后两种外贸代理的法律性质分歧明显,主要有“信托法律关系”说、“不公开本人的代理”说和“间接代理”说。而《合同法(1999)》颁布之后,有的学者将其性质界定为代理,并且是排除行纪在外的代理。实际上,我国《合同法(1999)》一方面“完全移植了折衷模式的委托代理立法,其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主要参照了《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的规定。如《合同法(1999)》第396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彻底摒弃了《民法通则》奉行的名义标准,不要求代理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为代理行为,实采普通法的广义的代理概念。而其第402条、第403条的规定直接采用了公约的第12条、第13条的内容,完全接受了公约对委托代理的划分及相应权利义务配置,也吸收了公约对介入权和选择权进行的限制。我国《合同法(1999)》对公约的这种全面继受弱化了普通法模式的委托代理制度,完全摧毁了一直沿用的大陆法的代理观念,建立了比较先进和完备的委托代理制度,有利于我国外贸代理的发展。另一方面仍严格遵循着大陆法系的基本架构,既规定有委托合同,又规定有行纪合同。鉴于《合同法(1999)》分别设专章规定了委托合同和行纪合同,那么对同一部法律内部的分别独立两章之间就不应当厚此薄彼,我们没有理由两只眼睛只盯住委托合同,而无视行纪合同的存在。对照大陆法、普通法以及国际公约的代理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外贸代理制既不同于大陆法的规定,又不同于普通法的规定,也与国际公约不一致。在我国既存在外贸的直接代理,又有间接代理(行纪)、隐名代理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