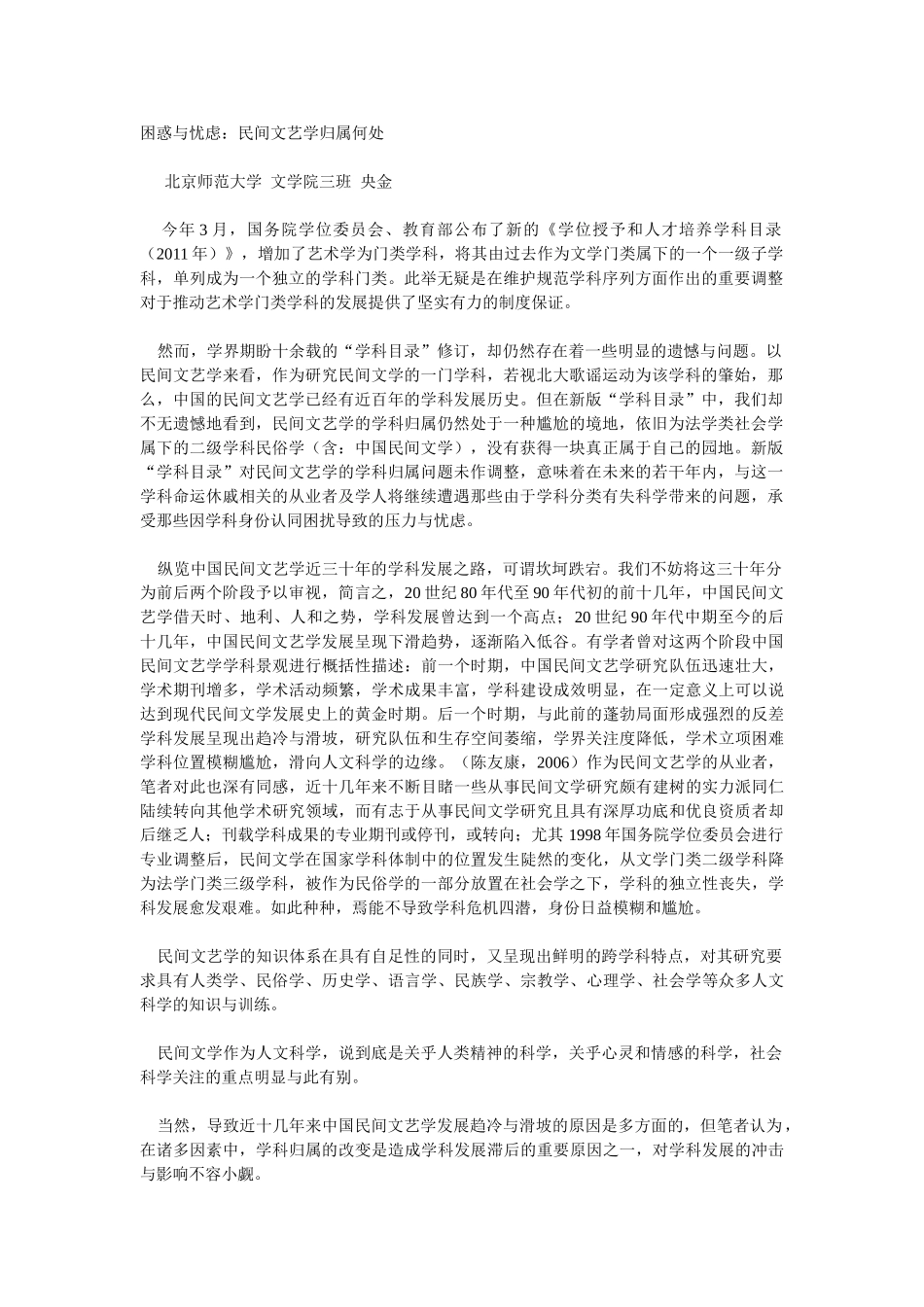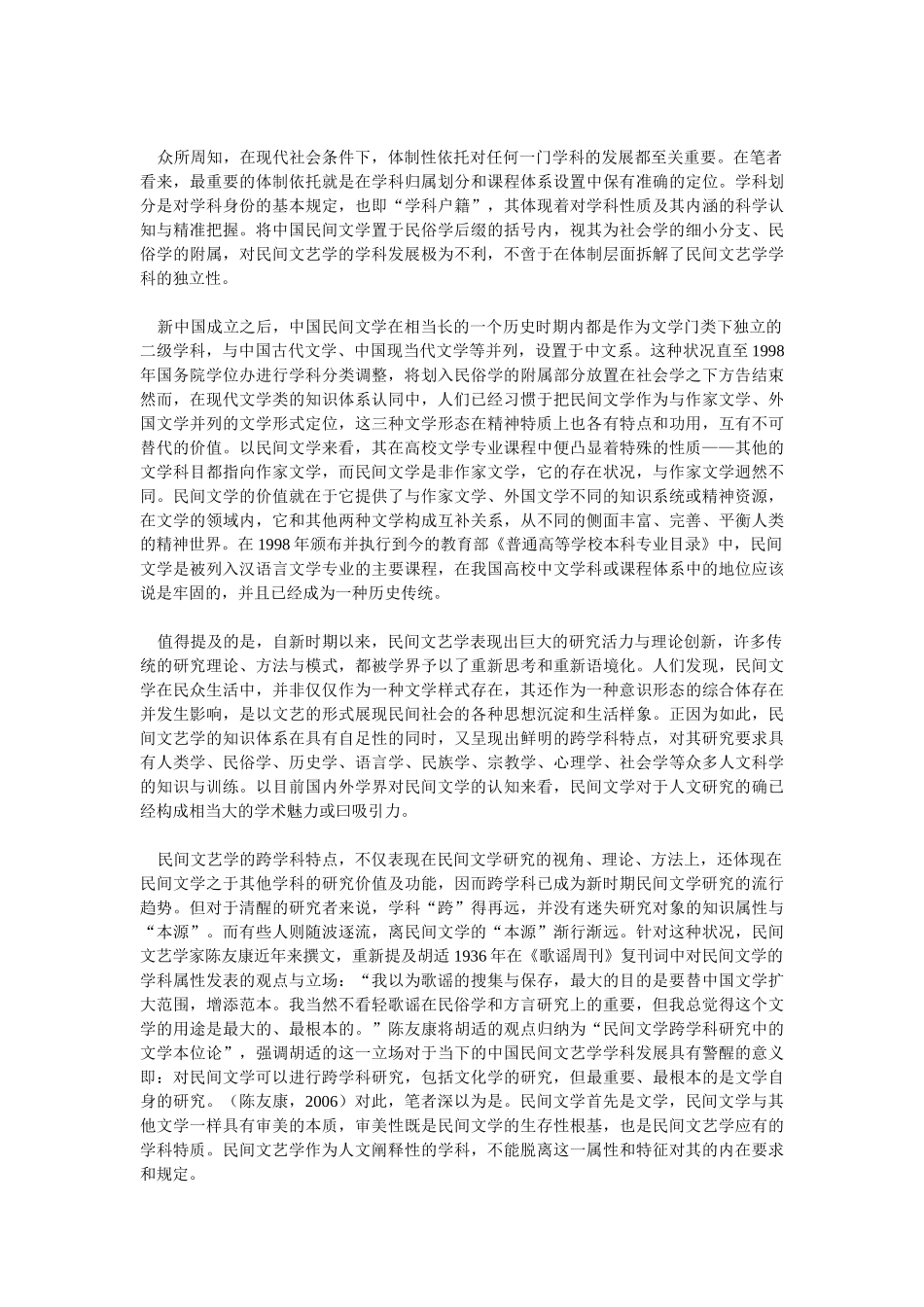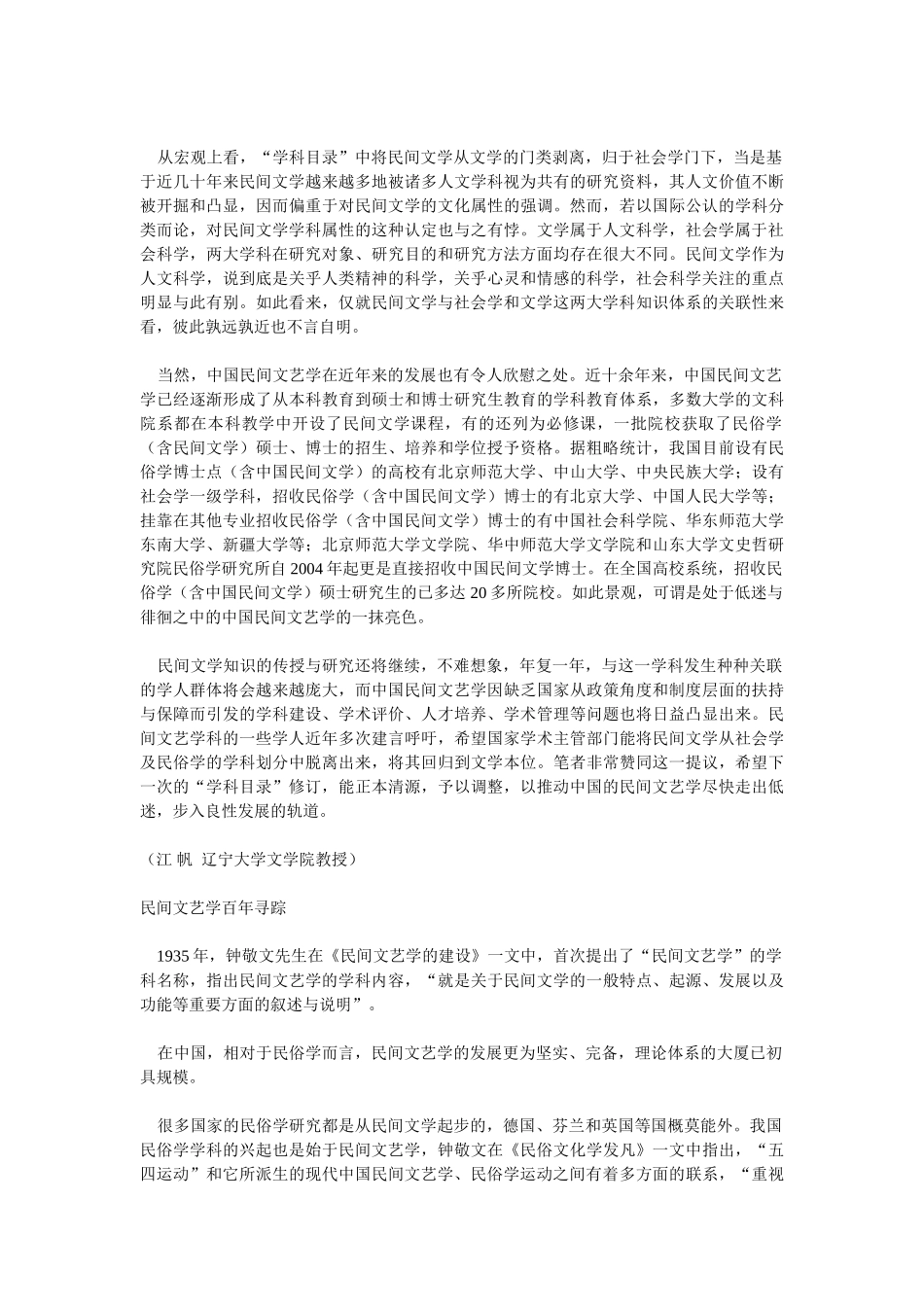困惑与忧虑:民间文艺学归属何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三班央金今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增加了艺术学为门类学科,将其由过去作为文学门类属下的一个一级子学科,单列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此举无疑是在维护规范学科序列方面作出的重要调整对于推动艺术学门类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保证。然而,学界期盼十余载的“学科目录”修订,却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遗憾与问题。以民间文艺学来看,作为研究民间文学的一门学科,若视北大歌谣运动为该学科的肇始,那么,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已经有近百年的学科发展历史。但在新版“学科目录”中,我们却不无遗憾地看到,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归属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依旧为法学类社会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没有获得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园地。新版“学科目录”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未作调整,意味着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与这一学科命运休戚相关的从业者及学人将继续遭遇那些由于学科分类有失科学带来的问题,承受那些因学科身份认同困扰导致的压力与忧虑。纵览中国民间文艺学近三十年的学科发展之路,可谓坎坷跌宕。我们不妨将这三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予以审视,简言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前十几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借天时、地利、人和之势,学科发展曾达到一个高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后十几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呈现下滑趋势,逐渐陷入低谷。有学者曾对这两个阶段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景观进行概括性描述:前一个时期,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学术期刊增多,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成果丰富,学科建设成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达到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后一个时期,与此前的蓬勃局面形成强烈的反差学科发展呈现出趋冷与滑坡,研究队伍和生存空间萎缩,学界关注度降低,学术立项困难学科位置模糊尴尬,滑向人文科学的边缘。(陈友康,2006)作为民间文艺学的从业者,笔者对此也深有同感,近十几年来不断目睹一些从事民间文学研究颇有建树的实力派同仁陆续转向其他学术研究领域,而有志于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且具有深厚功底和优良资质者却后继乏人;刊载学科成果的专业期刊或停刊,或转向;尤其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专业调整后,民间文学在国家学科体制中的位置发生陡然的变化,从文学门类二级学科降为法学门类三级学科,被作为民俗学的一部分放置在社会学之下,学科的独立性丧失,学科发展愈发艰难。如此种种,焉能不导致学科危机四潜,身份日益模糊和尴尬。民间文艺学的知识体系在具有自足性的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对其研究要求具有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人文科学的知识与训练。民间文学作为人文科学,说到底是关乎人类精神的科学,关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明显与此有别。当然,导致近十几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趋冷与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学科归属的改变是造成学科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学科发展的冲击与影响不容小觑。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体制性依托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体制依托就是在学科归属划分和课程体系设置中保有准确的定位。学科划分是对学科身份的基本规定,也即“学科户籍”,其体现着对学科性质及其内涵的科学认知与精准把握。将中国民间文学置于民俗学后缀的括号内,视其为社会学的细小分支、民俗学的附属,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发展极为不利,不啻于在体制层面拆解了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独立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间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是作为文学门类下独立的二级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设置于中文系。这种状况直至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进行学科分类调整,将划入民俗学的附属部分放置在社会学之下方告结束然而,在现代文学类的知识体系认同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民间文学作为与作家文学、外国文学并列的文学形式定位,这三种文学形态在精神特质上也各有特点和功用,互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