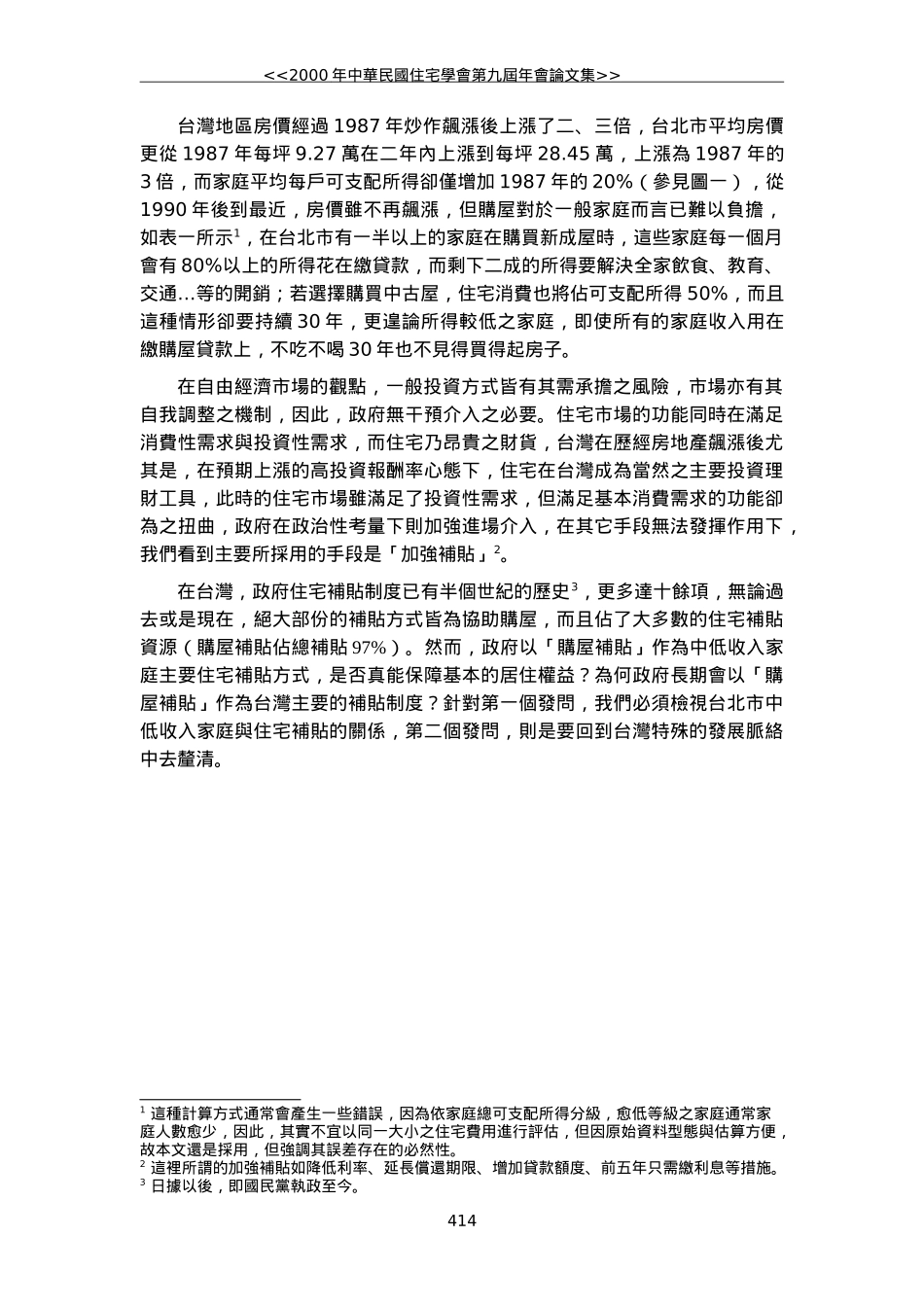<<2000年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場次:2A-4台灣住宅補貼制度與都市地區中低收入家庭之互動-以台北市為例石振弘*摘要社會福利的發展始於救貧,而「失業」是大部份福利國家在二十世紀初即認為是致貧與解決貧窮問題的癥結點,於是為了解決造成貧窮的「失業」問題,諸如「講求教育機會均等」與「以經濟政策作為社會政策的一環」等策略紛紛出籠,而這樣的思考模式在台灣亦然。我們不否認失業與貧窮間的關連,但是,若將貧窮問題放在台灣特殊的發展脈絡下,有一個「關鍵點」卻常常被忽略,就是「居住問題」,或更直接的說是「住宅消費負擔」,「住宅消費負擔」不見得是致貧的主因,但是在台灣尤其是都市地區,住宅消費卻可能導致中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頓,但是這樣的問題在台灣社會福利的討論上卻是沒被重視。台灣住宅問題是被歸在猶如工程單位的國宅局處負責,而國宅與社福單位的關連性是不高的。台灣住宅補貼制度的制訂與執行常常是泛政治化的,再加上長期「以量制價」的手段,以及「德政式」的低收入家庭照護,造成住宅補貼制度主要的照顧對象是中階層收入家庭而非中低收入家庭,而以「購屋補貼」的姿態出現,佔據了97%的資源。然而,預防中低收入家庭的抗爭,最有效的消音政策即是「容忍非正式部門的存在」。在台灣,不將住宅問題與貧窮問題連結是有問題的,而錯誤的方式可能比不解決還糟。正視住宅的結構性問題與中低收入家庭真正的需求才會幫助台灣邁向「生活機會公平分享的公民社會權」的第一步。關鍵字:住宅補貼、低收入家庭、購屋補貼、台北市壹、前言*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413<<2000年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台灣地區房價經過1987年炒作飆漲後上漲了二、三倍,台北市平均房價更從1987年每坪9.27萬在二年內上漲到每坪28.45萬,上漲為1987年的3倍,而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卻僅增加1987年的20%(參見圖一),從1990年後到最近,房價雖不再飆漲,但購屋對於一般家庭而言已難以負擔,如表一所示1,在台北市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在購買新成屋時,這些家庭每一個月會有80%以上的所得花在繳貸款,而剩下二成的所得要解決全家飲食、教育、…交通等的開銷;若選擇購買中古屋,住宅消費也將佔可支配所得50%,而且這種情形卻要持續30年,更遑論所得較低之家庭,即使所有的家庭收入用在繳購屋貸款上,不吃不喝30年也不見得買得起房子。在自由經濟市場的觀點,一般投資方式皆有其需承擔之風險,市場亦有其自我調整之機制,因此,政府無干預介入之必要。住宅市場的功能同時在滿足消費性需求與投資性需求,而住宅乃昂貴之財貨,台灣在歷經房地產飆漲後尤其是,在預期上漲的高投資報酬率心態下,住宅在台灣成為當然之主要投資理財工具,此時的住宅市場雖滿足了投資性需求,但滿足基本消費需求的功能卻為之扭曲,政府在政治性考量下則加強進場介入,在其它手段無法發揮作用下,我們看到主要所採用的手段是「加強補貼」2。在台灣,政府住宅補貼制度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3,更多達十餘項,無論過去或是現在,絕大部份的補貼方式皆為協助購屋,而且佔了大多數的住宅補貼資源(購屋補貼佔總補貼97%)。然而,政府以「購屋補貼」作為中低收入家庭主要住宅補貼方式,是否真能保障基本的居住權益?為何政府長期會以「購屋補貼」作為台灣主要的補貼制度?針對第一個發問,我們必須檢視台北市中低收入家庭與住宅補貼的關係,第二個發問,則是要回到台灣特殊的發展脈絡中去釐清。1這種計算方式通常會產生一些錯誤,因為依家庭總可支配所得分級,愈低等級之家庭通常家庭人數愈少,因此,其實不宜以同一大小之住宅費用進行評估,但因原始資料型態與估算方便,故本文還是採用,但強調其誤差存在的必然性。2這裡所謂的加強補貼如降低利率、延長償還期限、增加貸款額度、前五年只需繳利息等措施。3日據以後,即國民黨執政至今。414<<2000年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圖一台北市房價與可支配所得增長率註:以1981年為100%計算;原始資料來源:台北市家庭收支概況調查報告、信義房屋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1998)本研究整理表一台北市承購中古屋與預售屋貸款與所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