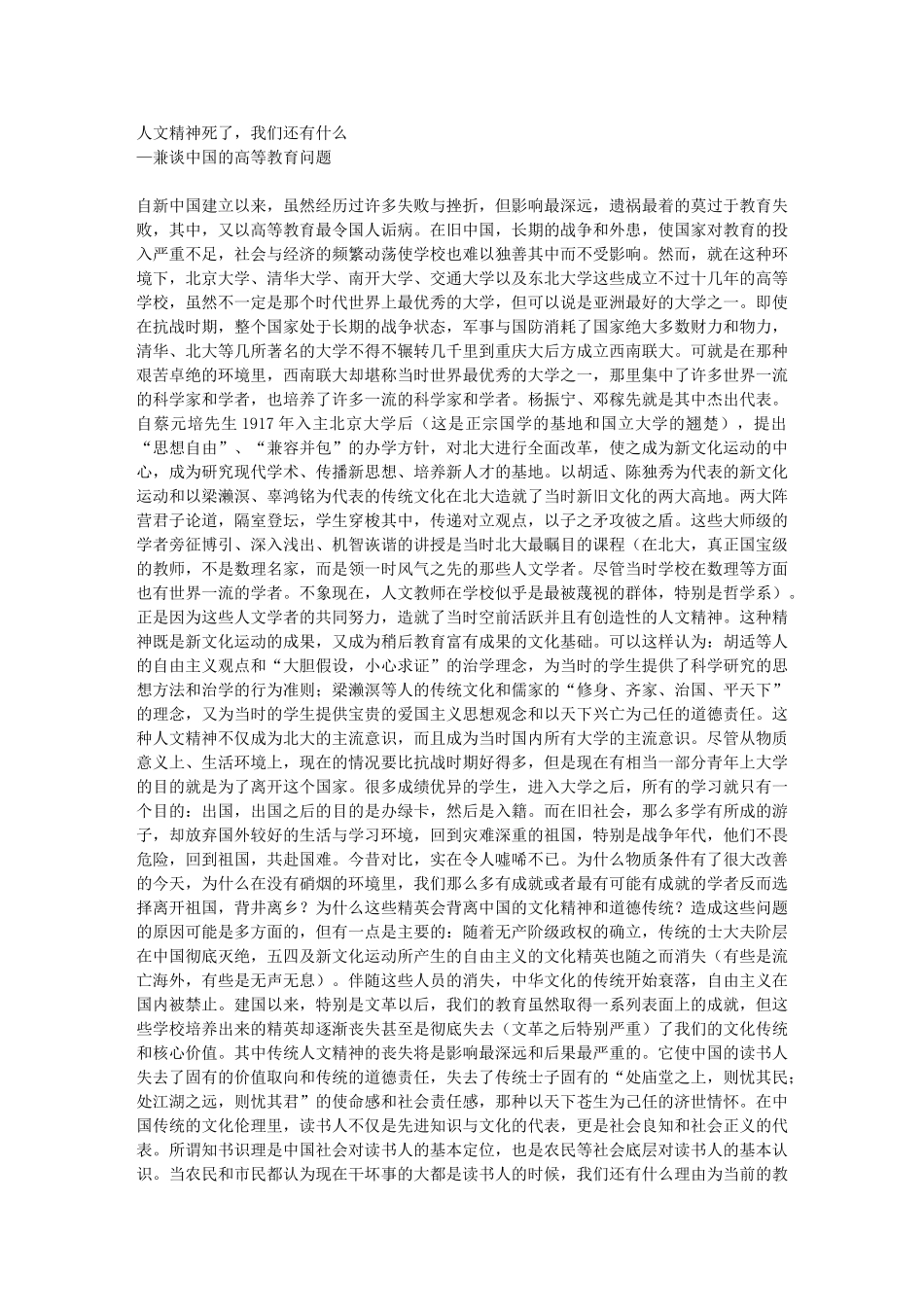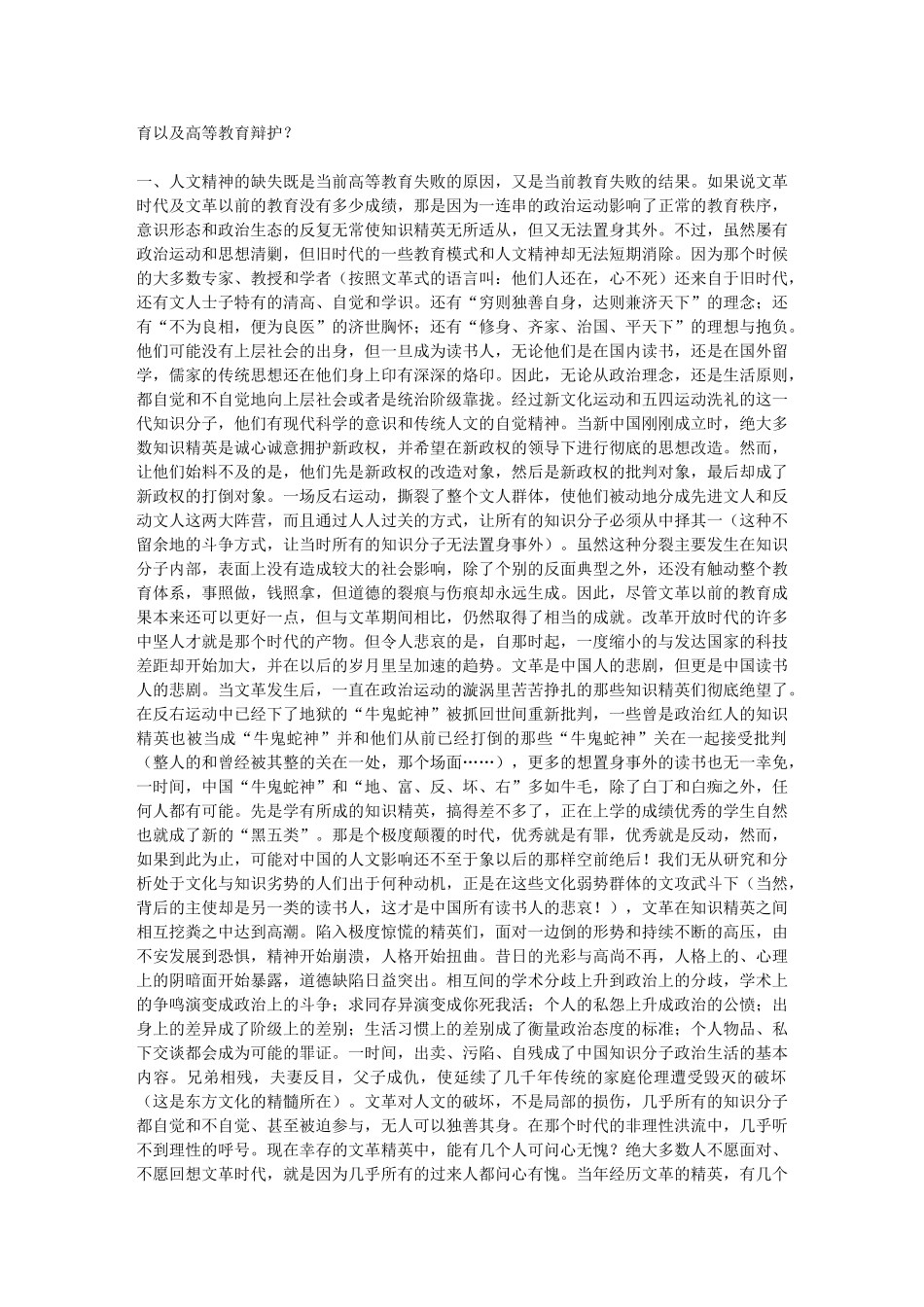人文精神死了,我们还有什么—兼谈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经历过许多失败与挫折,但影响最深远,遗祸最着的莫过于教育失败,其中,又以高等教育最令国人诟病。在旧中国,长期的战争和外患,使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社会与经济的频繁动荡使学校也难以独善其中而不受影响。然而,就在这种环境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以及东北大学这些成立不过十几年的高等学校,虽然不一定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但可以说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即使在抗战时期,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军事与国防消耗了国家绝大多数财力和物力,清华、北大等几所著名的大学不得不辗转几千里到重庆大后方成立西南联大。可就是在那种艰苦卓绝的环境里,西南联大却堪称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那里集中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学者,也培养了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和学者。杨振宁、邓稼先就是其中杰出代表。自蔡元培先生1917年入主北京大学后(这是正宗国学的基地和国立大学的翘楚),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现代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以梁濑溟、辜鸿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北大造就了当时新旧文化的两大高地。两大阵营君子论道,隔室登坛,学生穿梭其中,传递对立观点,以子之矛攻彼之盾。这些大师级的学者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机智诙谐的讲授是当时北大最瞩目的课程(在北大,真正国宝级的教师,不是数理名家,而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那些人文学者。尽管当时学校在数理等方面也有世界一流的学者。不象现在,人文教师在学校似乎是最被蔑视的群体,特别是哲学系)。正是因为这些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当时空前活跃并且有创造性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又成为稍后教育富有成果的文化基础。可以这样认为: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观点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为当时的学生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治学的行为准则;梁濑溟等人的传统文化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又为当时的学生提供宝贵的爱国主义思想观念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道德责任。这种人文精神不仅成为北大的主流意识,而且成为当时国内所有大学的主流意识。尽管从物质意义上、生活环境上,现在的情况要比抗战时期好得多,但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国家。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所有的学习就只有一个目的:出国,出国之后的目的是办绿卡,然后是入籍。而在旧社会,那么多学有所成的游子,却放弃国外较好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特别是战争年代,他们不畏危险,回到祖国,共赴国难。今昔对比,实在令人嘘唏不已。为什么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的今天,为什么在没有硝烟的环境里,我们那么多有成就或者最有可能有成就的学者反而选择离开祖国,背井离乡?为什么这些精英会背离中国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传统?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主要的: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彻底灭绝,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自由主义的文化精英也随之而消失(有些是流亡海外,有些是无声无息)。伴随这些人员的消失,中华文化的传统开始衰落,自由主义在国内被禁止。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后,我们的教育虽然取得一系列表面上的成就,但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精英却逐渐丧失甚至是彻底失去(文革之后特别严重)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其中传统人文精神的丧失将是影响最深远和后果最严重的。它使中国的读书人失去了固有的价值取向和传统的道德责任,失去了传统士子固有的“处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那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伦理里,读书人不仅是先进知识与文化的代表,更是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的代表。所谓知书识理是中国社会对读书人的基本定位,也是农民等社会底层对读书人的基本认识。当农民和市民都认为现在干坏事的大都是读书人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当前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