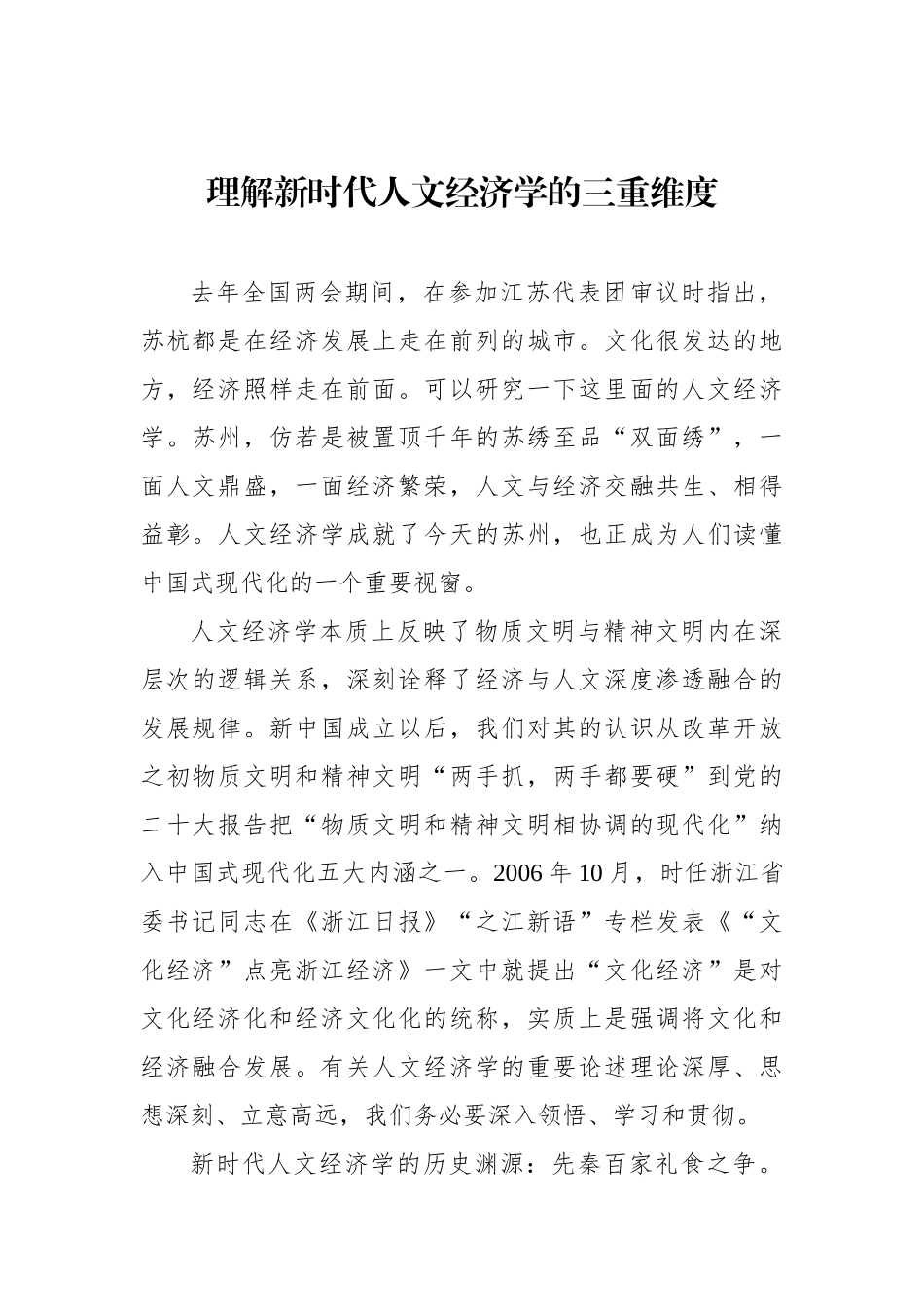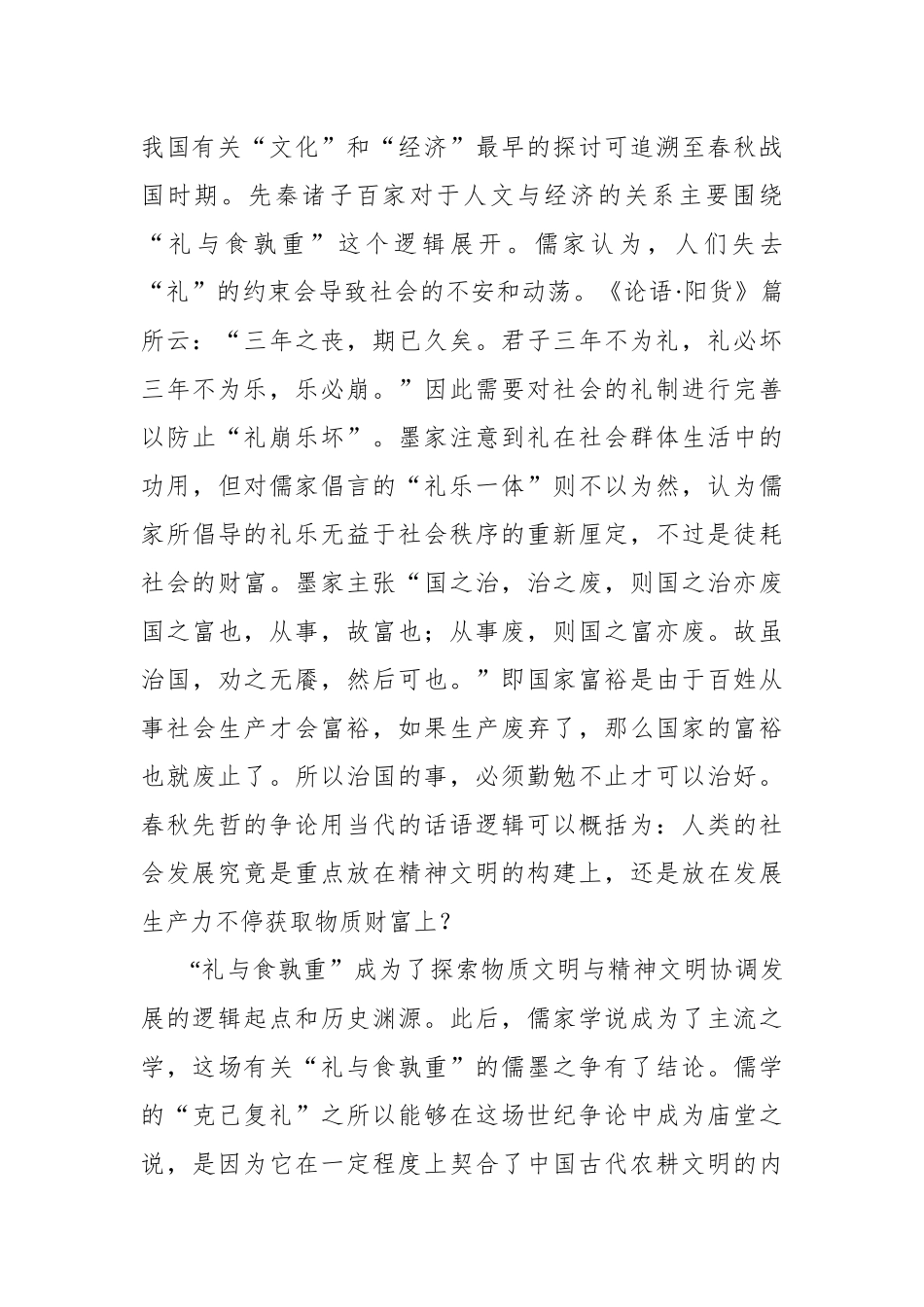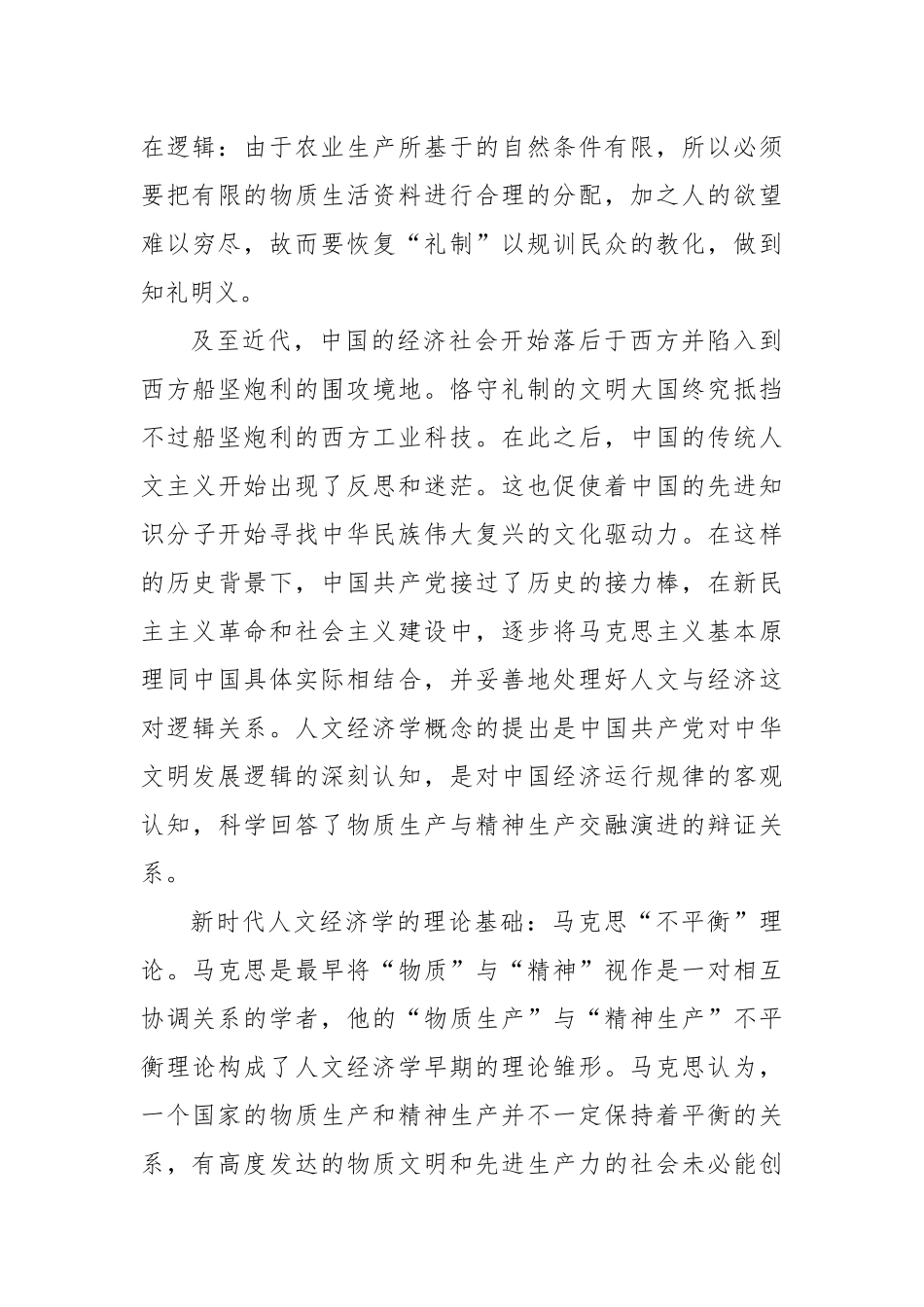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三重维度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苏州,仿若是被置顶千年的苏绣至品“双面绣”,一面人文鼎盛,一面经济繁荣,人文与经济交融共生、相得益彰。人文经济学成就了今天的苏州,也正成为人们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窗。人文经济学本质上反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内在深层次的逻辑关系,深刻诠释了经济与人文深度渗透融合的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其的认识从改革开放之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五大内涵之一。2006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中就提出“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实质上是强调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有关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理论深厚、思想深刻、立意高远,我们务必要深入领悟、学习和贯彻。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先秦百家礼食之争。我国有关“文化”和“经济”最早的探讨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百家对于人文与经济的关系主要围绕“礼与食孰重”这个逻辑展开。儒家认为,人们失去“礼”的约束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和动荡。《论语·阳货》篇所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因此需要对社会的礼制进行完善以防止“礼崩乐坏”。墨家注意到礼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的功用,但对儒家倡言的“礼乐一体”则不以为然,认为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无益于社会秩序的重新厘定,不过是徒耗社会的财富。墨家主张“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即国家富裕是由于百姓从事社会生产才会富裕,如果生产废弃了,那么国家的富裕也就废止了。所以治国的事,必须勤勉不止才可以治好。春秋先哲的争论用当代的话语逻辑可以概括为:人类的社会发展究竟是重点放在精神文明的构建上,还是放在发展生产力不停获取物质财富上?“礼与食孰重”成为了探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渊源。此后,儒家学说成为了主流之学,这场有关“礼与食孰重”的儒墨之争有了结论。儒学的“克己复礼”之所以能够在这场世纪争论中成为庙堂之说,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内在逻辑:由于农业生产所基于的自然条件有限,所以必须要把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进行合理的分配,加之人的欲望难以穷尽,故而要恢复“礼制”以规训民众的教化,做到知礼明义。及至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开始落后于西方并陷入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围攻境地。恪守礼制的文明大国终究抵挡不过船坚炮利的西方工业科技。在此之后,中国的传统人文主义开始出现了反思和迷茫。这也促使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驱动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妥善地处理好人文与经济这对逻辑关系。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深刻认知,是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认知,科学回答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交融演进的辩证关系。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不平衡”理论。马克思是最早将“物质”与“精神”视作是一对相互协调关系的学者,他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理论构成了人文经济学早期的理论雏形。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不一定保持着平衡的关系,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社会未必能创造出同样发达的精神文明和文学艺术。具体来说,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某些文艺兴盛的状态可能只存在于该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文明的进步,文明的繁荣底色会逐渐褪色。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曾经创造的文明体系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呈现给世人。其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