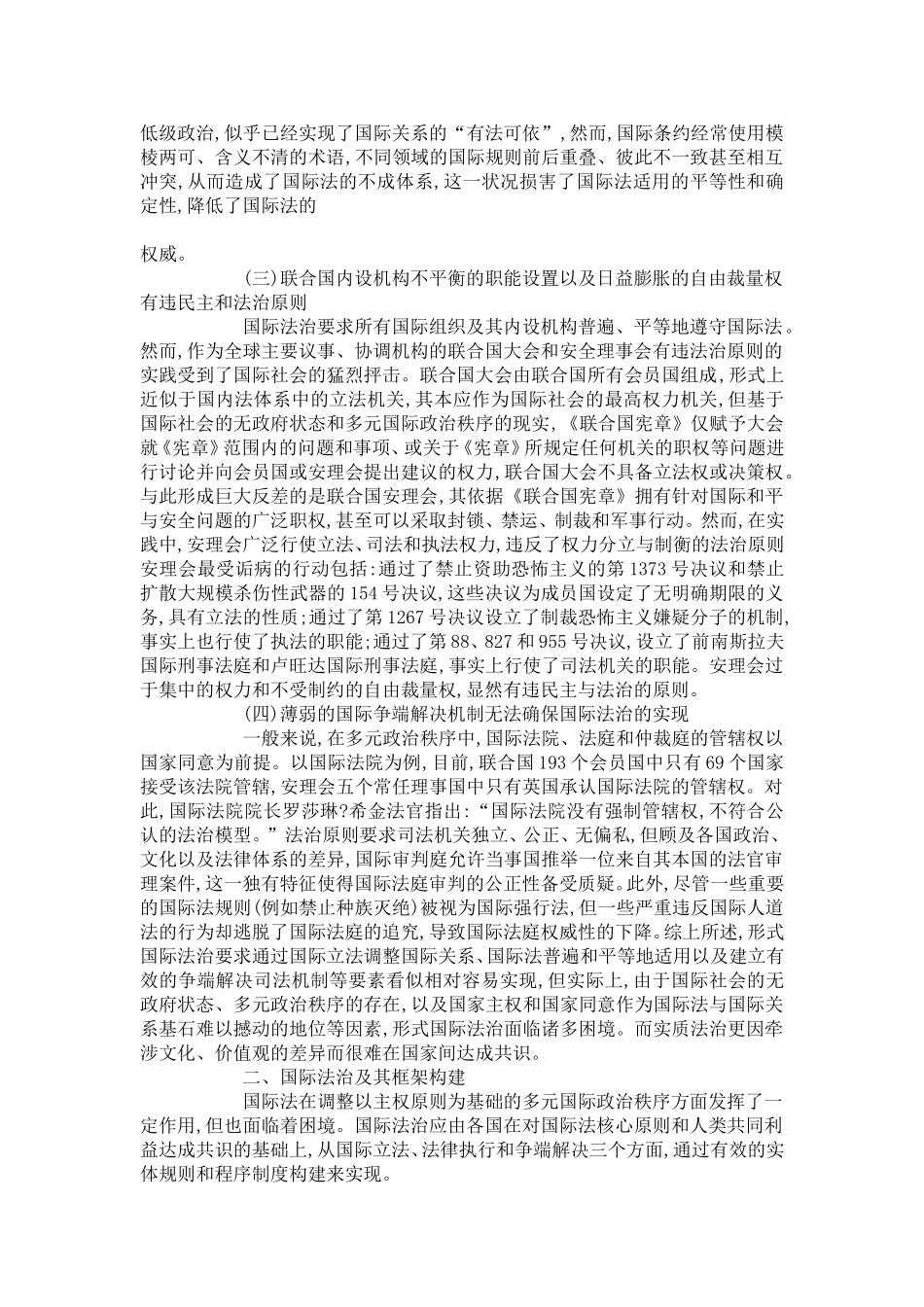多元秩序的国际法论文一、多元政治秩序维度下国际法治的当下困境在多元政治秩序的维度下,实现国际法治的基础性前提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有法可依、规范国际交往的有法必依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健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立法迅速发展,主权国家建立了庞大的条约体系,国际组织也创制了大量“软法”指导国家行为,其内容广泛涉及到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国际组织、特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既是资源和信息的收集与传播者,又是国际法和国家行为指南的制定与执行平台,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为了有效地执行国际法,国际和区域层面都建立了常设或临时的争端解决机构,包括国际和区域法院、法庭、仲裁庭等司法机构。由是,实现国际法治所需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的基础设施得以初步形成。然而,现实政治是构建国际关系首要考虑的因素,亦是国际法的支柱。尽管目前国际关系的重心正从强调国家权利和国家间关系转向对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人权保护的关切,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将长期存在,国家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石,国家同意是国际法治实现的重要前提。强势国家为了维护其重大利益或维持当权者统治,可能置经其同意的国际法于不顾,亦有个别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例如跨国恐怖主义集团)有选择或完全游离于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之外。国际社会秩序的多元化特征、主权国家迥异的政治立场和意愿、现有国际规则产生和执行机制的缺陷,也都决定了法治在国际层面很难像在国内层面那样经过而得以实现。概括来看,国际法治面临着以下四方面困境:(一)在多元政治框架下,国家政治意愿的差别化程度制约着国际法的订立国际法旨在调整主权平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亦包括国际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在形式上,主权国家无论实力强弱均有权参加条约的制定。多边条约的约文谈判和议定一般在国际会议上进行,由各国指派代表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表决权为一国一票,各国通过全体一致、多数同意或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协议。但实际上,权力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际法的制定,超级大国甚至可以主导规则的宏观方向和微观细节,影响规则的实际施行效果。可见,主权国家的政治意愿对国际法的订立和效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二)不平等法律适用削弱了国际法的实施效果法律的普遍、平等适用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国际法对国家的不平等适用主要体现在:首先,一些国家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但仍通过扩张和歪曲法律来进行辩护。例如,美国以“预防性自卫”为借口对伊拉克使用武力,违反了自卫权应在遭到武装攻击的前提下行使、且应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的要求,而面对这种行为,现有国际法律机制失效。其次,国际法适用程序的不透明也削弱了国际法的效果。例如,WTO争端裁决是在不公开审理之下作出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裁定只在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公布,而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中的153程序也是保密的。再者,国际公约数量庞大、调整范围广阔,从触及国家安全及核心利益的战争与和平、军控等高级政治,到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低级政治,似乎已经实现了国际关系的“有法可依”,然而,国际条约经常使用模棱两可、含义不清的术语,不同领域的国际规则前后重叠、彼此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从而造成了国际法的不成体系,这一状况损害了国际法适用的平等性和确定性,降低了国际法的权威。(三)联合国内设机构不平衡的职能设置以及日益膨胀的自由裁量权有违民主和法治原则国际法治要求所有国际组织及其内设机构普遍、平等地遵守国际法。然而,作为全球主要议事、协调机构的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违法治原则的实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猛烈抨击。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组成,形式上近似于国内法体系中的立法机关,其本应作为国际社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多元国际政治秩序的现实,《联合国宪章》仅赋予大会就《宪章》范围内的问题和事项、或关于《宪章》所规定任何机关的职权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向会员国或安理会提出建议的权力,联合国大会不具备立法权或决策权。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其依据《联合国宪章》拥有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