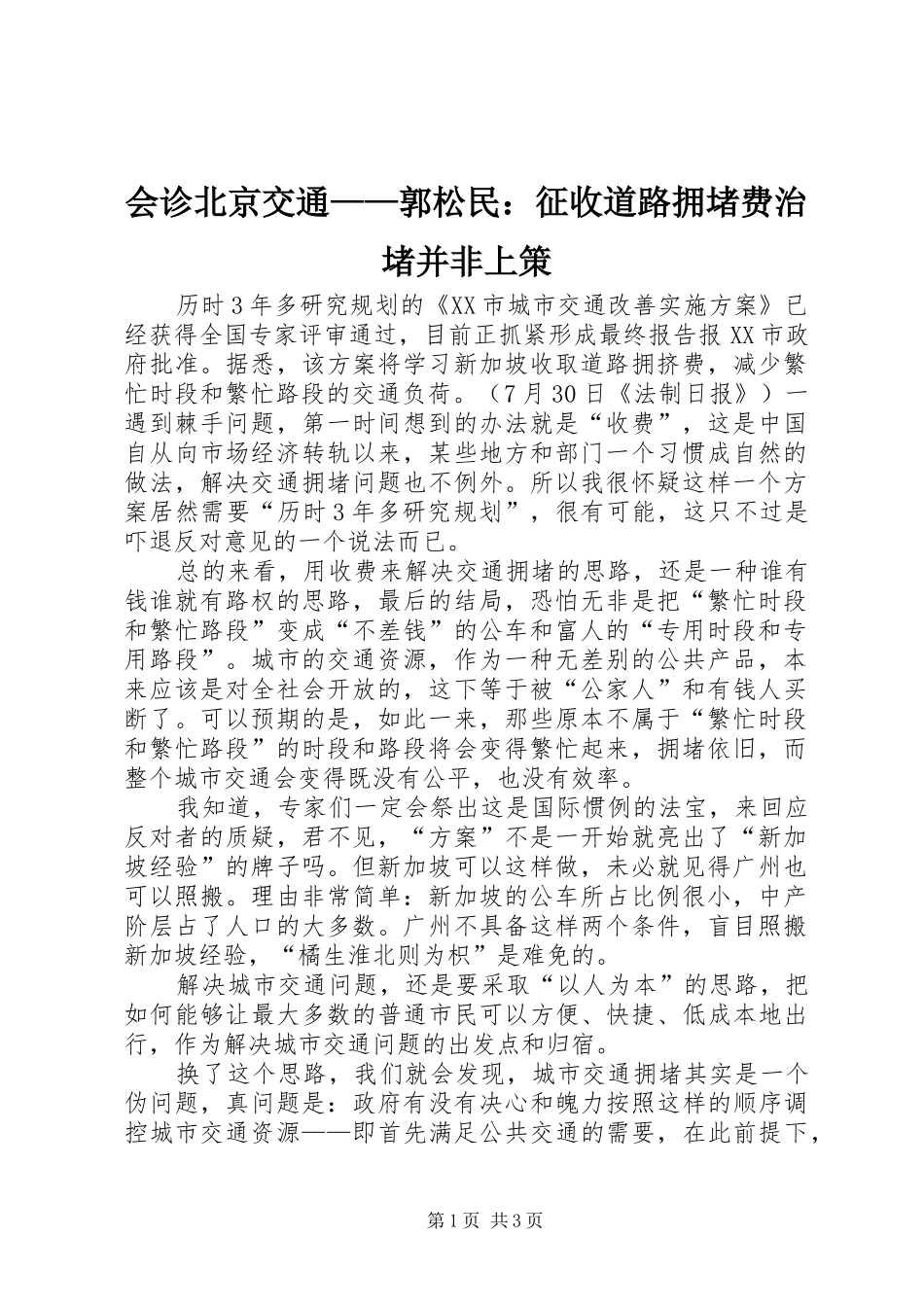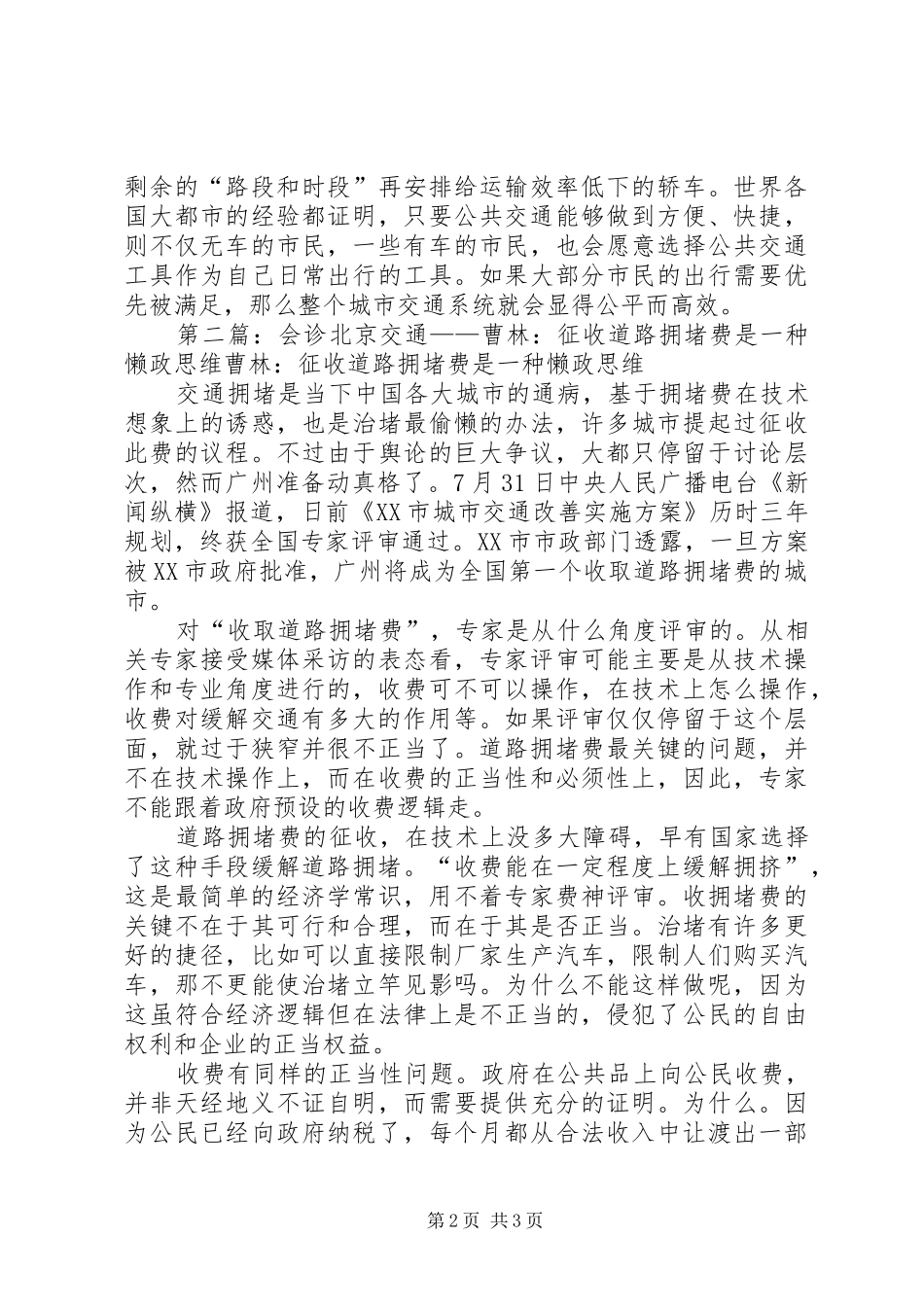会诊北京交通——郭松民:征收道路拥堵费治堵并非上策历时3年多研究规划的《XX市城市交通改善实施方案》已经获得全国专家评审通过,目前正抓紧形成最终报告报XX市政府批准。据悉,该方案将学习新加坡收取道路拥挤费,减少繁忙时段和繁忙路段的交通负荷。(7月30日《法制日报》)一遇到棘手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就是“收费”,这是中国自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某些地方和部门一个习惯成自然的做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也不例外。所以我很怀疑这样一个方案居然需要“历时3年多研究规划”,很有可能,这只不过是吓退反对意见的一个说法而已。总的来看,用收费来解决交通拥堵的思路,还是一种谁有钱谁就有路权的思路,最后的结局,恐怕无非是把“繁忙时段和繁忙路段”变成“不差钱”的公车和富人的“专用时段和专用路段”。城市的交通资源,作为一种无差别的公共产品,本来应该是对全社会开放的,这下等于被“公家人”和有钱人买断了。可以预期的是,如此一来,那些原本不属于“繁忙时段和繁忙路段”的时段和路段将会变得繁忙起来,拥堵依旧,而整个城市交通会变得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我知道,专家们一定会祭出这是国际惯例的法宝,来回应反对者的质疑,君不见,“方案”不是一开始就亮出了“新加坡经验”的牌子吗。但新加坡可以这样做,未必就见得广州也可以照搬。理由非常简单:新加坡的公车所占比例很小,中产阶层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广州不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盲目照搬新加坡经验,“橘生淮北则为枳”是难免的。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还是要采取“以人为本”的思路,把如何能够让最大多数的普通市民可以方便、快捷、低成本地出行,作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换了这个思路,我们就会发现,城市交通拥堵其实是一个伪问题,真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决心和魄力按照这样的顺序调控城市交通资源——即首先满足公共交通的需要,在此前提下,第1页共3页剩余的“路段和时段”再安排给运输效率低下的轿车。世界各国大都市的经验都证明,只要公共交通能够做到方便、快捷,则不仅无车的市民,一些有车的市民,也会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作为自己日常出行的工具。如果大部分市民的出行需要优先被满足,那么整个城市交通系统就会显得公平而高效。第二篇:会诊北京交通——曹林:征收道路拥堵费是一种懒政思维曹林:征收道路拥堵费是一种懒政思维交通拥堵是当下中国各大城市的通病,基于拥堵费在技术想象上的诱惑,也是治堵最偷懒的办法,许多城市提起过征收此费的议程。不过由于舆论的巨大争议,大都只停留于讨论层次,然而广州准备动真格了。7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报道,日前《XX市城市交通改善实施方案》历时三年规划,终获全国专家评审通过。XX市市政部门透露,一旦方案被XX市政府批准,广州将成为全国第一个收取道路拥堵费的城市。对“收取道路拥堵费”,专家是从什么角度评审的。从相关专家接受媒体采访的表态看,专家评审可能主要是从技术操作和专业角度进行的,收费可不可以操作,在技术上怎么操作,收费对缓解交通有多大的作用等。如果评审仅仅停留于这个层面,就过于狭窄并很不正当了。道路拥堵费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技术操作上,而在收费的正当性和必须性上,因此,专家不能跟着政府预设的收费逻辑走。道路拥堵费的征收,在技术上没多大障碍,早有国家选择了这种手段缓解道路拥堵。“收费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拥挤”,这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常识,用不着专家费神评审。收拥堵费的关键不在于其可行和合理,而在于其是否正当。治堵有许多更好的捷径,比如可以直接限制厂家生产汽车,限制人们购买汽车,那不更能使治堵立竿见影吗。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这虽符合经济逻辑但在法律上是不正当的,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和企业的正当权益。收费有同样的正当性问题。政府在公共品上向公民收费,并非天经地义不证自明,而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明。为什么。因为公民已经向政府纳税了,每个月都从合法收入中让渡出一部第2页共3页分交给政府,就是为了向其“购买”国防、交通、环保、教育等市场和个人无力自给的公共产品。为了享受宽阔的公路和便捷的交通,车主更是支付了从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