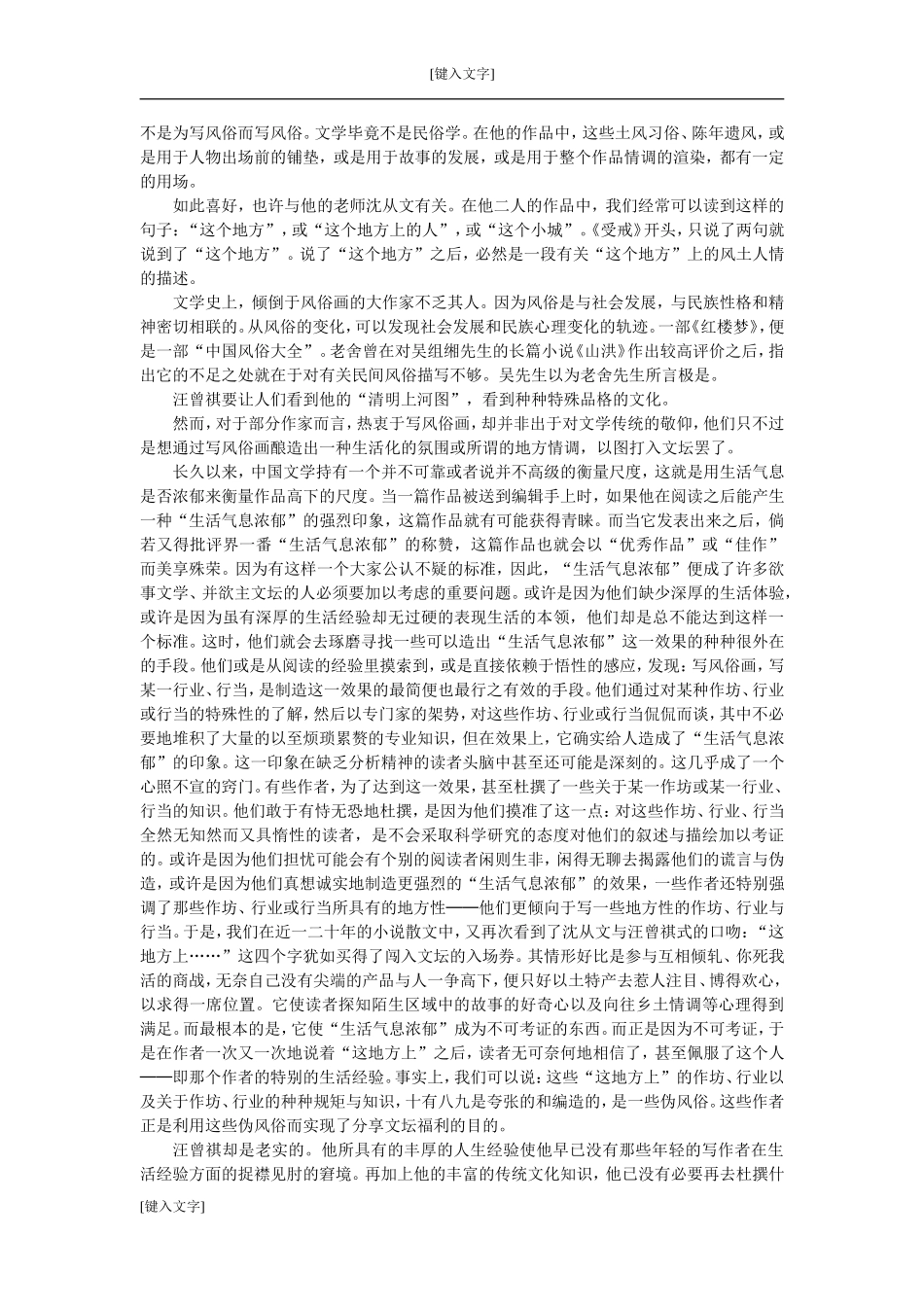[键入文字]汪曾祺的文学世界曹文轩1.汪式“地域主义”江曾祺基本上属于一个地域性作家。他把绝大部分篇幅交给了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地区一方土地。从空间大小来讲,世界上的作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地域性作家,一类是地域性作家。前者认定,所谓的地方特色、风俗人情,于文学而言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甚至有意淡化和排斥这些元素。这种认定,其理论基础是:文学所要表现的,应是人类共有的生活以及普遍的人性。这类作家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了没有特定空间的想象上,所编织的故事,带有更多的假设性。在西方,这一类作家似乎占多数。而另一类作家,则将生活的空间严格地限制在一个他认为他所熟悉的固定的点上,方圆十八里,一辈子也不肯跨越一步。在其作品中,显示出了浓重的地方情调和特别的小文化环境。在中国,这一类作家似乎居多。沈从文是这类作家的一个经典。他表现的生活范围或者说那些最能代表他创作成就的作品,基本上都生长于湘西。国外也有这类作家,著名者如美国的福克纳。据他自己讲,他一生就只写了邮票大小一块地方。这些作家的理论基础是:艺术必须选择特殊的空间,展示特殊的生活画面,通过对特定文化的显示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艺术的认识和审美之目的。批评者对这两者褒贬似乎不一。但印象中,挨批评更多一些的似乎是那些地域性作家。就中国而言,地域性的过分强调、地域性作家所占比例过大,多少妨碍了中国文学的提升,降低了中国文学的规格。在中国,地域性变成了一位作家成功的一条途径。谁想获得成功,谁就必须讲究地域性。占据一方生活小岛,以对付文坛的激烈竞争,竟成为许多中国作家的一个意识、一种策略。于是当代文学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东西南北,各据一方,以独特的地域风土人情为奇货为本钱来从事文学的买卖。于是,偌大一片中国版图,被瓜分殆尽。于是出来所谓的湘军、晋军之类的说法。于是,文学要表现的人的生活,最终变成了地方生活,中国文化变成了若干区域文化。地域性的过分强调,最终变成了地域主义,直至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当代文学少了世界文学的宏大气派。对泥土气息的过于认同,使中国文学从风格上讲,就显得有点儿过于小气,甚至俗气。地域主义的极端化,使文学失去了抽象的动机,失去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失去了重大的、具有哲学意义的主题,并因它的过于狭隘与特别而失去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主义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创作观念。但,却谁也无法批评长期占据一方土地而经营他的文字世界的汪曾祺。一,他虽然将自己的作品的内容限制在一区域内,但他并不向他人提倡地域主义,尽管他是率先体现地域性的,但后来有那么多人蜂涌而上,则与他无关;二,他很得当、很有分寸地体现了地域性,未去一味摆弄地域性;三,他是带着一种现代的、永恒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态度重新走向地域的,地域只不过是他为他的普遍性的艺术观找到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场所而已。《受戒》如此,《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等莫不如此。地域性非但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为施展人性、显示他美学趣味的佳境。2.汪式“风俗画”当许多年轻作家拜倒在现代观念的脚下,想方设法寻找现代人的感觉,竭力在作品中制造现代氛围时,汪曾祺的作品却倒行逆施,追忆着过去,追忆着传统,追忆着原初,给人们酿出的是一股温馨的古风。古风之生成,与风俗画有关。他对风俗画的追求是刻意的。追溯现代文学史,在小说中对风俗画的描绘始于鲁迅先生(如《祝福》《社戏》《孔乙己》等),沈从文的《边城》则是风俗画的一个高峰。这条线索,在五六十年代中断了。因为,这种美学情趣,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到了80年代初,又由汪曾祺将这条线索连接了起来。婚丧礼仪、居所陈设、饮食服饰等等民俗现象,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当然,又绝[键入文字][键入文字]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文学毕竟不是民俗学。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土风习俗、陈年遗风,或是用于人物出场前的铺垫,或是用于故事的发展,或是用于整个作品情调的渲染,都有一定的用场。如此喜好,也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有关。在他二人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