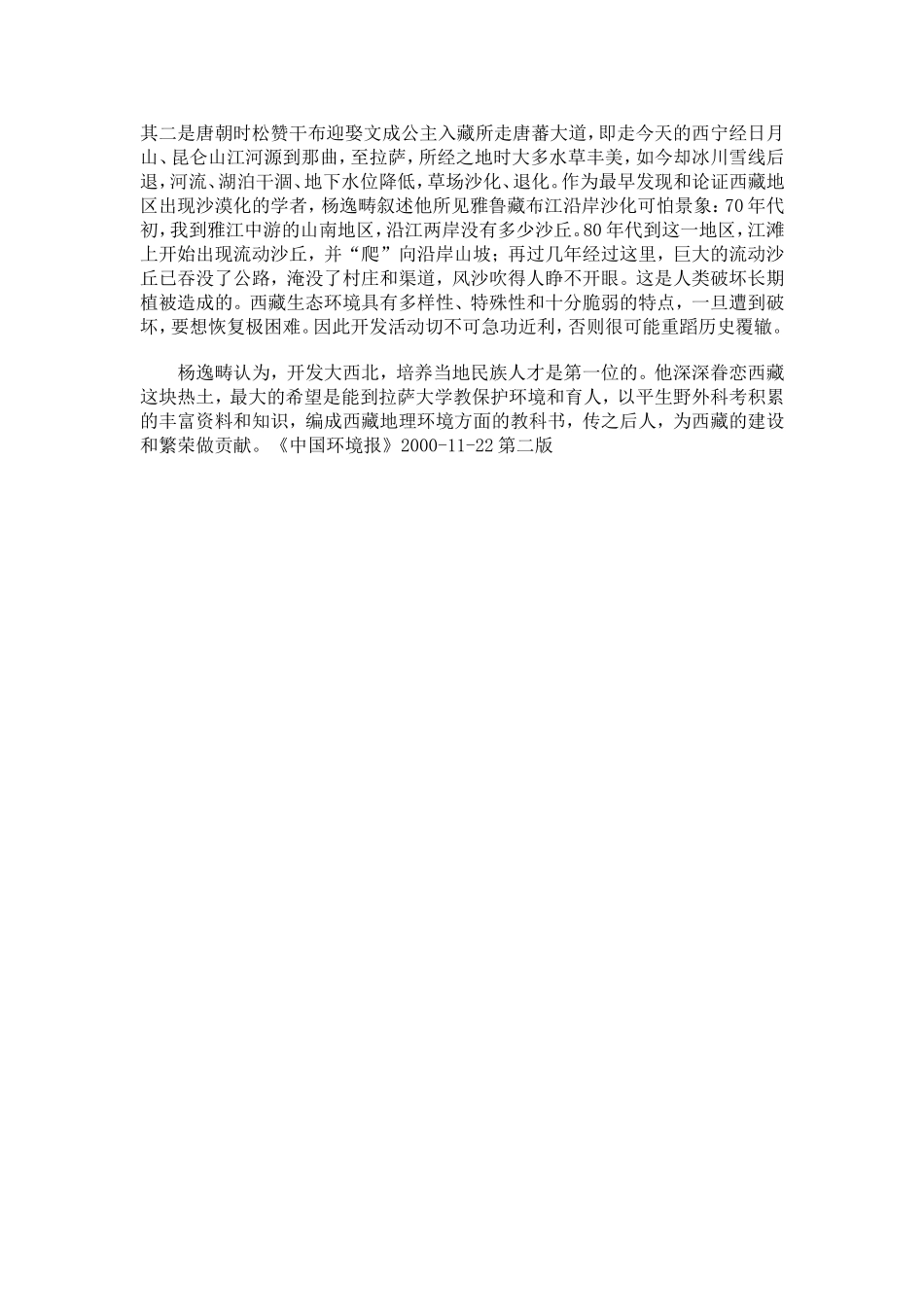杨逸畴:西部开发先行者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的一栋普通宿舍里,记者慕名见到被称为“当代徐霞客”、65岁的地理学家杨逸畴。他回忆起8次进大峡谷科考激动不已:大峡谷奇观世界第一,而沿途轰鸣飞泻的雪崩、泥石流,惊心动魄的过江溜索,令人闻风色变的毒蛇、毒蜂、旱蚂蝗,处处险象环生;当地各族群众热情为科考队当向导、背粮食和仪器,大家同甘共苦,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他讲了一个故事:每次完成考察踏上归程,总要派一名跑得最快的珞巴族民工先回去报信,带上口粮食来接我们,几天后我们和前来接应的村民及民工的亲人在途中相遇,大家见面相抱痛哭那情景令人永生难忘。杨逸畴动情地说,1996年,西藏自治区领导向中央汇报工作,院领导参加了,回来后告诉我,大峡谷的乡亲们想念你,令我深受感动。我因为高血压和心脏动脉血管变形,被医生严厉禁止再上高原,当时已有十几年没去大峡谷了。我们这些老青藏队员们也都很怀念乡亲们,他特别提到南迦巴瓦峰西坡格嘎村的藏族老人德钦。考察队每次上山或进大峡谷,都要路过他的家,老人每次都在村口迎接我们。队员们住在老人家里,大家围着火塘喝酥油茶,吃手抓肉,和老人聊天,感觉就象在自己家一样。考察队返回时,就把设备器材存在老人家中,下次进山再用。老人是一部活地图,有关大峡谷的各种故事、南迦巴瓦峰西坡跃动冰川数10年间的变化,1950年墨脱大地震等极其重要的历史情况,就是老人讲述的。队员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南迦巴瓦老人”。老人提供的这些情况,为后来相关的科考成果奠定了重要基础。杨逸畴说,可以说,没有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科考活动就寸步难行,更不要说今天大峡谷的累累科考硕果了。说到开发西部这位把大半生献给青藏高原的地理学家充满自豪感:很多朋友把我们这些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科考工作者称为“青藏人”,我们以此为荣。看到我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在国家发展战略能够得到重视和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感到欣慰了。他说,科学要允许大胆假设、大胆创新。大峡谷对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峡谷内的江水从海拔3000多米陡然下降到500多米,形成一个巨大落差,蕴藏了其世界第一的水能资源。科学工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利用对大拐弯裁弯取直,从派———多雄拉———汗密建设16公里的引水隧洞,建设成3000多千瓦的水电站,发电能量将超过三峡发电量2.5倍。如果进一步打通喜玛拉雅山山脉,形成新水汽通道,把雅江水和印度洋暖湿空气流引向西北,就有可能彻底改变我国西北干旱面貌。当然,这些都还有待于科学上做大量周密的调查论证工作。现在就应该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把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织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雅鲁藏布江和大峡谷的开发将对西藏和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的改善起到重要的作用。开发西北,一定要保护生态环境,否则一切都会成为无用功。杨逸畴引证历史上前车之鉴:其一是汉唐兴盛的丝绸之路,当年都是绿洲,只因人类无度开垦索取,破坏生态平衡,其后都为流沙吞没,楼兰、尼雅等古城废墟就是历史的见证其二是唐朝时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所走唐蕃大道,即走今天的西宁经日月山、昆仑山江河源到那曲,至拉萨,所经之地时大多水草丰美,如今却冰川雪线后退,河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位降低,草场沙化、退化。作为最早发现和论证西藏地区出现沙漠化的学者,杨逸畴叙述他所见雅鲁藏布江沿岸沙化可怕景象:70年代初,我到雅江中游的山南地区,沿江两岸没有多少沙丘。80年代到这一地区,江滩上开始出现流动沙丘,并“爬”向沿岸山坡;再过几年经过这里,巨大的流动沙丘已吞没了公路,淹没了村庄和渠道,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这是人类破坏长期植被造成的。西藏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特殊性和十分脆弱的特点,一旦遭到破坏,要想恢复极困难。因此开发活动切不可急功近利,否则很可能重蹈历史覆辙。杨逸畴认为,开发大西北,培养当地民族人才是第一位的。他深深眷恋西藏这块热土,最大的希望是能到拉萨大学教保护环境和育人,以平生野外科考积累的丰富资料和知识,编成西藏地理环境方面的教科书,传之后人,为西藏的建设和繁荣做贡献。《中国环境报》2000-11-22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