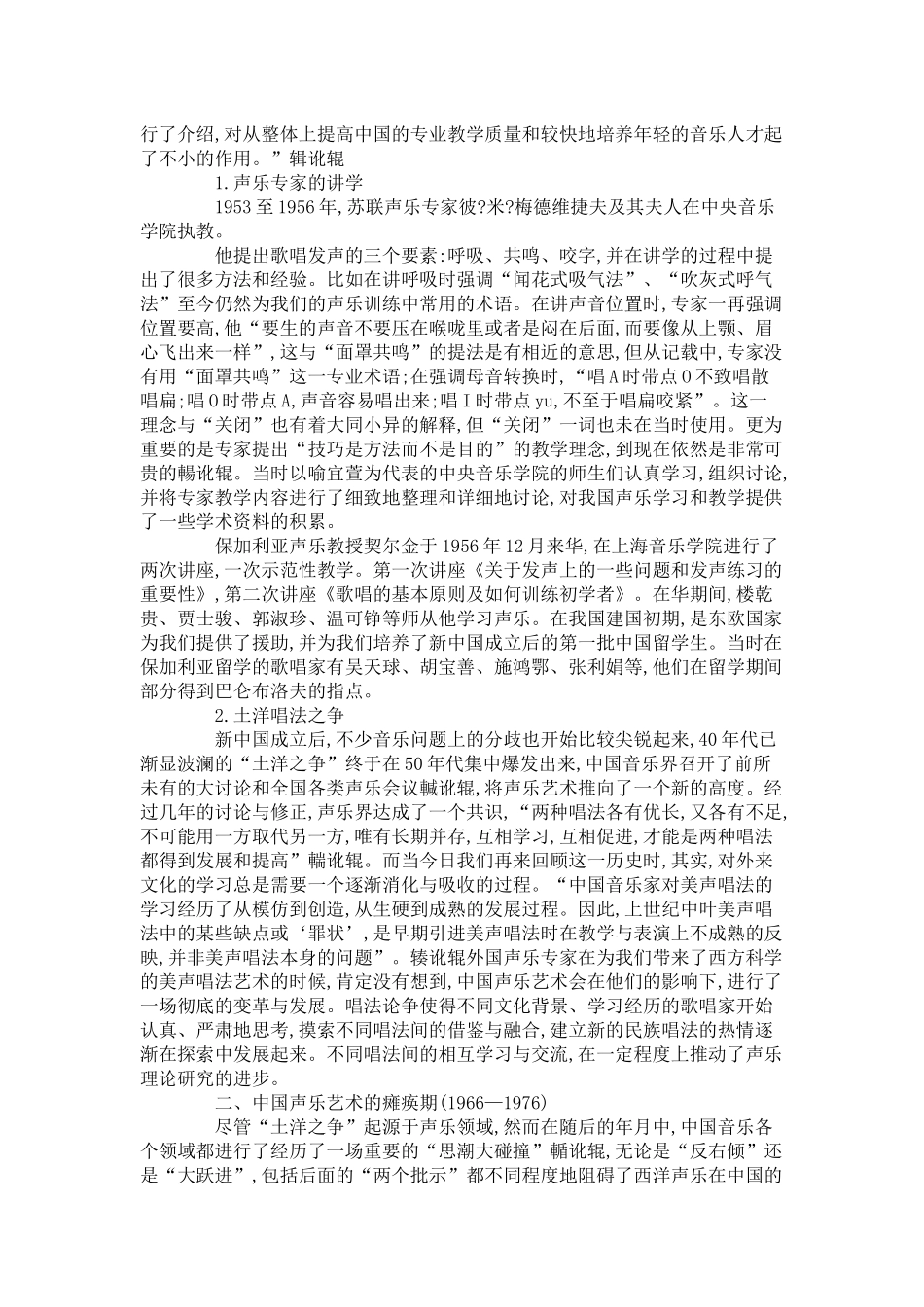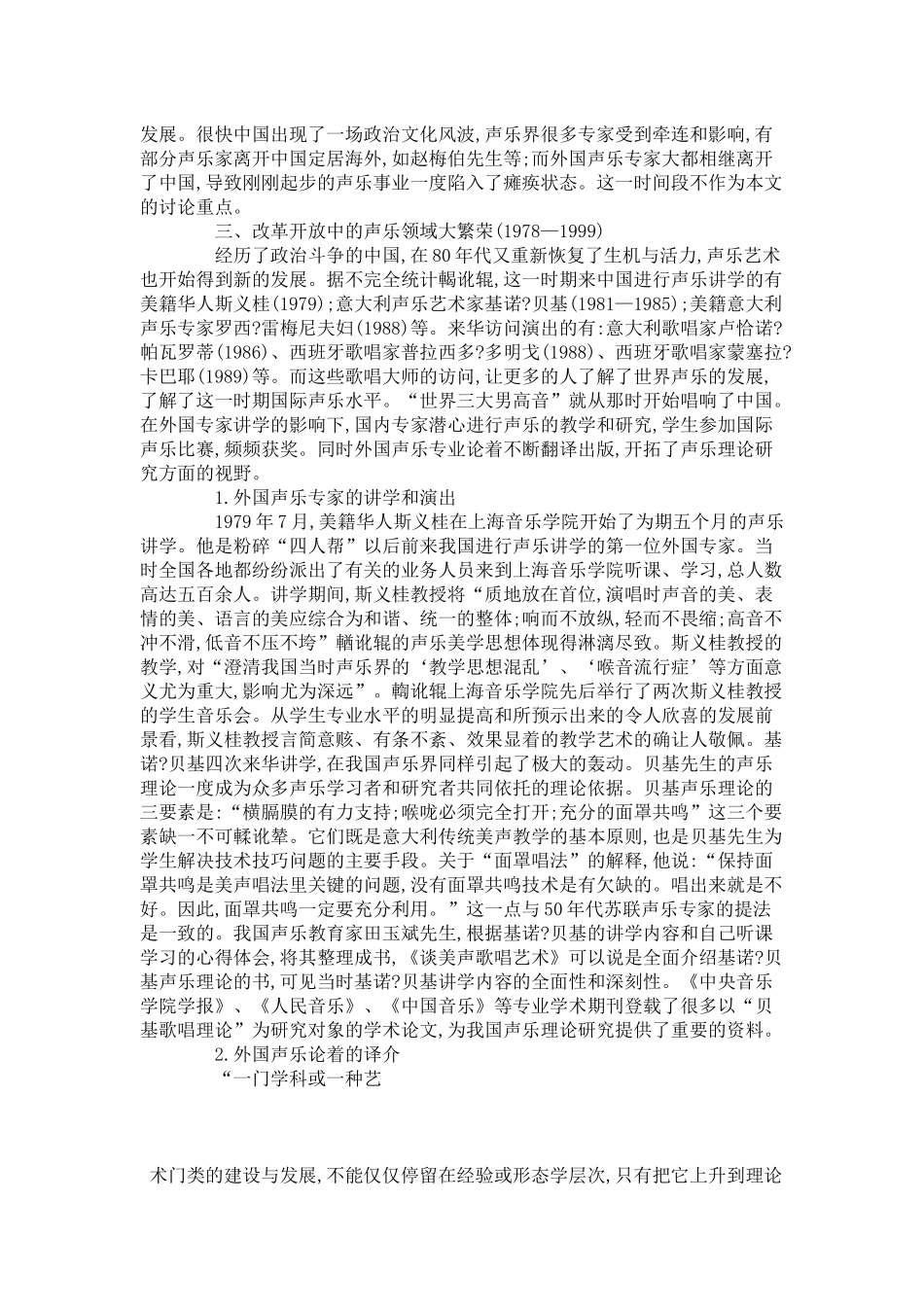外国专家对国内声乐的影响及启发后期以上海国立音乐院为代表的高等音乐教育的兴起,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上最为全面的传播西洋音乐文化的时期”①。学习和运用西洋发声方法和技巧,美声唱法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声乐艺术开始了新的一页。本文通过对外国声乐专家②在我国进行的声乐教学或演出等活动的梳理,以对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声乐艺术发展的轨迹,从而获得一些启示。引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传播和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有两方面③:一是通过“五四”前后出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另一则是通过外籍教师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我国各音乐院校任职的外籍声乐教师有④:苏石林、斯拉维阿诺夫、马尔切夫、马可林斯基夫人、范天祥夫人、威尔逊夫人、凯夫、沙里凡诺夫、富尔登、德利亚等。来华进行演出的着名外国音乐家有⑤:世界着名男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宾;世界着名花腔女音歌唱家加利?库契;世界着名女高音歌唱家丽利?庞斯等。虽然当时留下的文字记载资料较少,但这些外籍声乐教师及音乐家在这一历史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这一时期来华时间最长,为中国声乐做出巨大贡献的当属苏石林。苏石林是苏联优秀的男低音歌唱家、卓越的声乐教育家。自1924年来到中国至1956年离开,他在中国的三十余年里在国立音专执教长达26年。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苏石林不仅为中国带来了俄罗斯声乐艺术;而且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声乐人才,如:黄友葵、斯义桂、周小燕、唐荣枚、胡然、高芝兰、李志曙、温可铮、董爱琳、魏启贤、孙家馨等;同时他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苏石林对声乐的演绎“不仅体现在对于俄罗斯艺术歌曲及西洋传统歌剧的诠释,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演唱中国歌曲所达到的极高的艺术境界”。⑥据廖辅叔的回忆说,苏石林演唱的《问》、《教我如何不想他》丝毫不亚于当时的中国声乐歌唱家⑦。就在西洋美声唱法开始在专业音乐界得到传播的时候,“新的民族学派的声乐艺术早在救亡歌咏运动中就已露出苗头来了”⑧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音乐界出现了所谓“救亡派”与“学院派”之间的矛盾,“尽管两者在抗日救亡这一根本目的上并无分歧,但因音乐观念、音乐技巧等方面的分歧与差距,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互相批评乃至讥讽攻击的现象。”⑨一场具有学术争议的文化争鸣———“土洋之争”在这一时期初现,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声乐艺术领域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东欧国家声乐专家对中国声乐的影响(1949—1965)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相关文化协定,大量聘请各个学科的东欧专家支援建设。声乐方面专家有⑩:梅德维捷夫(苏联)、阿克达夫?克利斯德斯库(罗马尼亚,)、契尔金(保加利亚)、基洛娃(保加利亚)等。像这样大规模地聘请国外音乐专家来华的教学和学术活动,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的壮举。60年代初,保加利亚专家布伦巴罗夫对我国声乐也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笔者资料有限,不能过多展开。这些专家不仅“及时弥补了新中国建立初期高级专业教师的不足,还将完整的苏联音乐教育体系全面系统地进行了介绍,对从整体上提高中国的专业教学质量和较快地培养年轻的音乐人才起了不小的作用。”辑讹辊1.声乐专家的讲学1953至1956年,苏联声乐专家彼?米?梅德维捷夫及其夫人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他提出歌唱发声的三个要素:呼吸、共鸣、咬字,并在讲学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方法和经验。比如在讲呼吸时强调“闻花式吸气法”、“吹灰式呼气法”至今仍然为我们的声乐训练中常用的术语。在讲声音位置时,专家一再强调位置要高,他“要生的声音不要压在喉咙里或者是闷在后面,而要像从上颚、眉心飞出来一样”,这与“面罩共鸣”的提法是有相近的意思,但从记载中,专家没有用“面罩共鸣”这一专业术语;在强调母音转换时,“唱A时带点O不致唱散唱扁;唱O时带点A,声音容易唱出来;唱I时带点yu,不至于唱扁咬紧”。这一理念与“关闭”也有着大同小异的解释,但“关闭”一词也未在当时使用。更为重要的是专家提出“技巧是方法而不是目的”的教学理念,到现在依然是非常可贵的輰讹辊。当时以喻宜萱为代表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们认真学习,组织讨论,并将专家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