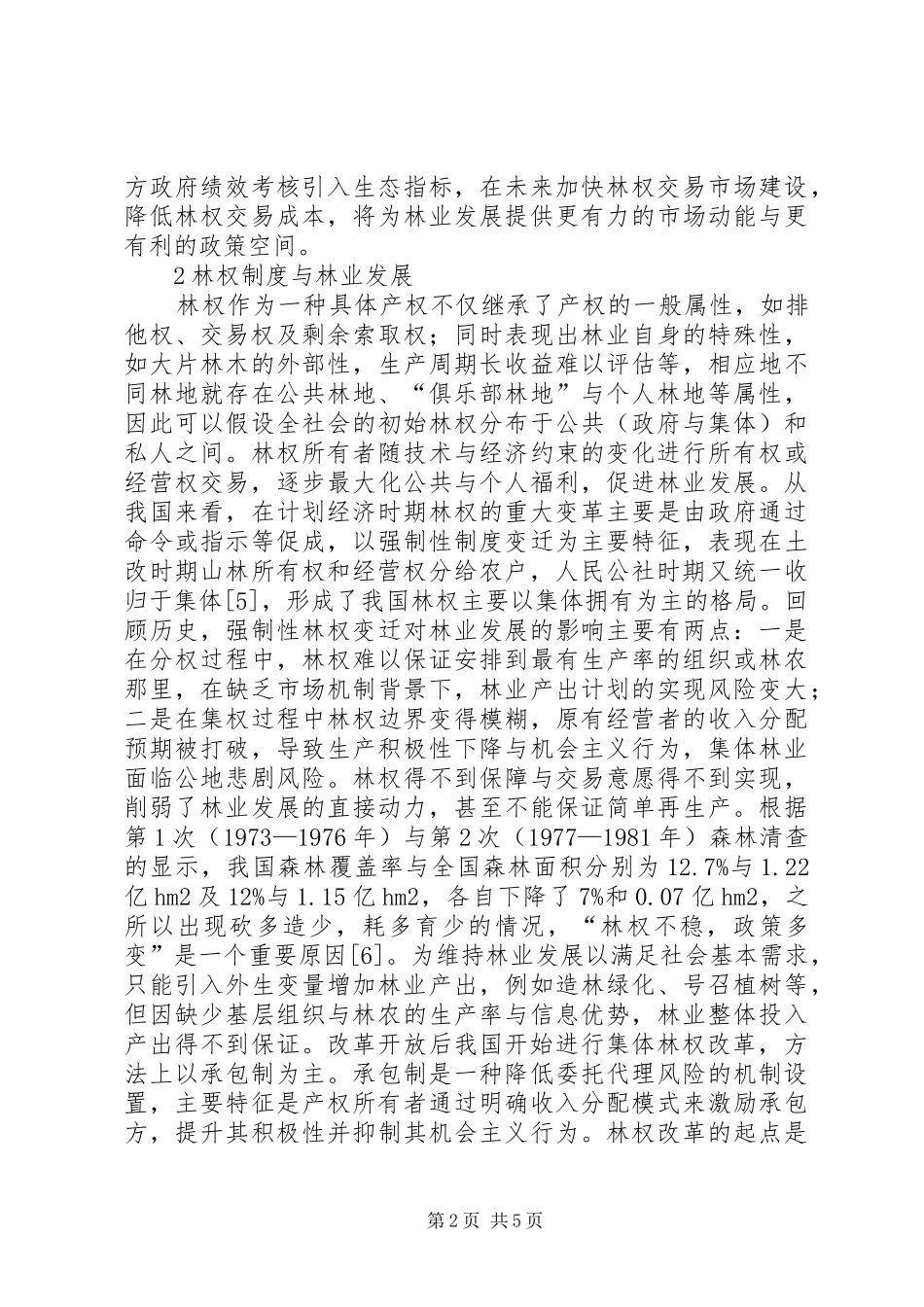集体林权改革与林业发展政治经济分析摘要:从林权制度与政府行为角度,以森林覆盖率变化为指标,对我国林业发展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集体林权改革与政府行为对林业发展起重要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地方政府评价指标以及林权交易市场建设,为林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形成互促机制提供政策条件与市场基础。关键词:集体林权;林权改革;地方政府;森林覆盖率1引言我国集体林权改革始于1981年,类似1978年小岗村“分田到户”,当时人民公社、生产队等集体拥有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尝试把集体林地分给农户经营管理。其后历经延长承包期、省份试点等实践,2008年政府在全国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XX年提出完善集体林权制度。这一期间重要的林权改革政策与林业发展状况,刘璨和张永亮等(20XX)[1]和刘璨和刘浩等(20XX)[2]做了详细的归纳与实证研究。虽然在时间上林地改革相对田地改革似乎进度稍慢,但此间我国林业发展同样取得巨大成绩。由于林业发展内涵丰富而大国林业发展的根基是本国林木增加,本文以森林覆盖率作为衡量林业发展的代理指标。数据显示全球森林面积20世纪90年代显著减少[3],根据新近20XX年与20XX年的世界森林状况评估,全球森林面积缩减状况仍在继续[4],但以1981年森林清查数据为基期,我国20XX年森林覆盖率增长了8.93%,年均增长约0.27%,为世界林业做出重大贡献。这一典型事实,为我们理解林权改革提供了一个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林权改革政策对促进林业发展是有效的。政策有效理论上意味着宏观变量具有微观基础,所以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也是我国渐近式改革的重要经验。基于此,本文首先以我国林权制度安排与林业发展的基本进程为线索,分析林权改革与林业发展的内在关系,然后分析政府发展林业的激励。研究结果表明,集体林权改革为我国林业发展提供了市场激励,虽然地方政府偏好gdp增长,但中央政府可以利用地区增长在宏观层面保障林业发展,这为我国总体优异的林业发展成绩提供了一个解释。本文的现实意义是:随着20XX年地第1页共5页方政府绩效考核引入生态指标,在未来加快林权交易市场建设,降低林权交易成本,将为林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市场动能与更有利的政策空间。2林权制度与林业发展林权作为一种具体产权不仅继承了产权的一般属性,如排他权、交易权及剩余索取权;同时表现出林业自身的特殊性,如大片林木的外部性,生产周期长收益难以评估等,相应地不同林地就存在公共林地、“俱乐部林地”与个人林地等属性,因此可以假设全社会的初始林权分布于公共(政府与集体)和私人之间。林权所有者随技术与经济约束的变化进行所有权或经营权交易,逐步最大化公共与个人福利,促进林业发展。从我国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林权的重大变革主要是由政府通过命令或指示等促成,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表现在土改时期山林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给农户,人民公社时期又统一收归于集体[5],形成了我国林权主要以集体拥有为主的格局。回顾历史,强制性林权变迁对林业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分权过程中,林权难以保证安排到最有生产率的组织或林农那里,在缺乏市场机制背景下,林业产出计划的实现风险变大;二是在集权过程中林权边界变得模糊,原有经营者的收入分配预期被打破,导致生产积极性下降与机会主义行为,集体林业面临公地悲剧风险。林权得不到保障与交易意愿得不到实现,削弱了林业发展的直接动力,甚至不能保证简单再生产。根据第1次(1973—1976年)与第2次(1977—1981年)森林清查的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与全国森林面积分别为12.7%与1.22亿hm2及12%与1.15亿hm2,各自下降了7%和0.07亿hm2,之所以出现砍多造少,耗多育少的情况,“林权不稳,政策多变”是一个重要原因[6]。为维持林业发展以满足社会基本需求,只能引入外生变量增加林业产出,例如造林绿化、号召植树等,但因缺少基层组织与林农的生产率与信息优势,林业整体投入产出得不到保证。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进行集体林权改革,方法上以承包制为主。承包制是一种降低委托代理风险的机制设置,主要特征是产权所有者通过明确收入分配模式来激励承包方,提升其积极性并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