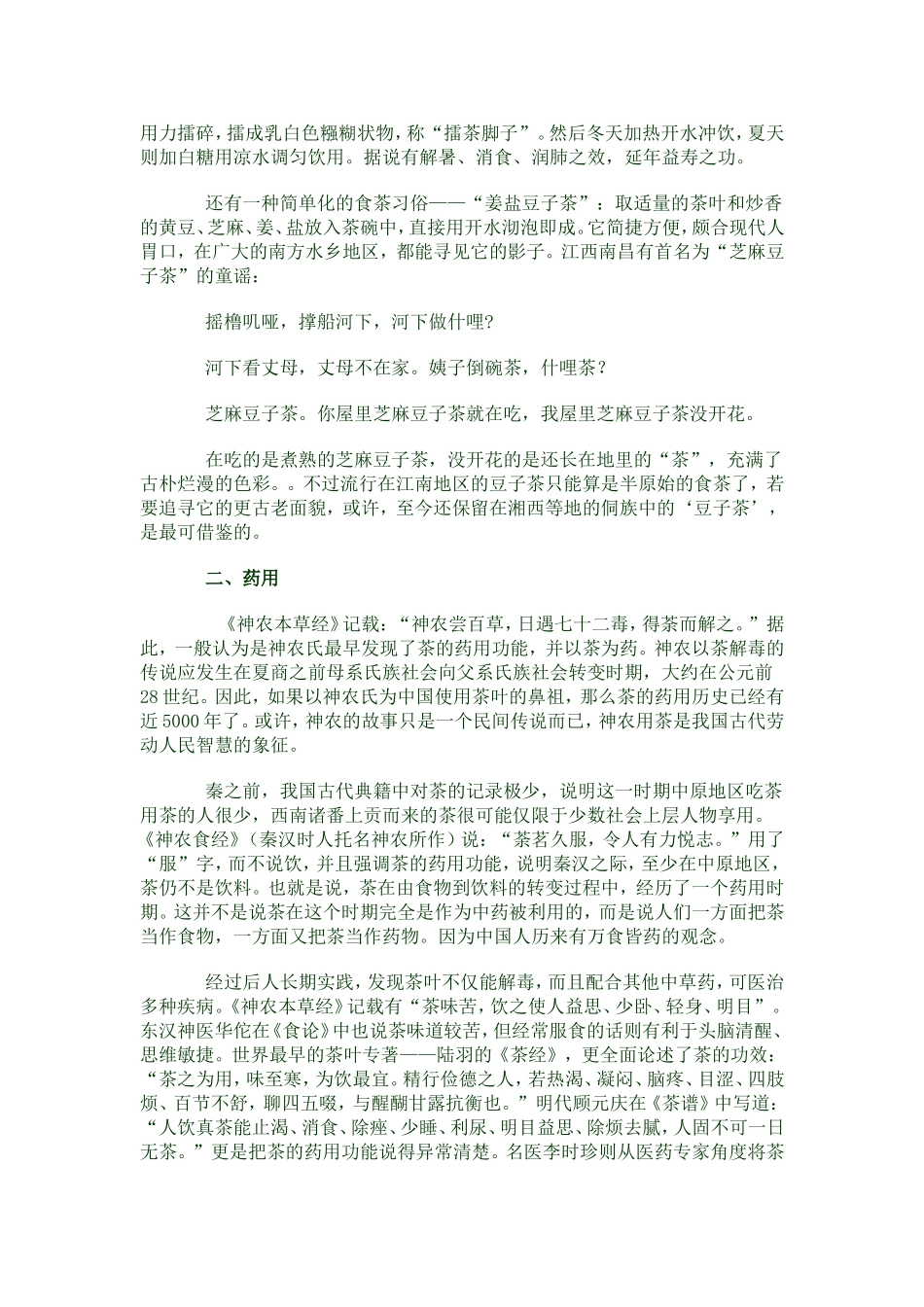第二章茶文化基础知识第一节中国用茶的源流“在我国,饮茶之始,是食饮同宗”,茶在作为饮料之前,它是被食而用之的。语言学者研究认为:在原始人的语素中,“茶”的发音意为“一切可以用来吃的植物”。我们的祖先从野生大茶树上砍下枝条,采集嫩梢,先是生嚼,后来加水煮成羹汤,服而食之。又古人有“药食同源”之说,人们在长期食用茶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它的药用功能。可见茶的药用阶段与食用阶段是交织在一起的,只不过,人们把茶从其它的食物中分离出来,是从认识到它的药用价值开始的。所以最早记载饮茶的既不是“诸子之言”,也不是史书,而是本草一类的“药书”,例如《神农本草》《食论》《本草拾遗》《本草纲目》等书中均有关于“茶”之条目。茶经历了从食用、药用到饮用的演变,三者之间有先后承启的关系,但是又不可能进行绝对划分,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哪怕是到了我们今天,茶以品饮为主,同时也是一种保健药品,云南的基诺族至今仍把茶叶凉拌了做菜吃。一、食用早期的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食物被人们用来吃的。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茶叶已经从西南地区传播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齐国(今山东境内)已出现用茶叶做成的菜肴。《晏子春秋》中就记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晏子是春秋时人,卒年在公元前500年,也就是说,茶在这个时候还是作为下饭的菜食用的。今天,仍有一些食茶的习俗保留了下来。世世代代生活在云南茶山上的一些少数民族,例如基诺族布朗族等,都有把新鲜茶叶经过简单加工做菜吃的习惯。此外,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自古以来有浓郁的吃擂茶的风习。南宋时,《都城纪胜》、《梦粱录》等史书记载,杭州“冬天兼卖擂茶”“冬月添卖七宝擂茶”,并记杭州人非常热衷于吃擂茶,由于打擂茶时很费棒杵故而当时还留下如此俗谚:“杭州人—日吃三十丈木头。”每天擂损的木棒竟然达30丈之多!这当然是夸张,但从中正可看出古时杭州人吃擂茶的风盛。现在,被认为是汉族后裔的一支的客家人,还流传着吃擂茶的习俗。客家人的擂茶是用生姜、生米、生茶叶(鲜茶叶)做成,故又名“三生汤”。实际上,“三生”也并不仅仅只有三种食物,原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故其还有“五味汤”“七宝茶”等名称。大体制法为:先将茶叶、芝麻放人特制的陶擂钵中,以茶子木或山楂木作杵不断擂磨,再将用水浸泡过的黄豆、绿豆、花生、米等加入其中,并放适量凉开水,用力擂碎,擂成乳白色糨糊状物,称“擂茶脚子”。然后冬天加热开水冲饮,夏天则加白糖用凉水调匀饮用。据说有解暑、消食、润肺之效,延年益寿之功。还有一种简单化的食茶习俗——“姜盐豆子茶”:取适量的茶叶和炒香的黄豆、芝麻、姜、盐放入茶碗中,直接用开水沏泡即成。它简捷方便,颇合现代人胃口,在广大的南方水乡地区,都能寻见它的影子。江西南昌有首名为“芝麻豆子茶”的童谣:摇橹叽哑,撑船河下,河下做什哩?河下看丈母,丈母不在家。姨子倒碗茶,什哩茶?芝麻豆子茶。你屋里芝麻豆子茶就在吃,我屋里芝麻豆子茶没开花。在吃的是煮熟的芝麻豆子茶,没开花的是还长在地里的“茶”,充满了古朴烂漫的色彩。。不过流行在江南地区的豆子茶只能算是半原始的食茶了,若要追寻它的更古老面貌,或许,至今还保留在湘西等地的侗族中的‘豆子茶’,是最可借鉴的。二、药用《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据此,一般认为是神农氏最早发现了茶的药用功能,并以茶为药。神农以茶解毒的传说应发生在夏商之前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8世纪。因此,如果以神农氏为中国使用茶叶的鼻祖,那么茶的药用历史已经有近5000年了。或许,神农的故事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而已,神农用茶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秦之前,我国古代典籍中对茶的记录极少,说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吃茶用茶的人很少,西南诸番上贡而来的茶很可能仅限于少数社会上层人物享用。《神农食经》(秦汉时人托名神农所作)说:“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用了“服”字,而不说饮,并且强调茶的药用功能,说明秦汉之际,至少在中原地区,茶仍不是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