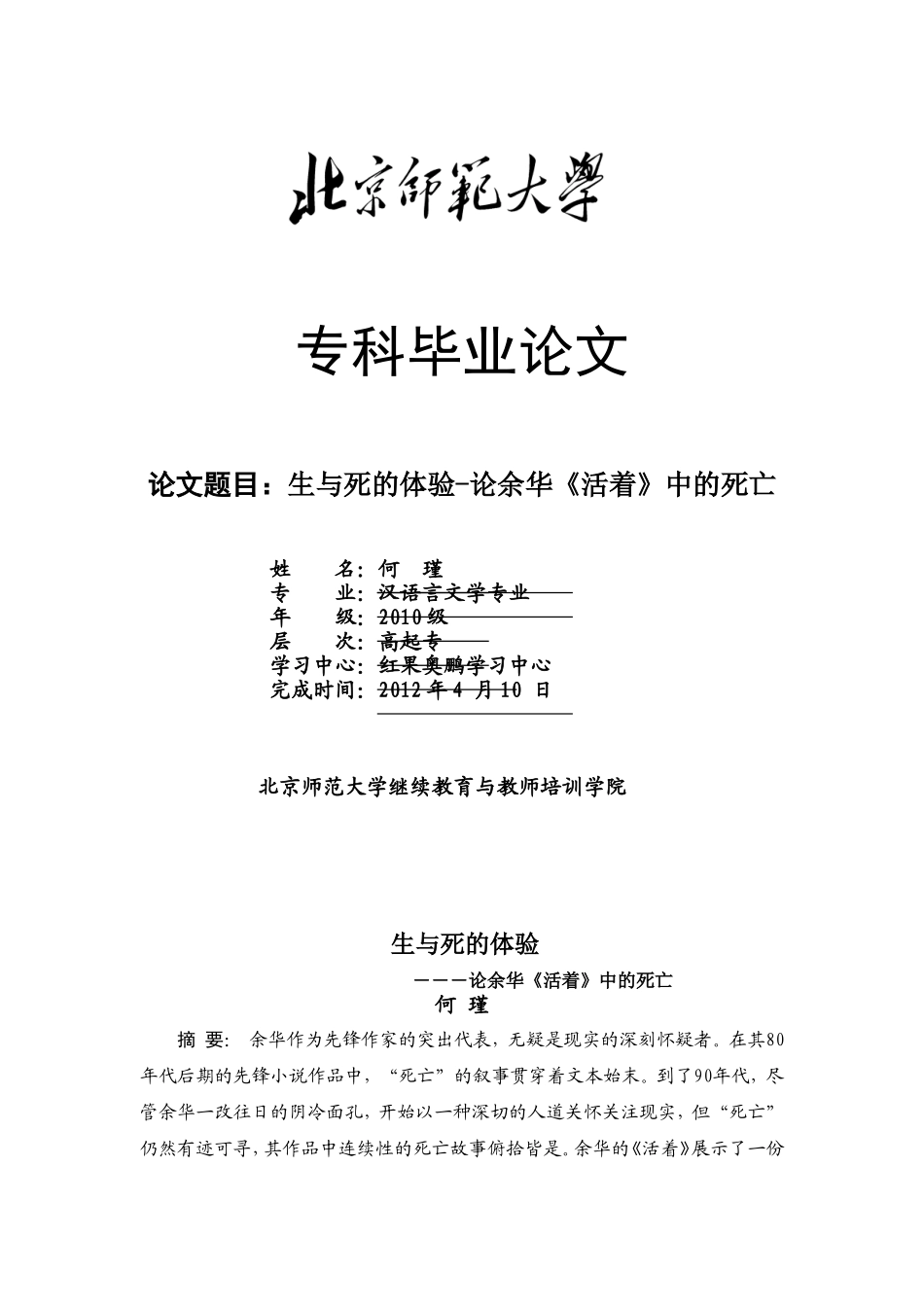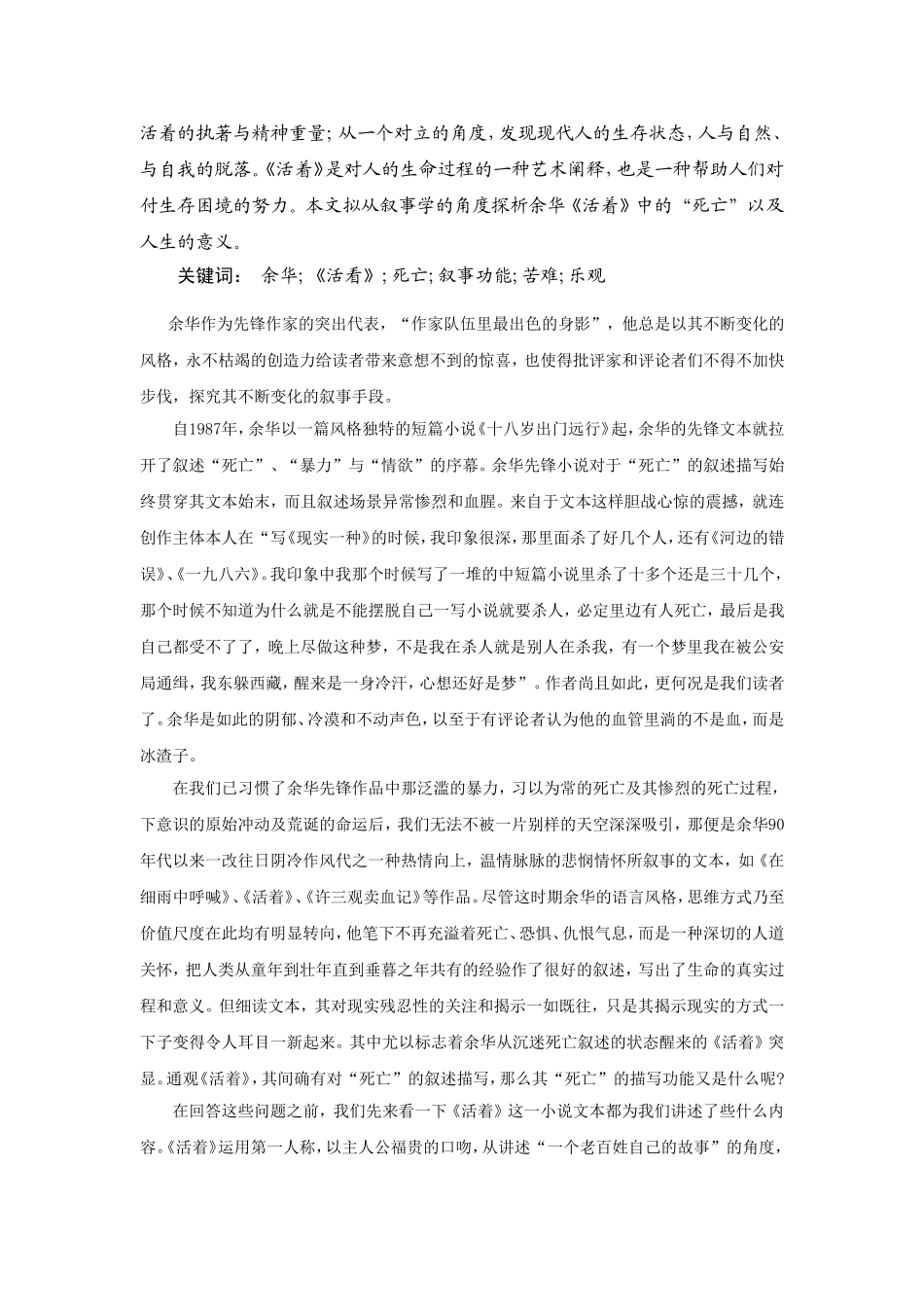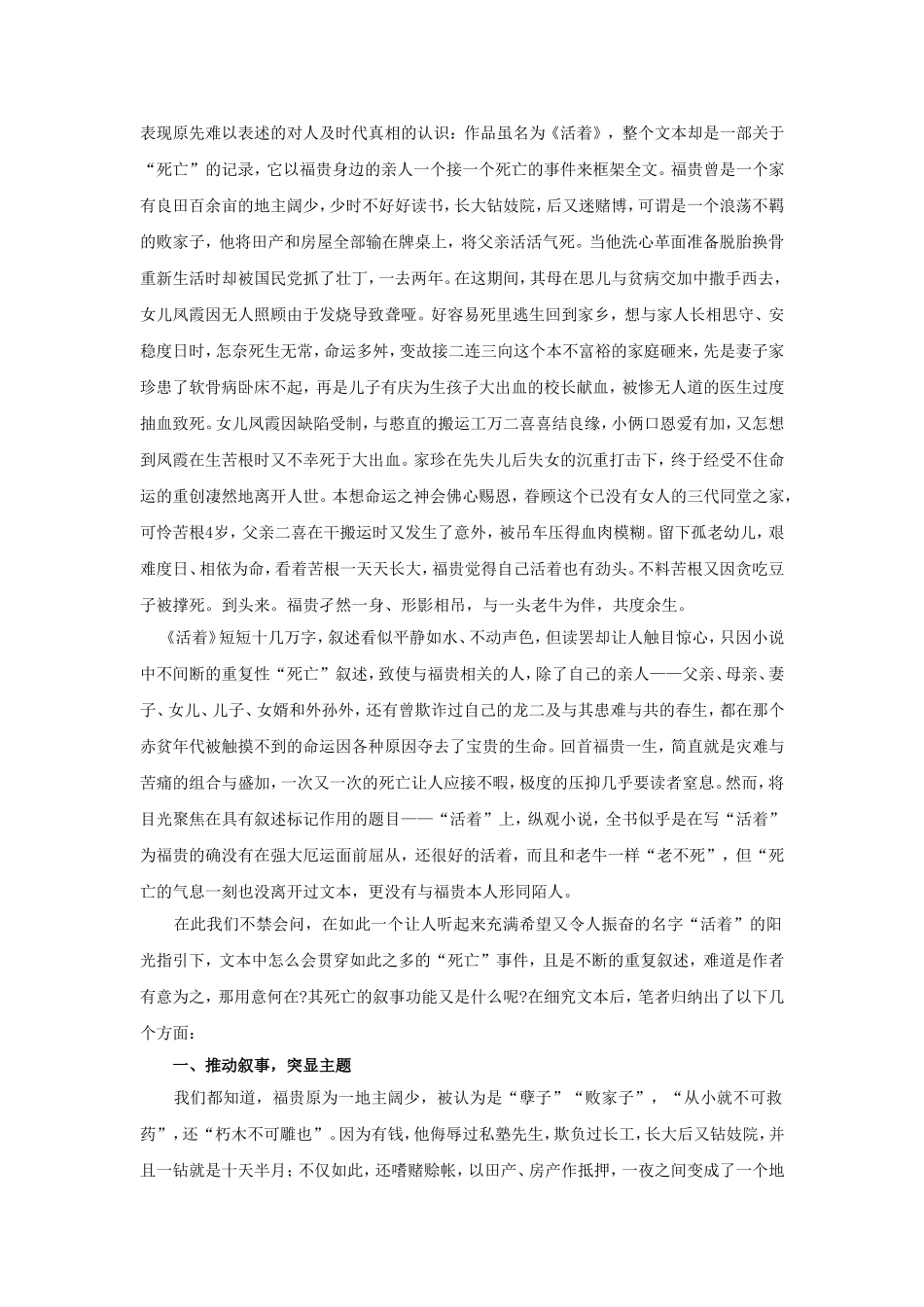专科毕业论文论文题目:生与死的体验-论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姓名:何瑾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年级:2010级层次:高起专学习中心:红果奥鹏学习中心完成时间:2012年4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生与死的体验―――论余华《活着》中的死亡何瑾摘要:余华作为先锋作家的突出代表,无疑是现实的深刻怀疑者。在其80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品中,“死亡”的叙事贯穿着文本始末。到了90年代,尽管余华一改往日的阴冷面孔,开始以一种深切的人道关怀关注现实,但“死亡”仍然有迹可寻,其作品中连续性的死亡故事俯拾皆是。余华的《活着》展示了一份活着的执著与精神重量;从一个对立的角度,发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与自然、与自我的脱落。《活着》是对人的生命过程的一种艺术阐释,也是一种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探析余华《活着》中的“死亡”以及人生的意义。关键词:余华;《活看》;死亡;叙事功能;苦难;乐观余华作为先锋作家的突出代表,“作家队伍里最出色的身影”,他总是以其不断变化的风格,永不枯竭的创造力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也使得批评家和评论者们不得不加快步伐,探究其不断变化的叙事手段。自1987年,余华以一篇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起,余华的先锋文本就拉开了叙述“死亡”、“暴力”与“情欲”的序幕。余华先锋小说对于“死亡”的叙述描写始终贯穿其文本始末,而且叙述场景异常惨烈和血腥。来自于文本这样胆战心惊的震撼,就连创作主体本人在“写《现实一种》的时候,我印象很深,那里面杀了好几个人,还有《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我印象中我那个时候写了一堆的中短篇小说里杀了十多个还是三十几个,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摆脱自己一写小说就要杀人,必定里边有人死亡,最后是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晚上尽做这种梦,不是我在杀人就是别人在杀我,有一个梦里我在被公安局通缉,我东躲西藏,醒来是一身冷汗,心想还好是梦”。作者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我们读者了。余华是如此的阴郁、冷漠和不动声色,以至于有评论者认为他的血管里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在我们已习惯了余华先锋作品中那泛滥的暴力,习以为常的死亡及其惨烈的死亡过程,下意识的原始冲动及荒诞的命运后,我们无法不被一片别样的天空深深吸引,那便是余华90年代以来一改往日阴冷作风代之一种热情向上,温情脉脉的悲悯情怀所叙事的文本,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尽管这时期余华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乃至价值尺度在此均有明显转向,他笔下不再充溢着死亡、恐惧、仇恨气息,而是一种深切的人道关怀,把人类从童年到壮年直到垂暮之年共有的经验作了很好的叙述,写出了生命的真实过程和意义。但细读文本,其对现实残忍性的关注和揭示一如既往,只是其揭示现实的方式一下子变得令人耳目一新起来。其中尤以标志着余华从沉迷死亡叙述的状态醒来的《活着》突显。通观《活着》,其间确有对“死亡”的叙述描写,那么其“死亡”的描写功能又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活着》这一小说文本都为我们讲述了些什么内容。《活着》运用第一人称,以主人公福贵的口吻,从讲述“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角度,表现原先难以表述的对人及时代真相的认识:作品虽名为《活着》,整个文本却是一部关于“死亡”的记录,它以福贵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亡的事件来框架全文。福贵曾是一个家有良田百余亩的地主阔少,少时不好好读书,长大钻妓院,后又迷赌博,可谓是一个浪荡不羁的败家子,他将田产和房屋全部输在牌桌上,将父亲活活气死。当他洗心革面准备脱胎换骨重新生活时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去两年。在这期间,其母在思儿与贫病交加中撒手西去,女儿凤霞因无人照顾由于发烧导致聋哑。好容易死里逃生回到家乡,想与家人长相思守、安稳度日时,怎奈死生无常,命运多舛,变故接二连三向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砸来,先是妻子家珍患了软骨病卧床不起,再是儿子有庆为生孩子大出血的校长献血,被惨无人道的医生过度抽血致死。女儿凤霞因缺陷受制,与憨直的搬运工万二喜喜结良缘,小俩口恩爱有加,又怎想到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