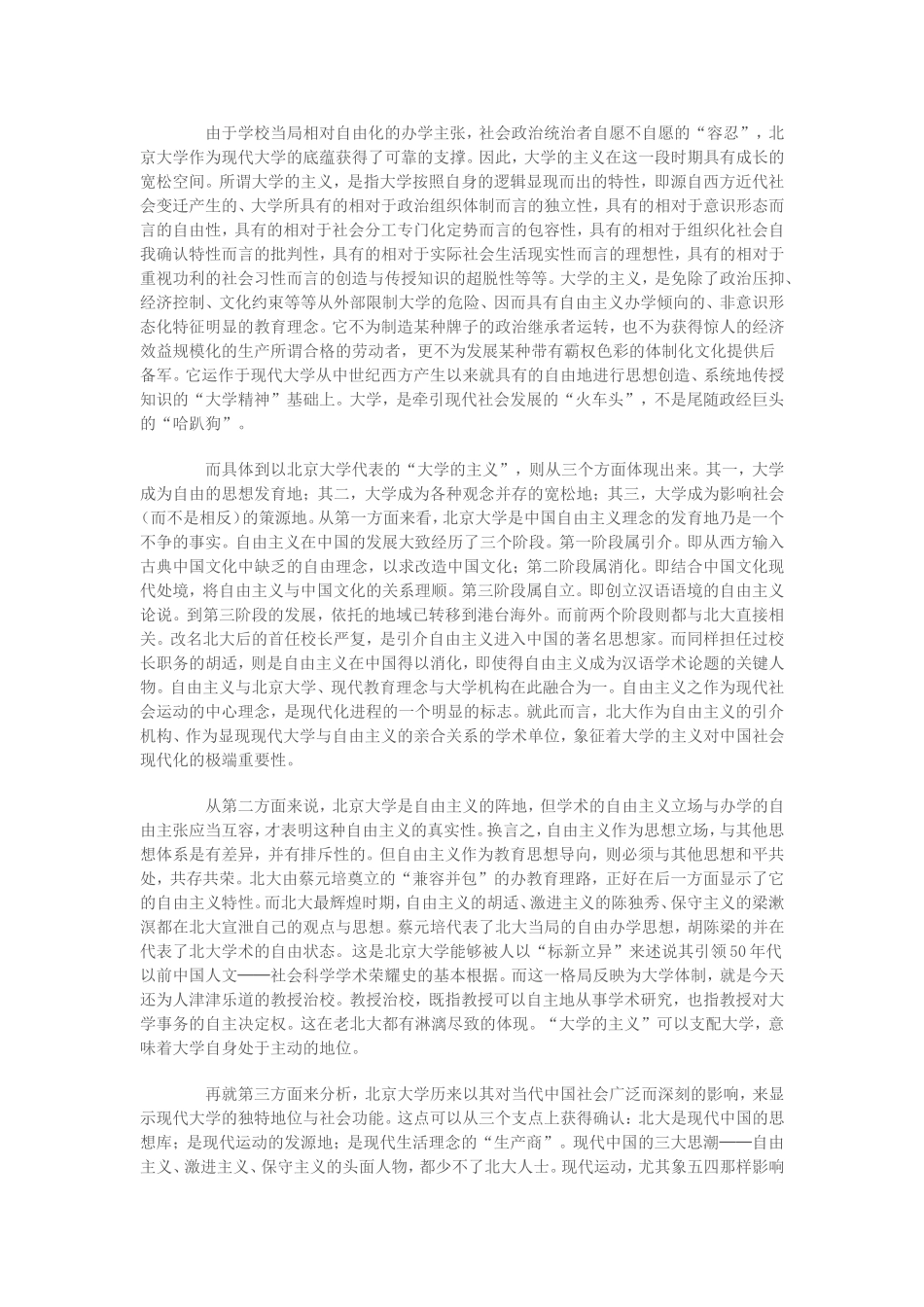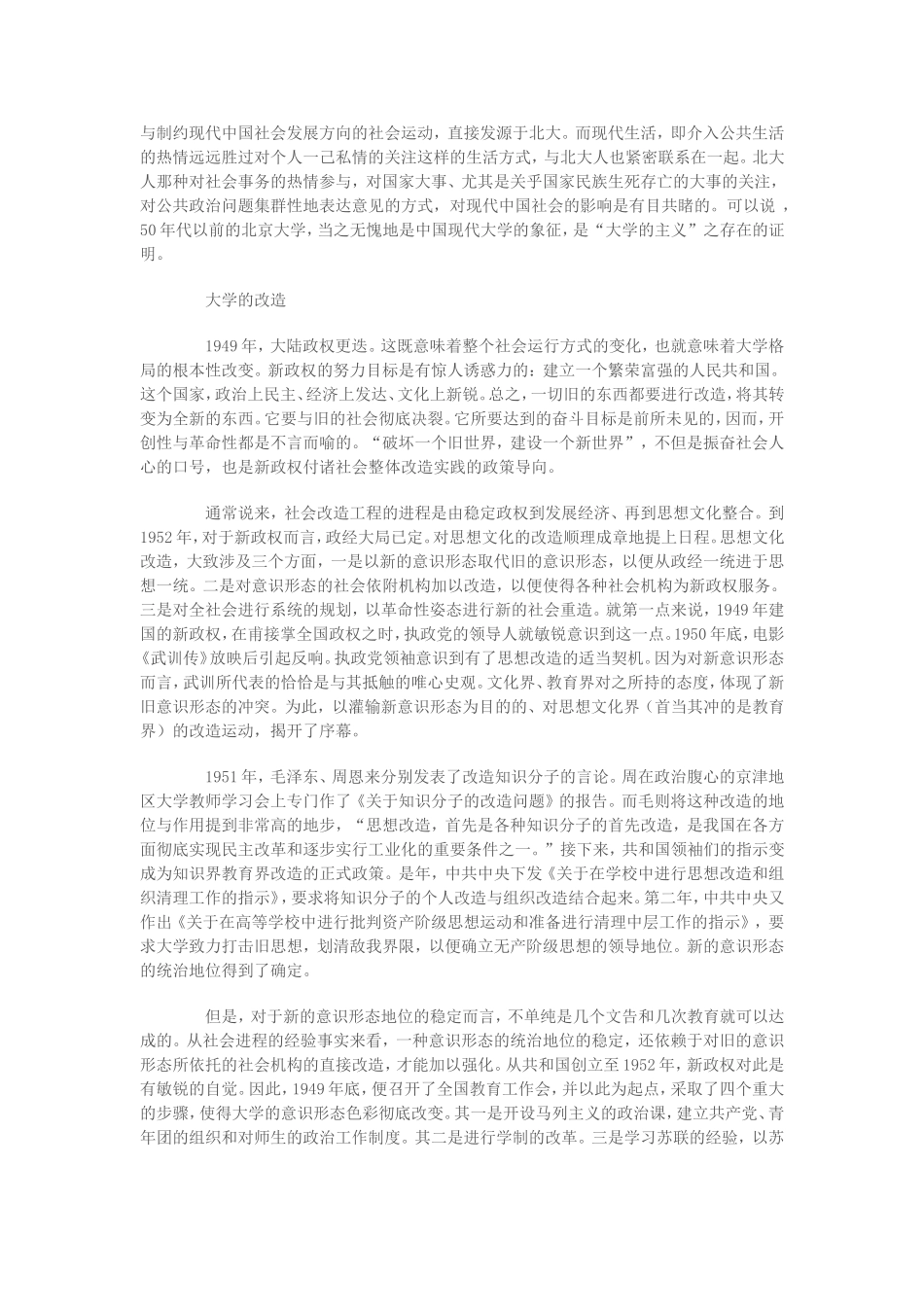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作者:任剑涛来源:南风窗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整整100年历程。因此,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大学诞生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百年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恰恰与百年中国大学不平坦的成长相映成趣。在此,北京大学百年就与现代中国发生了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一所大学与一个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而这一社会和这所大学都有如此之多令人反思的地方,因而,解读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可以合理地视为解读现代中国大学史、解读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史。考虑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后发外生的,这一特性注定了一切“现代的”东西进入中国,都得有一个思想上的再验证、介入社会运动之时的有用性检验问题,故尔,一种思想是否能在社会变迁中获得广泛认同与支持,就与其能否经受得起思想检验与社会筛选直接相关。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需求、现代教育思想的产物,大学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变迁过程中能否显现而出,便要看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大学实践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是否获得了自证其合理性的依据。为此,我们得思考大学“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而社会、尤其是社会统治者又想大学成为一个什么模样,从而,在大学与社会互动的边沿上,刻画中国大学精神形成及其演变的过程。而北京大学,正是窥见中国大学这只全豹的“一斑”。大学的主义:老北大的底蕴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所学校究竟要建设成一个样子,就已由京师大学堂这一“新政”措施出台有关的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进行了设计,基本精神从八个字上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而且他从四方面分疏了这一中国最初的大学理念。一者从鼓舞国民士气、维新图强出发,新学校的开办比旧科举要为优,而且是“急补养以培其中气”的“最要”措施;二者古典社会以科举取代学校,人才渐少,国运亦衰;三者观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枝,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四者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举措“可急就”,但“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可见兴办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大学在定位上的特殊性。而大学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区别、与以“学”即思想与知识为象征性标志的独特性,在康有为处已得到清晰认知。京师大学堂在度过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正式称为北京大学之前,学校当局就明确强调学校的基本精神是“为国求学”,对学生的的要求则是“努力自爱”。如果说这为北京大学奠定了办学方向,那么,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尤其是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便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机制,则有保护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后者就是为今天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所赞不绝口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办学思想。这一思路,为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局所继承。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学校当局相对自由化的办学主张,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蕴获得了可靠的支撑。因此,大学的主义在这一段时期具有成长的宽松空间。所谓大学的主义,是指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大学的主义,是免除了政治压抑、经济控制、文化约束等等从外部限制大学的危险、因而具有自由主义办学倾向的、非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