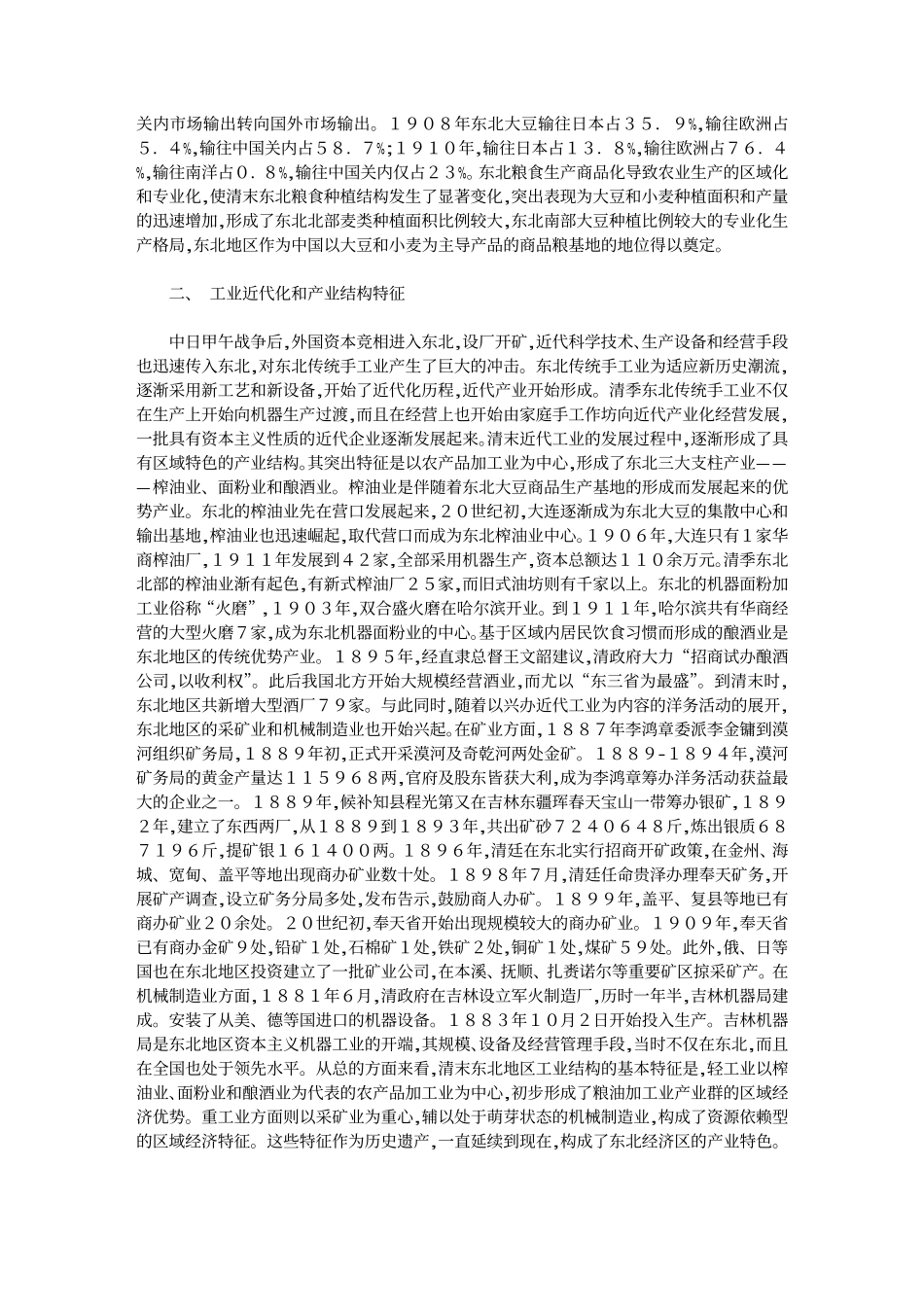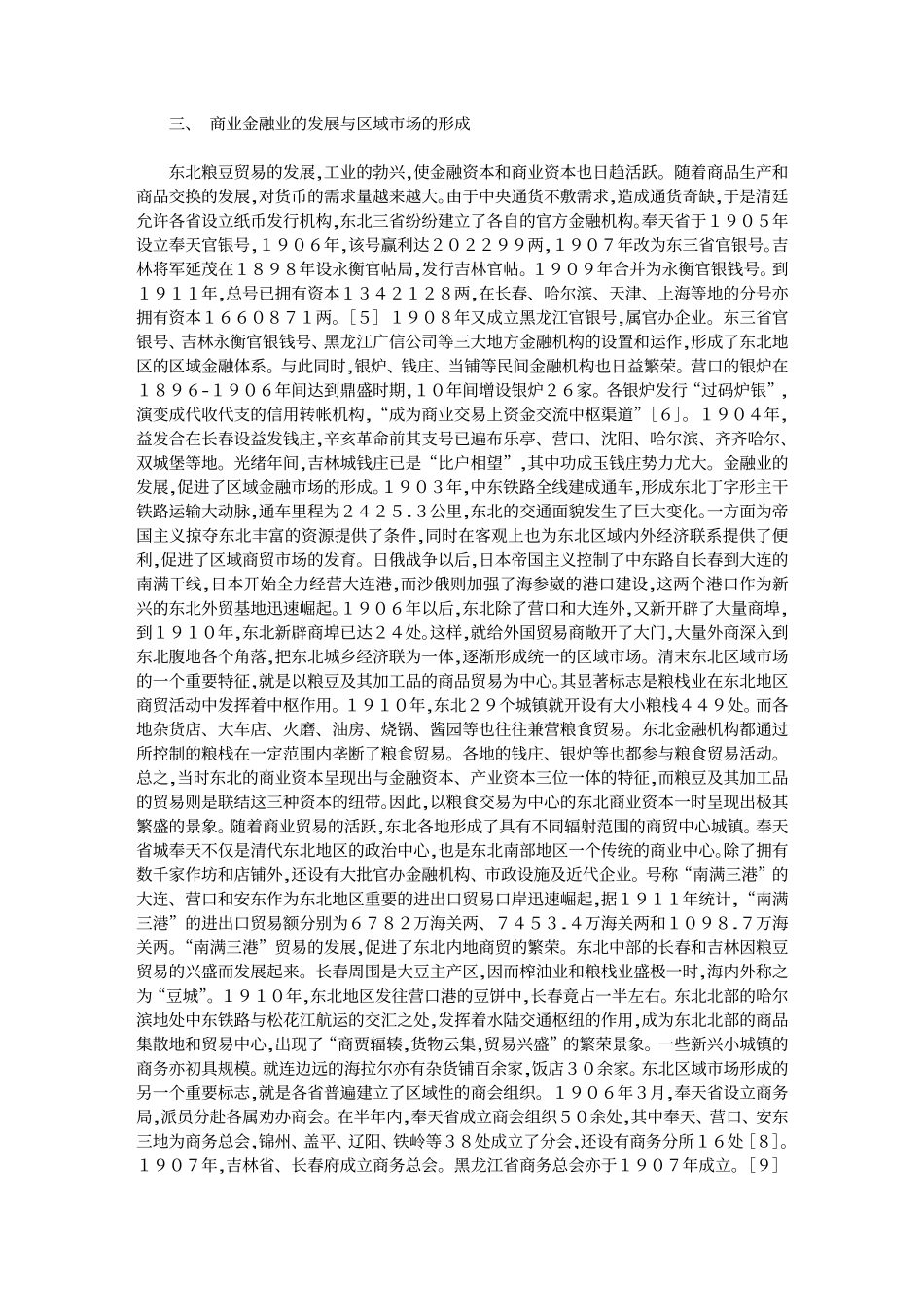论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成衣保中东北经济区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单元,既不同于自然地理区域,也不同于行政区域,而是由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等要素构成的区域共同体。区域开发是经济区形成的物质基础,而区域经济近代化,即以近代工业为基础,以近代交通为纽带,形成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才形成了具有近代含义的经济区。就东北地区而言,在古代长期处于缓慢的开发期,晚清以来,伴随着移民开发浪潮,东北经济迅速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被国内外普遍认同的经济区域。一、区域开发与商品粮基地形成曾在辽东颁行“招垦令”,鼓励关内农民出关开荒。不久又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先后设立官庄,将大批罪犯流放到吉、黑地区充作壮丁,同时派拨旗兵和站丁进入东北屯驻,开辟大片旗田。但清政府从“首崇满洲”,维护“龙兴之地”的统治利益出发,乾隆以后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划作“围场”、“牧场”、“禁山”、“蒙地”等等,禁止流民进入私垦,限制了东北的土地开发。因此,直到近代以前东北区域仍然是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边陲奥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和抵御沙俄侵略的需要出发,对东北的封禁逐渐放松,东北移民迅速增加。据统计,从1850年到1910年,东北人口由289.8万人增长为2158.2万人,60年间净增人口1868.4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山东、河北移来的农民。移民的增加和清政府的弛禁放垦政策,促进了东北的土地开发。1857年后奉天地区各牧场、围场及封禁地陆续对垦民开放。据统计,到清末民初,奉天全省垦地面积已达6822.6万亩,吉林省垦地面积达493.2万垧,黑龙江省亦达211万垧。[1]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加,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据1908年调查,东北五大主粮年产量总和为800多万吨。1911年,吉、黑两省粮食产量亦已达101.5亿斤,人均粮食达1200多斤。清末东北出现了很多粮食剩余的州县。例如绥中县盛产粮食,谚云:“填不满的山海关,拉不败的中后所(即绥中县)。”[2]每年输出粮食5万石,花生5万斤,豆饼7万块。东北地区每年向市场提供大量的商品粮,粮食的商品率迅速提高,从各种资料反映的综合情况看,清末东北的粮食商品率在30-40%左右。辽东在乾嘉年间,也曾有部分粮食运往关内。但当时辽东是清朝“陪都”盛京的所在地,王公大臣聚集之处,农产品主要用于供奉王公贵族、八旗驻兵及官府衙门,剩余部分十分有限。清政府为了保障盛京地区粮食供给,对“奉天、直隶海船往来,贩运米豆杂粮,向有例禁”,[3]限制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致使辽东农业长期处于封建自然经济状态。1861年牛庄(营口)开港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东北渗透。1863年清政府被迫开放“豆禁”,下令“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4]“豆禁”开放后,大量外轮进入营口。外商参与东北粮豆运输和贸易后,营口大豆、豆饼、豆油的输出量逐年增加,1864年为166.5万担,1867年增为216.2万担。1869年,清政府又解除了将大豆运往外国的禁令,从此东北大豆不仅运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开始向日本、香港、南洋等地输出,东北的粮豆市场进一步扩大,输出量也日益增加。1875年,营口大豆的输出量为275.9万担,1891年已达731.4万担。1908年,东北大豆在英国试销成功,同年沙俄纳坦索公司将东北大豆、小麦等粮谷5000吨输往美国,哈尔滨粮食交易所也在同年将在东北购买的1000吨大豆销往敖得萨。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也先后取消对东北大豆进口的限制。从此,东北大豆对欧美的输出明显增加,东北粮食生产迅速被纳入世界市场中。此后,东北的大豆三品输出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很快由向关内市场输出转向国外市场输出。1908年东北大豆输往日本占35.9%,输往欧洲占5.4%,输往中国关内占58.7%;1910年,输往日本占13.8%,输往欧洲占76.4%,输往南洋占0.8%,输往中国关内仅占23%。东北粮食生产商品化导致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使清末东北粮食种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为大豆和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的迅速增加,形成了东北北部麦类种植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