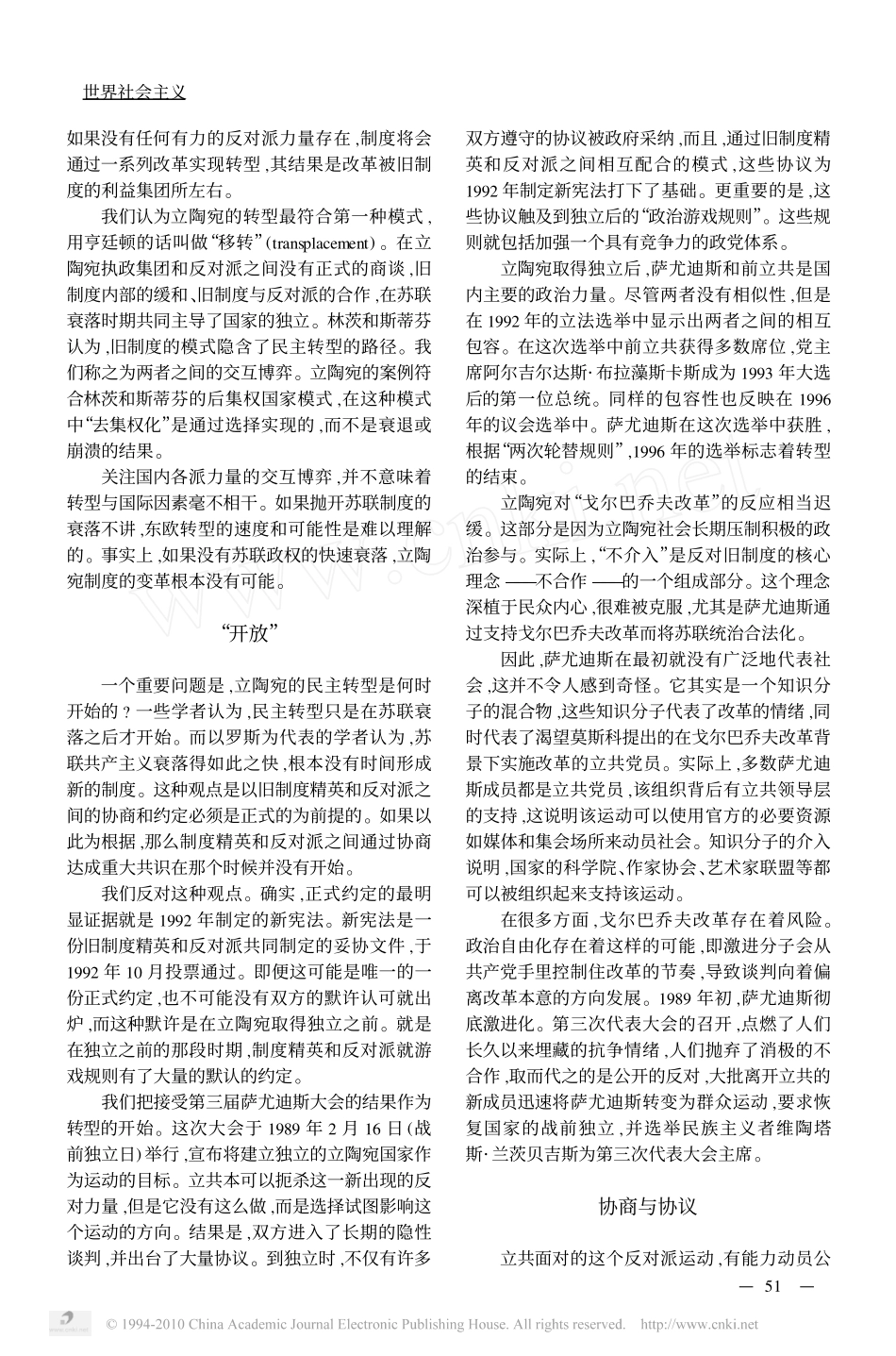透视立陶宛共产党继承党[美]特里·D.克拉克[立陶宛]霍维塔·普拉耐维秋特王新颖编译在后苏联时期,立陶宛共产党继承党一直是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该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重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苏联时期的制度类型:民族共产主义?虽然有1941年德国迫使苏联红军撤离立陶宛这样一段插曲,但立陶宛从1940年到1991年一直都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立共作为莫斯科的代理,保证苏联统治贯穿始终。立共对其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充满戒备,压制任何反对意见。党的第一任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克库斯从1940年8月到1974年1月在任期间,将大批立陶宛人流放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并残酷镇压阻挠苏联对立陶宛农村实施有效控制的武装起义。其结果是立陶宛社会变成一个权力等级结构明显的社会,处于权力顶峰的是立共。同时,斯涅克库斯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上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由于他的努力,立陶宛成为唯一一个免于对老共产党员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共和国。他在民族和文化认同上也争取了一定的自治权。他最大的成功是阻挠了对立陶宛的苏联化,放缓了中央计划者对立陶宛进行工业化的企图。立共领导人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中开拓出一条“民族共产主义”的路径。立共在服从最高指示的同时,也在寻求最大程度的文化自治可能。立共不遗余力地保护立陶宛文化免于苏联化,因此经常被批评为经济沙文主义、教育和文化民族主义。苏联时期的反对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涅克库斯绕开莫斯科指令的成功战略却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去斯大林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事实上,立陶宛的反制度力量比苏联其他地区都要强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两股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不同性质的地下组织,它们均反对文化“种族灭绝”,并宣称国家1940年并入苏联的条约是非法条约。还有一类民族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支持更广泛的宗教表达自由,很少关心政治独立,认同天主教会。与民族主义者相同,自由派反对俄罗斯化、支持民族文化的复兴。然而,他们习惯性地对苏联占领避而不谈,而是将他们的批判指向苏联体制的失败,要求给予少数民族文化以权利,同时要求苏联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们的首个非法出版物《透视》(Perspektyvos)表达了这一立场,这份左派杂志促进了一个“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政见者运动深受国际事件的影响。东德和保加利亚1953年危机、匈牙利1956年危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危机、波兰1980—1981年的危机,都给立陶宛带来公开反对苏联制度的浪潮。就在不同政见者公开表示反抗的同时,对制度形成真正威胁的实际是广大民众以不合作的态度所表达出来的消极抵制,包括不参加苏联庆典、拒绝行政职位、拒绝参加社会组织。另外,不合作的行动还表现在非法出版物无处不在上。立陶宛从共产主义的转型关于民主转型的一些重要文献认为,集权主义的终结是由精英驱动的,转型的模式影响随后创建的制度和机制。许多学者认为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开启了政治自由化的可能。反对派的力量和作用是转型模式的关键,这种集权统治塑造了随后出现的政治制度框架。普遍的观点认为,反对派的力量越强,转型就越有可能商议和妥协,就越有可能出现旧制度精英与代表反对旧制度的公民社会的精英对立者之间的约定。这种约定反映了对权力共享的安排,确保制度的实施兼顾各党利益并达到政府内彼此相互制衡。但是,如果反对派过于强大,压制了旧制度,那么转型将会是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而没有约定和妥协的可能。—05—《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9年第5期如果没有任何有力的反对派力量存在,制度将会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转型,其结果是改革被旧制度的利益集团所左右。我们认为立陶宛的转型最符合第一种模式,用亨廷顿的话叫做“移转”(transplacement)。在立陶宛执政集团和反对派之间没有正式的商谈,旧制度内部的缓和、旧制度与反对派的合作,在苏联衰落时期共同主导了国家的独立。林茨和斯蒂芬认为,旧制度的模式隐含了民主转型的路径。我们称之为两者之间的交互博弈。立陶宛的案例符合林茨和斯蒂芬的后集权国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去集权化”是通过选择实现的,而不是衰退或崩溃的结果。关注国内各派力量的交互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