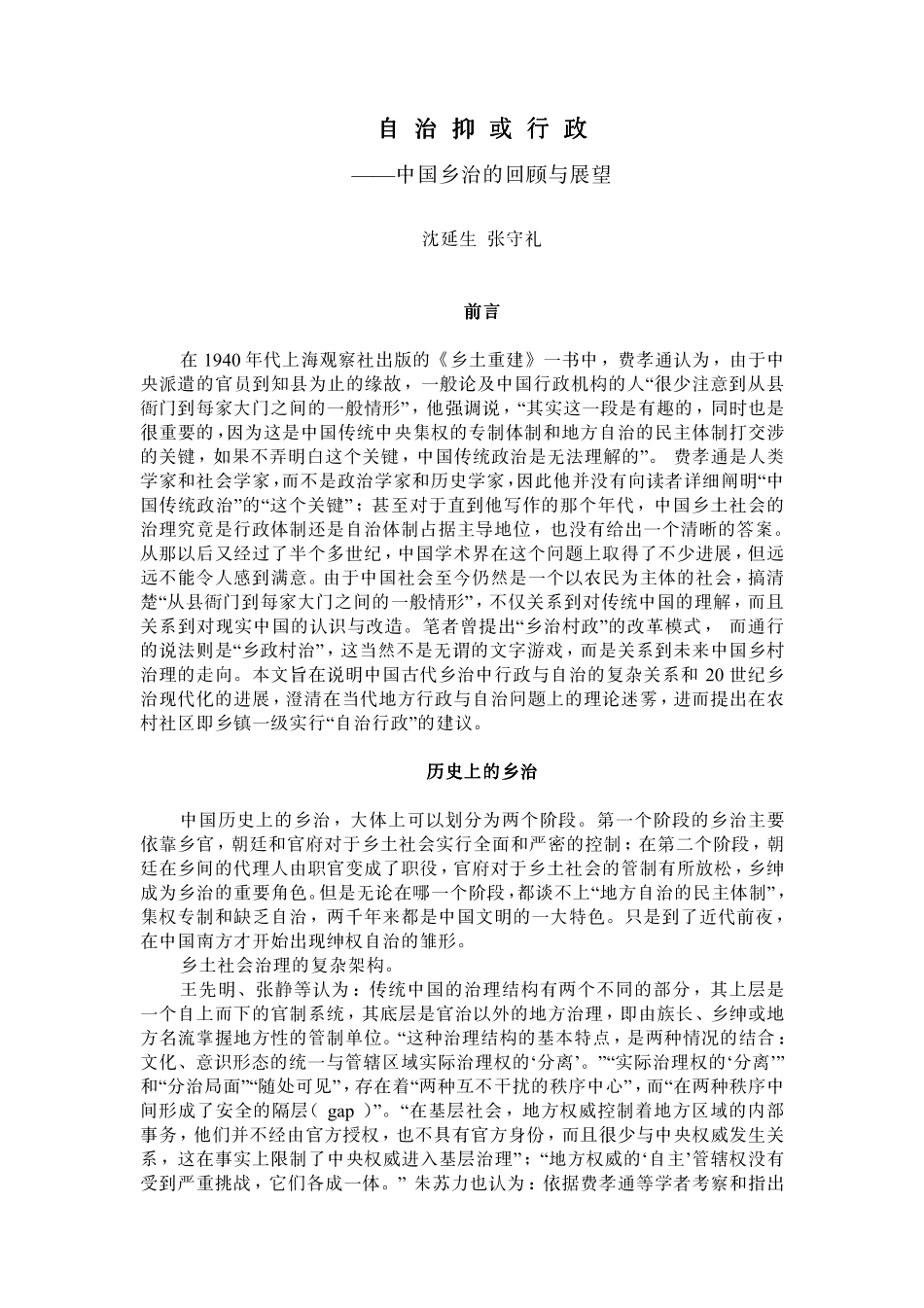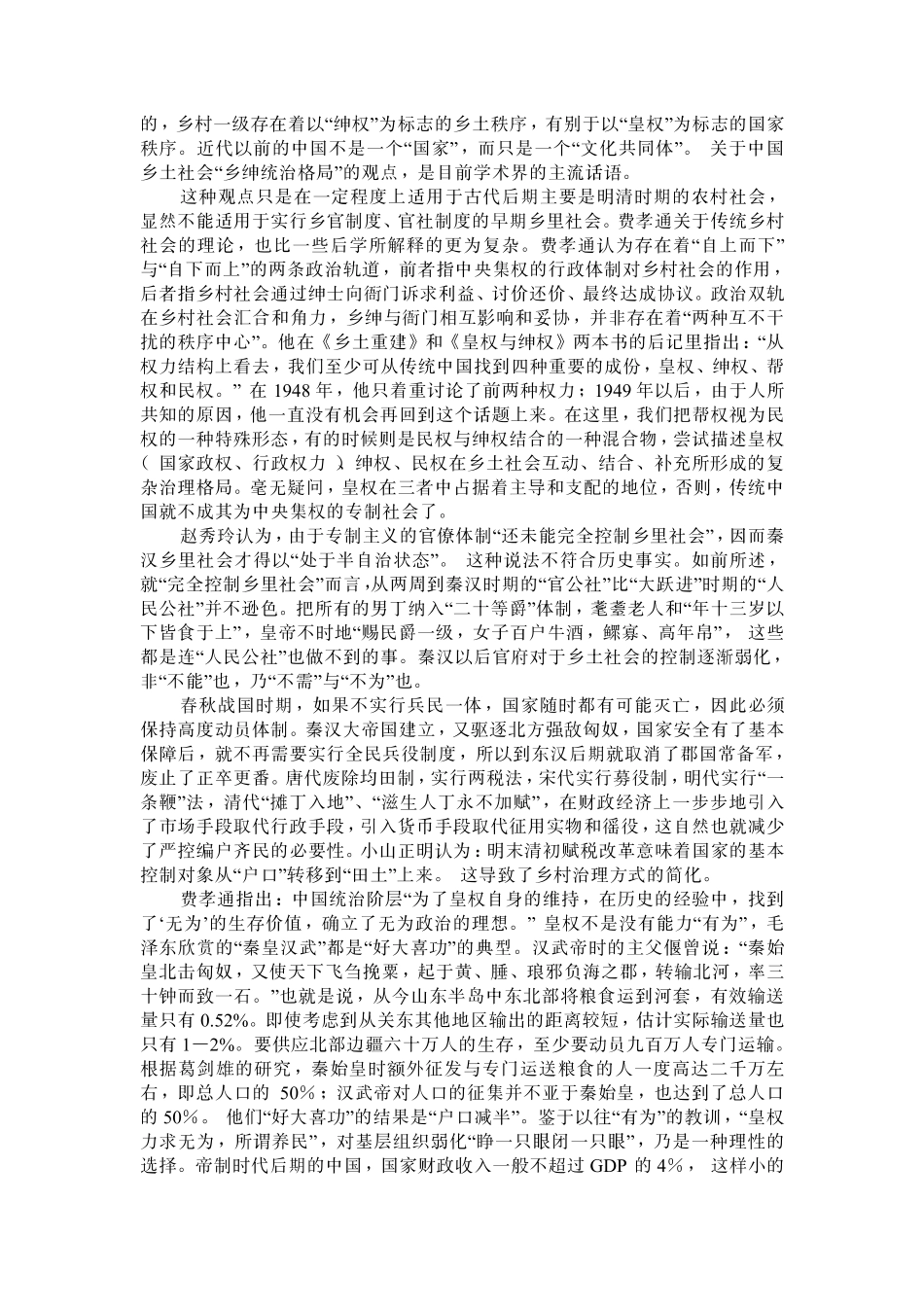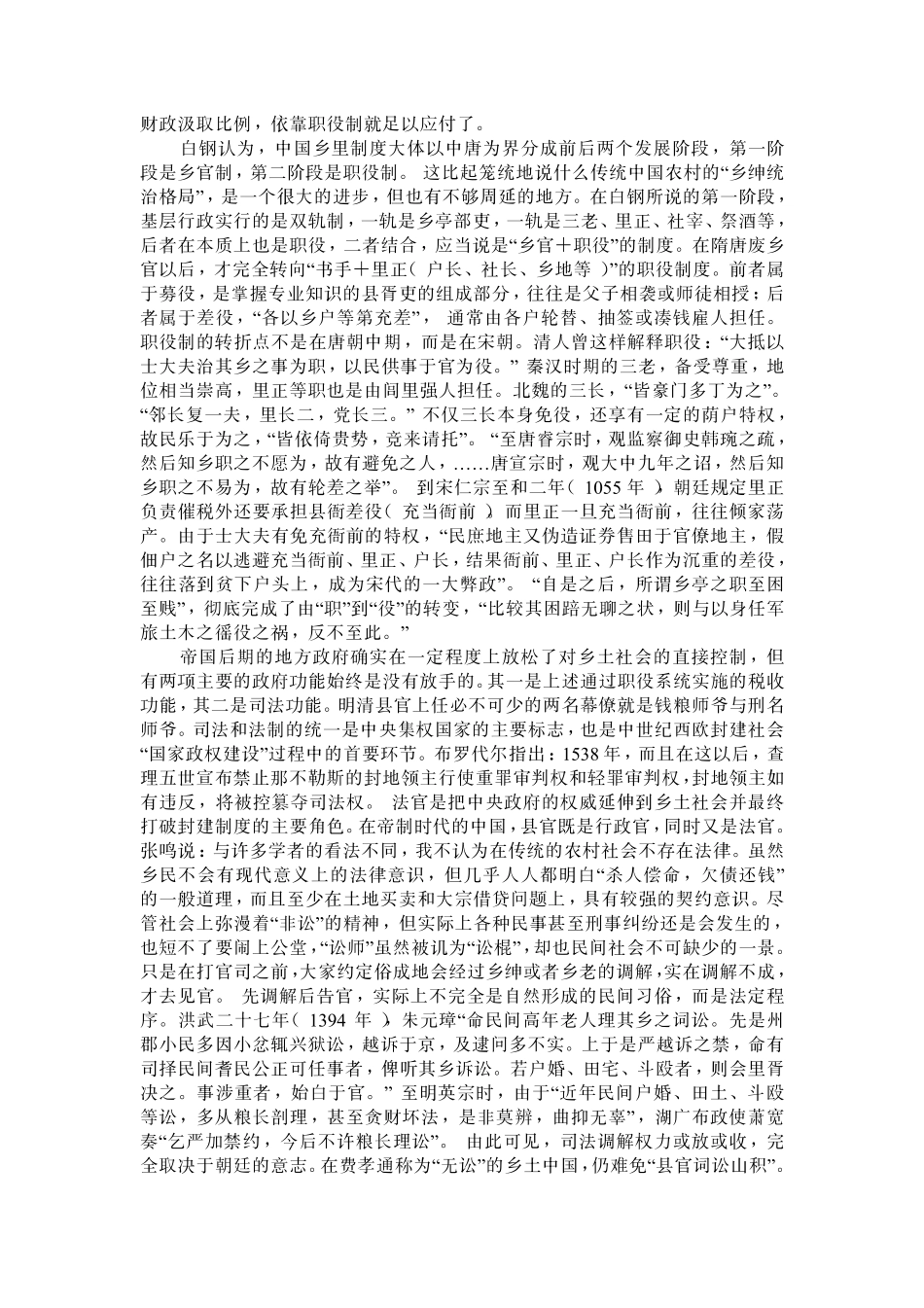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抑抑抑抑或或或或行行行行政政政政——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沈延生张守礼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在1940年代上海观察社出版的《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认为,由于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的缘故,一般论及中国行政机构的人“很少注意到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他强调说,“其实这一段是有趣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如果不弄明白这个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费孝通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他并没有向读者详细阐明“中国传统政治”的“这个关键”;甚至对于直到他写作的那个年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治理究竟是行政体制还是自治体制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远远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由于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搞清楚“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不仅关系到对传统中国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现实中国的认识与改造。笔者曾提出“乡治村政”的改革模式,而通行的说法则是“乡政村治”,这当然不是无谓的文字游戏,而是关系到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的走向。本文旨在说明中国古代乡治中行政与自治的复杂关系和20世纪乡治现代化的进展,澄清在当代地方行政与自治问题上的理论迷雾,进而提出在农村社区即乡镇一级实行“自治行政”的建议。历史上的乡治历史上的乡治历史上的乡治历史上的乡治中国历史上的乡治,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乡治主要依靠乡官,朝廷和官府对于乡土社会实行全面和严密的控制;在第二个阶段,朝廷在乡间的代理人由职官变成了职役,官府对于乡土社会的管制有所放松,乡绅成为乡治的重要角色。但是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集权专制和缺乏自治,两千年来都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只是到了近代前夜,在中国南方才开始出现绅权自治的雏形。乡土社会治理的复杂架构。王先明、张静等认为: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上层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底层是官治以外的地方治理,即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地方性的管制单位。“这种治理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两种情况的结合: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与管辖区域实际治理权的‘分离’。”“实际治理权的‘分离’”和“分治局面”“随处可见”,存在着“两种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而“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安全的隔层(gap)”。“在基层社会,地方权威控制着地方区域的内部事务,他们并不经由官方授权,也不具有官方身份,而且很少与中央权威发生关系,这在事实上限制了中央权威进入基层治理”;“地方权威的‘自主’管辖权没有受到严重挑战,它们各成一体。”朱苏力也认为:依据费孝通等学者考察和指出的,乡村一级存在着以“绅权”为标志的乡土秩序,有别于以“皇权”为标志的国家秩序。近代以前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关于中国乡土社会“乡绅统治格局”的观点,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话语。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古代后期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农村社会,显然不能适用于实行乡官制度、官社制度的早期乡里社会。费孝通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理论,也比一些后学所解释的更为复杂。费孝通认为存在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条政治轨道,前者指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对乡村社会的作用,后者指乡村社会通过绅士向衙门诉求利益、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政治双轨在乡村社会汇合和角力,乡绅与衙门相互影响和妥协,并非存在着“两种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他在《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两本书的后记里指出:“从权力结构上看去,我们至少可从传统中国找到四种重要的成份,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在1948年,他只着重讨论了前两种权力;1949年以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他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在这里,我们把帮权视为民权的一种特殊形态,有的时候则是民权与绅权结合的一种混合物,尝试描述皇权(国家政权、行政权力)、绅权、民权在乡土社会互动、结合、补充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