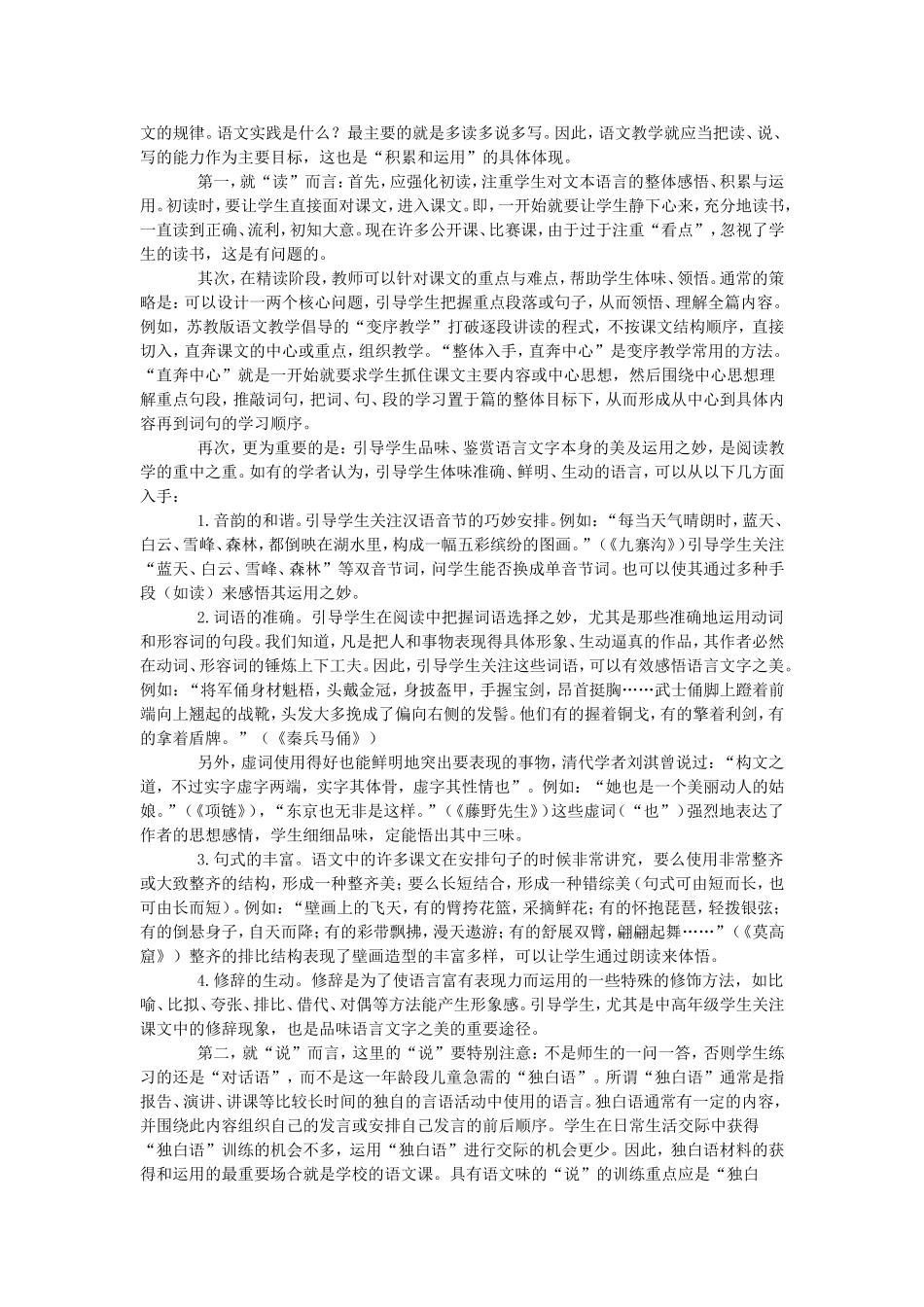再谈语文教学的“语文味”当下,不少教师都在谈语文的回归,谈本色语文、本味语文、语文味。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语文味”呢?又如何体现“语文味”呢?在作者看来,许多教师似乎就把“言语训练”当成语文味的突出表现,甚至是主要的、唯一的表现,这是有问题的。针对这一现象,作者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并且给出了我们明确的指示。“语文味”问题是语文教学中的老问题,但是近几年来,由于人们对语文性质认识的模糊,在教学中过分强调“人文性”的一面,淡化了语文的“工具性”,导致语文教学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因此,回归语文的本味,强调本味语文、本色语文的呼声日渐高涨,追求语文教学的“语文味”成为当下一道突出的风景线。然而,“语文味”难道就是“语言训练”吗?究竟怎样完整地理解“语文味”?本文试图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一、“语文味”辨析所谓“语文味”,实质上是要求语文教学体现“语文学科”(而不是其他学科)的本质,体现语文学科的主要或核心特色。那么,如何理解“语文味”呢?它的“要素”包括哪些方面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首先要回到原点,即首先要理解语文、语文学科(教学)、语文课程性质等问题。中国独立的“语文教育”并不是自古就有,在古代,语文教育是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教育融合在一起的,识字、作文与研习儒家经典结合在一起,仅仅是读经的工具和手段,德、才、学、识、能等都纳入“四书”“五经”“六艺”等学习之中。可见,“语文”当初的“根”是扎在“综合”土壤之中的,即是扎在具有综合意义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的。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语文始独立设科。在此后颁布的壬戌学制中,语文学科在小学、初中称“国语”,在高中称“国文”。在1942年,叶圣陶就指出“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关于“语文”,有不同的理解,经典的或主流的理解是“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的观点:叶老认为:“什么叫语文?平常说口语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吕叔湘对此也作过明确的解释:“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口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文字’是‘书面语’的意思,这样看来,语文教学就是‘口语’和‘书面语’的教学。”据此,“语文教学”就是指以语文教材与课外读物等文字材料中规范的言语,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教学。语言教学是整个语文教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形式的语文教学都必须以语言实践为主体,为归宿。上述阐述实际上表明的是“语文学科”基本性质的一个方面——工具性。所谓工具性,叶老认为“语文是工具”,这个“工具”既是生活的工具,又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其他学科的工具(基础),还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工具(终级目标)。这里有必要指出:体现语文“工具性”的“语文味”不仅仅是“语言实践”之“言语训练”,不仅仅是听说读写、品词析句等训练,它还应当包括“思维训练”,也就是说,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点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尤其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由于过分强调“小语”姓“小”而形成的“浅化现象”,教的都是那些“一望便知”的东西,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从某种角度讲,学生的精神成长史就是其思维发展史,思维发展是学生发展的核心。因此,注重课堂的“文化含量”(思想力量)和“思维含量”(思维训练、思维深度),注重课程资源的整合,力求“为学生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钱理群语)应是语文“本体价值”的题中之义,也是“语文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小学语文课堂着重要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要素主要有形象思维(想象、联想)、分析、推理、概括、评价能力等。就像语文工具性不能忽视其思维性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语文这个工具在用来交际、思维时,是充满着思想感情的,是负载着文化的,这是语文区别于其他工具的本质特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是孤立的语音、符号系统,而是在其中积淀了这个民族的睿智、文化、精神、感情。教母语,同时也就在教民族的文化、思想、感情,因为“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