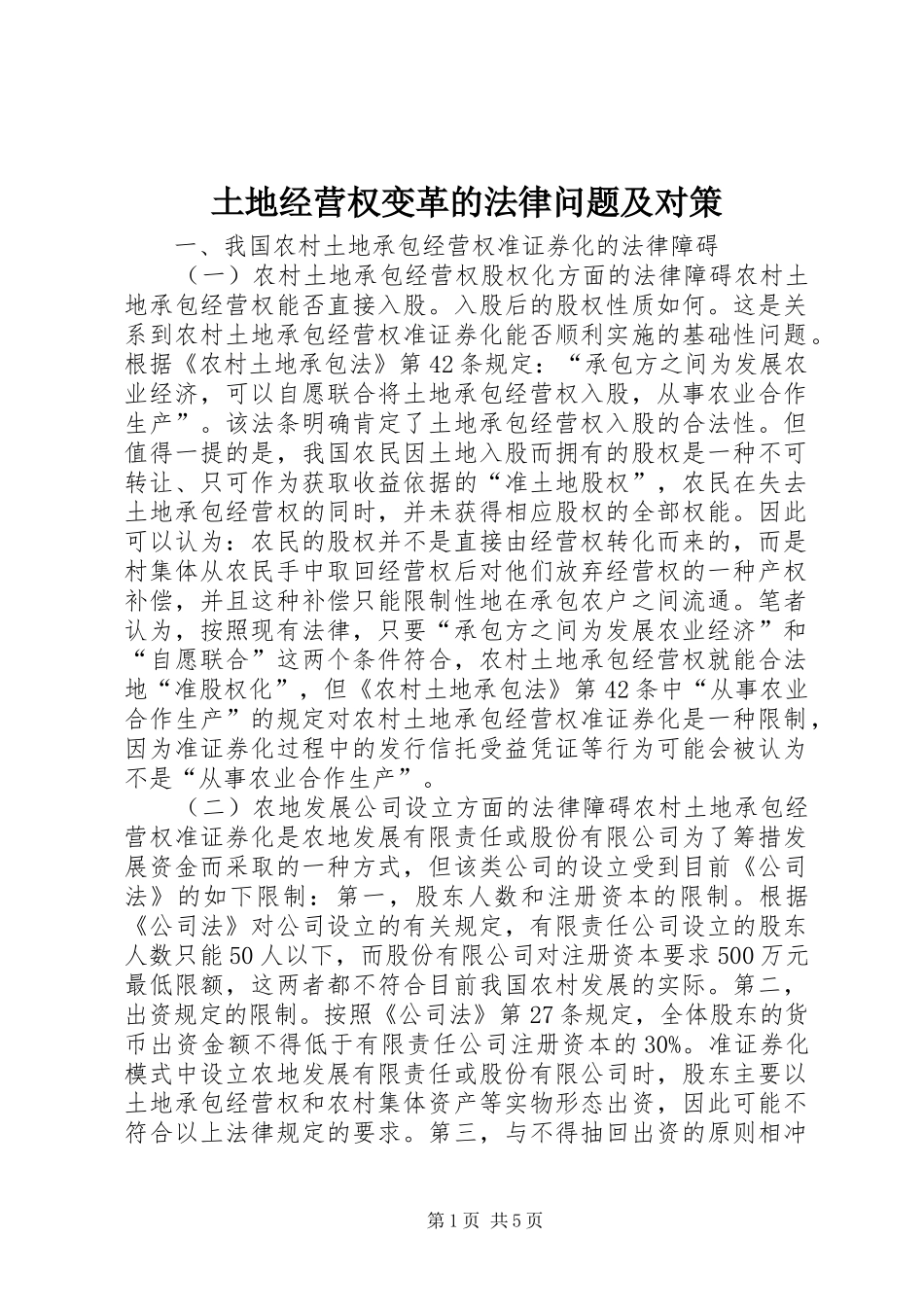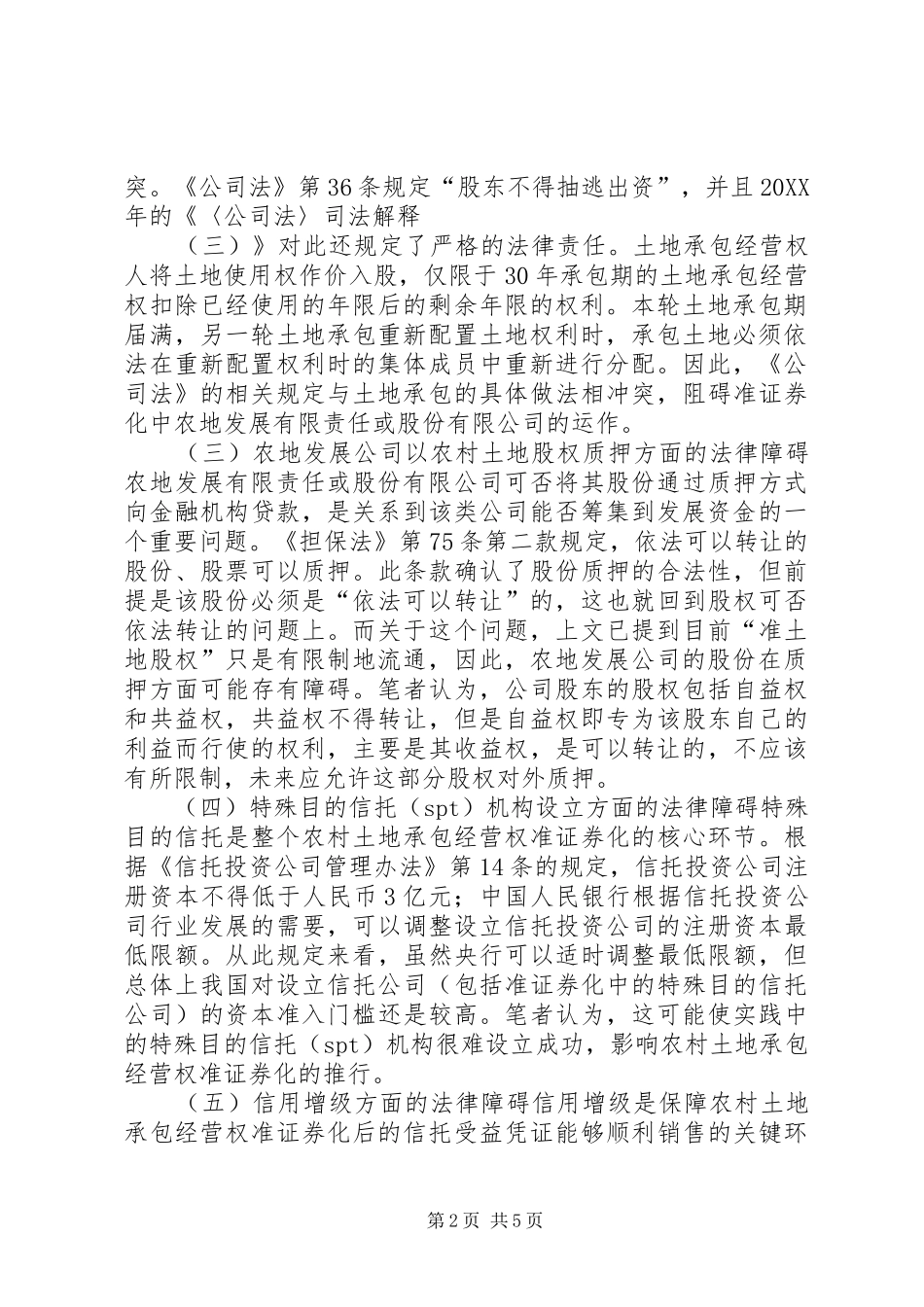土地经营权变革的法律问题及对策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准证券化的法律障碍(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方面的法律障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直接入股。入股后的股权性质如何。这是关系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准证券化能否顺利实施的基础性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该法条明确肯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合法性。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农民因土地入股而拥有的股权是一种不可转让、只可作为获取收益依据的“准土地股权”,农民在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并未获得相应股权的全部权能。因此可以认为:农民的股权并不是直接由经营权转化而来的,而是村集体从农民手中取回经营权后对他们放弃经营权的一种产权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只能限制性地在承包农户之间流通。笔者认为,按照现有法律,只要“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和“自愿联合”这两个条件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能合法地“准股权化”,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中“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的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准证券化是一种限制,因为准证券化过程中的发行信托受益凭证等行为可能会被认为不是“从事农业合作生产”。(二)农地发展公司设立方面的法律障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准证券化是农地发展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公司为了筹措发展资金而采取的一种方式,但该类公司的设立受到目前《公司法》的如下限制:第一,股东人数和注册资本的限制。根据《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有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股东人数只能50人以下,而股份有限公司对注册资本要求500万元最低限额,这两者都不符合目前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第二,出资规定的限制。按照《公司法》第27条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准证券化模式中设立农地发展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公司时,股东主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资产等实物形态出资,因此可能不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要求。第三,与不得抽回出资的原则相冲第1页共5页突。《公司法》第36条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并且20XX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此还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仅限于30年承包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扣除已经使用的年限后的剩余年限的权利。本轮土地承包期届满,另一轮土地承包重新配置土地权利时,承包土地必须依法在重新配置权利时的集体成员中重新进行分配。因此,《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与土地承包的具体做法相冲突,阻碍准证券化中农地发展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运作。(三)农地发展公司以农村土地股权质押方面的法律障碍农地发展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公司可否将其股份通过质押方式向金融机构贷款,是关系到该类公司能否筹集到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问题。《担保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此条款确认了股份质押的合法性,但前提是该股份必须是“依法可以转让”的,这也就回到股权可否依法转让的问题上。而关于这个问题,上文已提到目前“准土地股权”只是有限制地流通,因此,农地发展公司的股份在质押方面可能存有障碍。笔者认为,公司股东的股权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共益权不得转让,但是自益权即专为该股东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是其收益权,是可以转让的,不应该有所限制,未来应允许这部分股权对外质押。(四)特殊目的信托(spt)机构设立方面的法律障碍特殊目的信托是整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准证券化的核心环节。根据《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14条的规定,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亿元;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信托投资公司行业发展的需要,可以调整设立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从此规定来看,虽然央行可以适时调整最低限额,但总体上我国对设立信托公司(包括准证券化中的特殊目的信托公司)的资本准入门槛还是较高。笔者认为,这可能使实践中的特殊目的信托(spt)机构很难设立成功,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准证券化的推行。(五)信用增级方面的法律障碍信用增级是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准证券化后的信托受益凭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