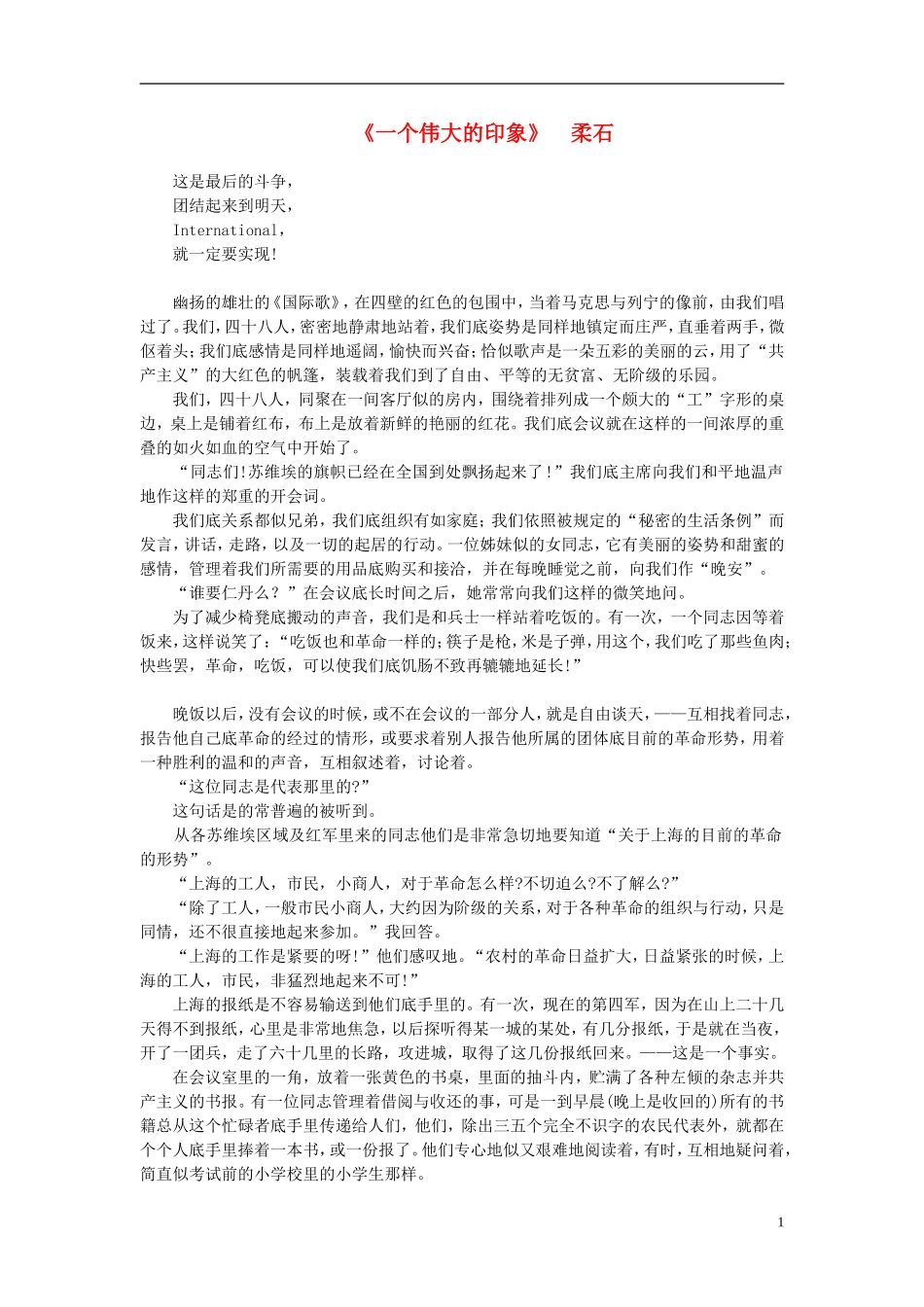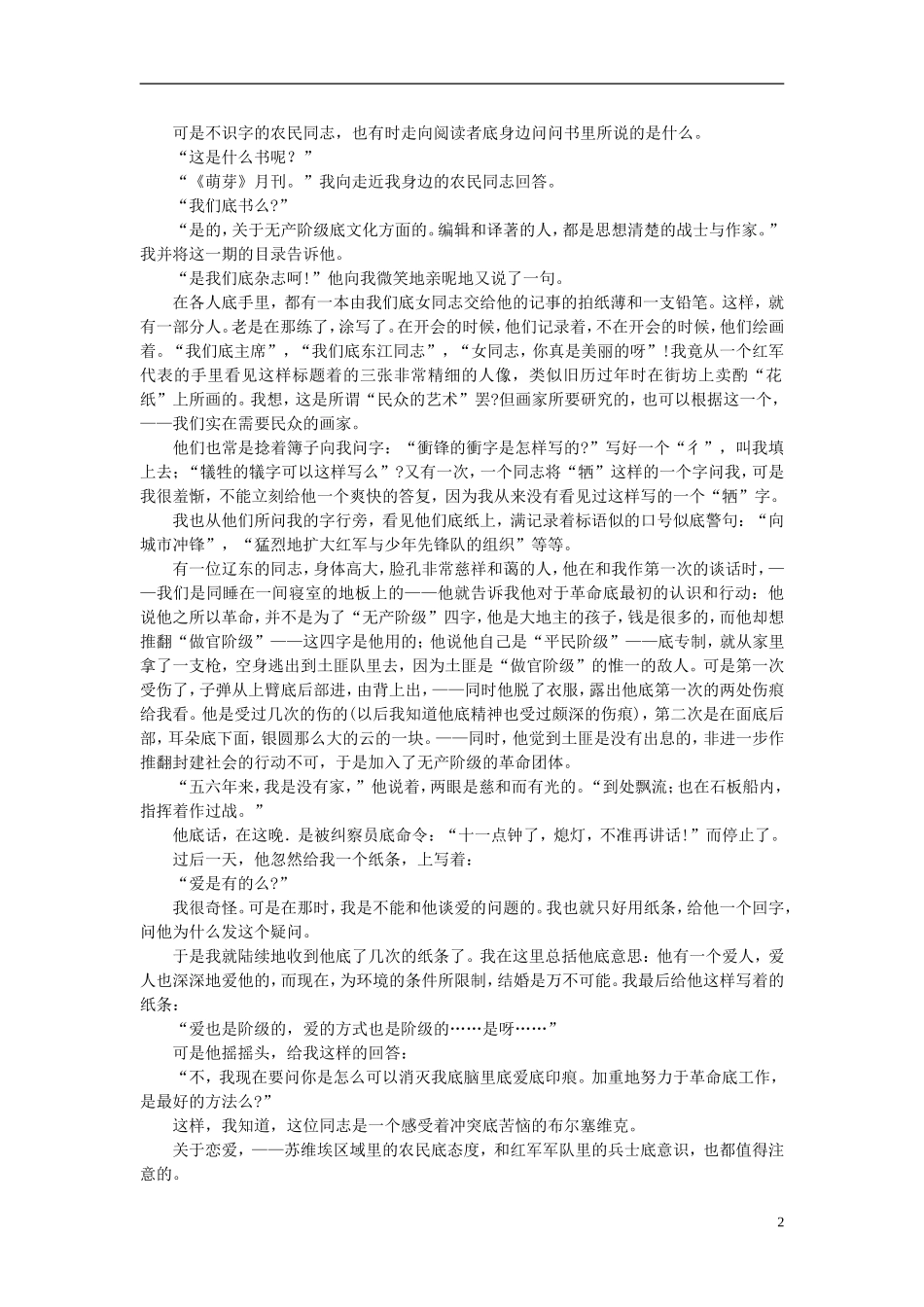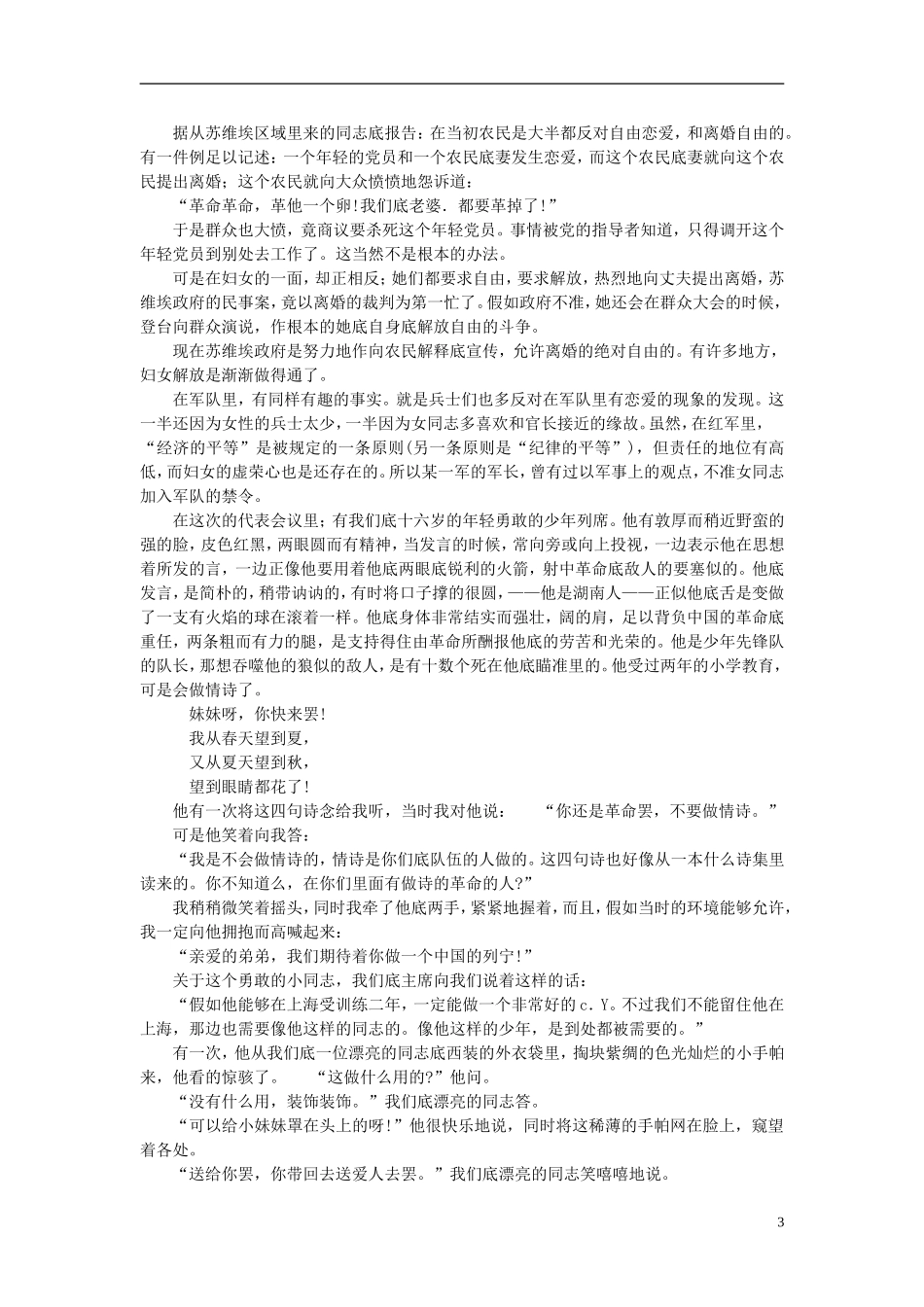《一个伟大的印象》柔石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幽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我们,四十八人,密密地静肃地站着,我们底姿势是同样地镇定而庄严,直垂着两手,微伛着头;我们底感情是同样地遥阔,愉快而兴奋;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园。我们,四十八人,同聚在一间客厅似的房内,围绕着排列成一个颇大的“工”字形的桌边,桌上是铺着红布,布上是放着新鲜的艳丽的红花。我们底会议就在这样的一间浓厚的重叠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起来了!”我们底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会词。我们底关系都似兄弟,我们底组织有如家庭;我们依照被规定的“秘密的生活条例”而发言,讲话,走路,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动。一位姊妹似的女同志,它有美丽的姿势和甜蜜的感情,管理着我们所需要的用品底购买和接洽,并在每晚睡觉之前,向我们作“晚安”。“谁要仁丹么?”在会议底长时间之后,她常常向我们这样的微笑地问。为了减少椅凳底搬动的声音,我们是和兵士一样站着吃饭的。有一次,一个同志因等着饭来,这样说笑了:“吃饭也和革命一样的;筷子是枪,米是子弹,用这个,我们吃了那些鱼肉;快些罢,革命,吃饭,可以使我们底饥肠不致再辘辘地延长!”晚饭以后,没有会议的时候,或不在会议的一部分人,就是自由谈天,——互相找着同志,报告他自己底革命的经过的情形,或要求着别人报告他所属的团体底目前的革命形势,用着一种胜利的温和的声音,互相叙述着,讨论着。“这位同志是代表那里的?”这句话是的常普遍的被听到。从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里来的同志他们是非常急切地要知道“关于上海的目前的革命的形势”。“上海的工人,市民,小商人,对于革命怎么样?不切迫么?不了解么?”“除了工人,一般市民小商人,大约因为阶级的关系,对于各种革命的组织与行动,只是同情,还不很直接地起来参加。”我回答。“上海的工作是紧要的呀!”他们感叹地。“农村的革命日益扩大,日益紧张的时候,上海的工人,市民,非猛烈地起来不可!”上海的报纸是不容易输送到他们底手里的。有一次,现在的第四军,因为在山上二十几天得不到报纸,心里是非常地焦急,以后探听得某一城的某处,有几分报纸,于是就在当夜,开了一团兵,走了六十几里的长路,攻进城,取得了这几份报纸回来。——这是一个事实。在会议室里的一角,放着一张黄色的书桌,里面的抽斗内,贮满了各种左倾的杂志并共产主义的书报。有一位同志管理着借阅与收还的事,可是一到早晨(晚上是收回的)所有的书籍总从这个忙碌者底手里传递给人们,他们,除出三五个完全不识字的农民代表外,就都在个个人底手里捧着一本书,或一份报了。他们专心地似又艰难地阅读着,有时,互相地疑问着,简直似考试前的小学校里的小学生那样。1可是不识字的农民同志,也有时走向阅读者底身边问问书里所说的是什么。“这是什么书呢?”“《萌芽》月刊。”我向走近我身边的农民同志回答。“我们底书么?”“是的,关于无产阶级底文化方面的。编辑和译著的人,都是思想清楚的战士与作家。”我并将这一期的目录告诉他。“是我们底杂志呵!”他向我微笑地亲昵地又说了一句。在各人底手里,都有一本由我们底女同志交给他的记事的拍纸薄和一支铅笔。这样,就有一部分人。老是在那练了,涂写了。在开会的时候,他们记录着,不在开会的时候,他们绘画着。“我们底主席”,“我们底东江同志”,“女同志,你真是美丽的呀”!我竟从一个红军代表的手里看见这样标题着的三张非常精细的人像,类似旧历过年时在街坊上卖酌“花纸”上所画的。我想,这是所谓“民众的艺术”罢?但画家所要研究的,也可以根据这一个,——我们实在需要民众的画家。他们也常是捻着簿子向我问字:“衝锋的衝字是怎样写的?”写好一个“彳”,叫我填上去;“犠牲的犠字可以这样写么”?又有一次,一个同志将“牺”这样的一个字问我,可是我很羞惭,不能立刻给他一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