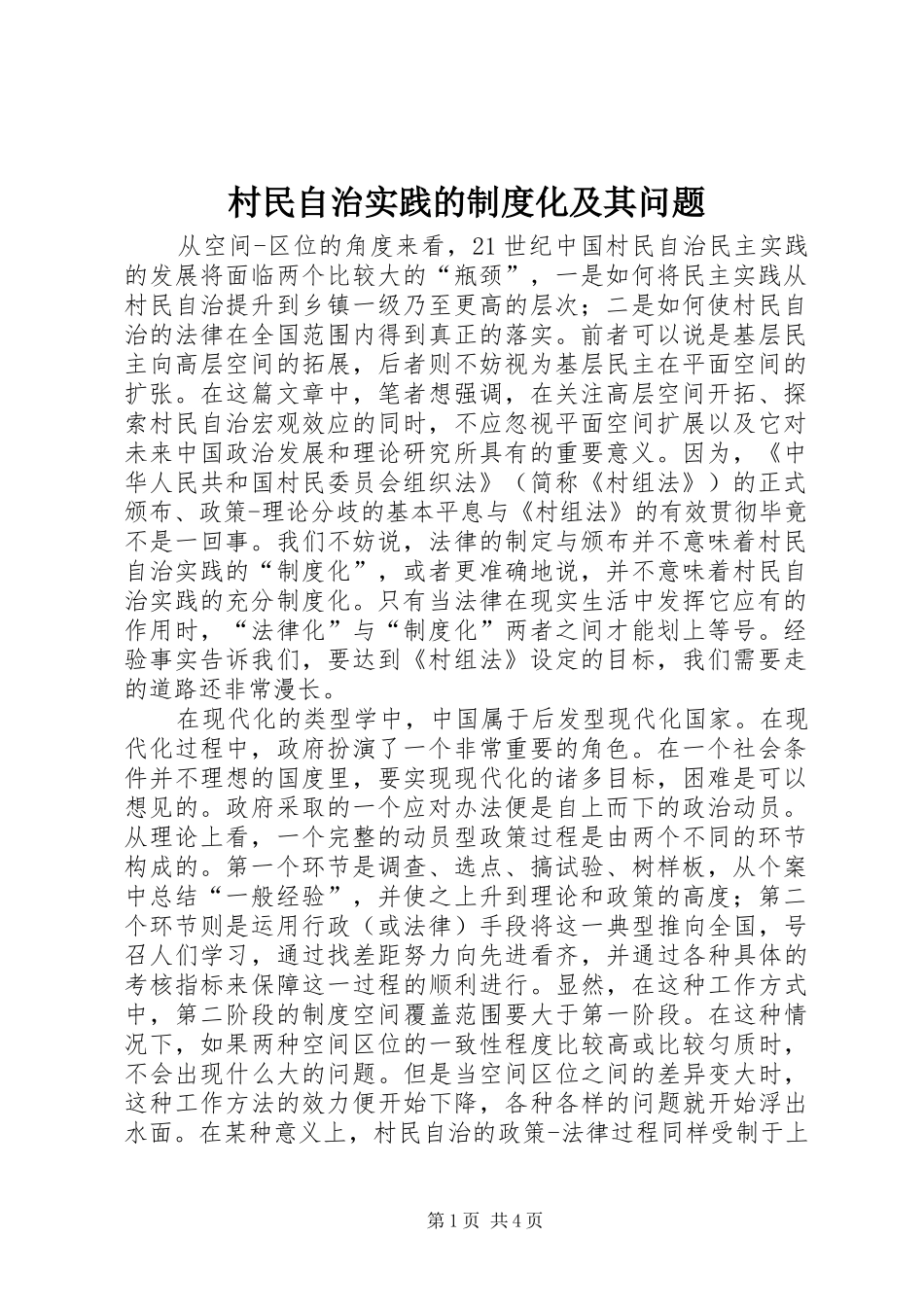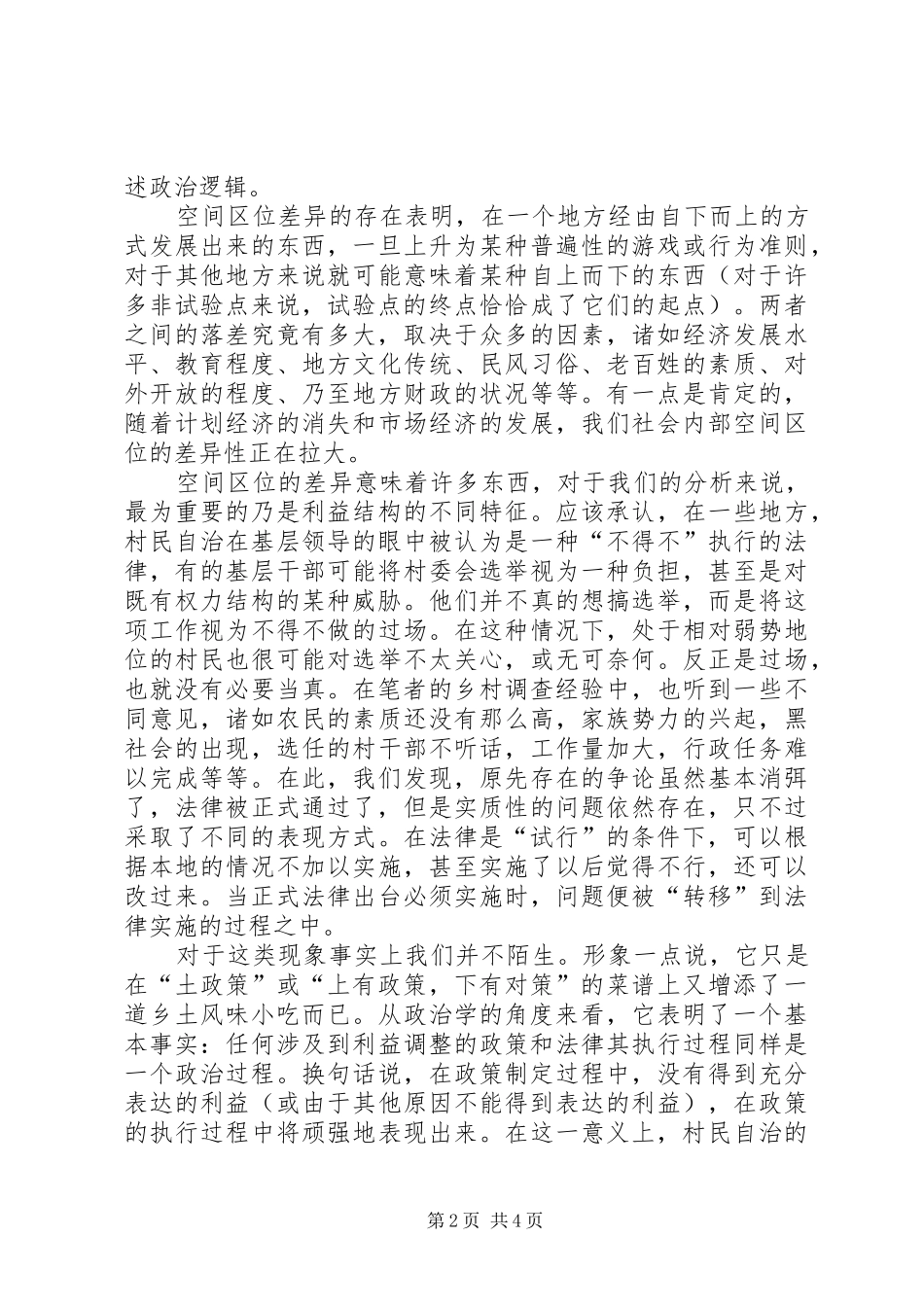村民自治实践的制度化及其问题从空间-区位的角度来看,21世纪中国村民自治民主实践的发展将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一是如何将民主实践从村民自治提升到乡镇一级乃至更高的层次;二是如何使村民自治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落实。前者可以说是基层民主向高层空间的拓展,后者则不妨视为基层民主在平面空间的扩张。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想强调,在关注高层空间开拓、探索村民自治宏观效应的同时,不应忽视平面空间扩展以及它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和理论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村组法》)的正式颁布、政策-理论分歧的基本平息与《村组法》的有效贯彻毕竟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妨说,法律的制定与颁布并不意味着村民自治实践的“制度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意味着村民自治实践的充分制度化。只有当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时,“法律化”与“制度化”两者之间才能划上等号。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要达到《村组法》设定的目标,我们需要走的道路还非常漫长。在现代化的类型学中,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社会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度里,要实现现代化的诸多目标,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政府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便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从理论上看,一个完整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调查、选点、搞试验、树样板,从个案中总结“一般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第二个环节则是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这一典型推向全国,号召人们学习,通过找差距努力向先进看齐,并通过各种具体的考核指标来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显然,在这种工作方式中,第二阶段的制度空间覆盖范围要大于第一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种空间区位的一致性程度比较高或比较匀质时,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当空间区位之间的差异变大时,这种工作方法的效力便开始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在某种意义上,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过程同样受制于上第1页共4页述政治逻辑。空间区位差异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地方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的游戏或行为准则,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对于许多非试验点来说,试验点的终点恰恰成了它们的起点)。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诸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地方文化传统、民风习俗、老百姓的素质、对外开放的程度、乃至地方财政的状况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计划经济的消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社会内部空间区位的差异性正在拉大。空间区位的差异意味着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利益结构的不同特征。应该承认,在一些地方,村民自治在基层领导的眼中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法律,有的基层干部可能将村委会选举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某种威胁。他们并不真的想搞选举,而是将这项工作视为不得不做的过场。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村民也很可能对选举不太关心,或无可奈何。反正是过场,也就没有必要当真。在笔者的乡村调查经验中,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诸如农民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家族势力的兴起,黑社会的出现,选任的村干部不听话,工作量加大,行政任务难以完成等等。在此,我们发现,原先存在的争论虽然基本消弭了,法律被正式通过了,但是实质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在法律是“试行”的条件下,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不加以实施,甚至实施了以后觉得不行,还可以改过来。当正式法律出台必须实施时,问题便被“转移”到法律实施的过程之中。对于这类现象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形象一点说,它只是在“土政策”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菜谱上又增添了一道乡土风味小吃而已。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涉及到利益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其执行过程同样是一个政治过程。换句话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利益(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得到表达的利益),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将顽强地表现出来。在这一意义上,村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