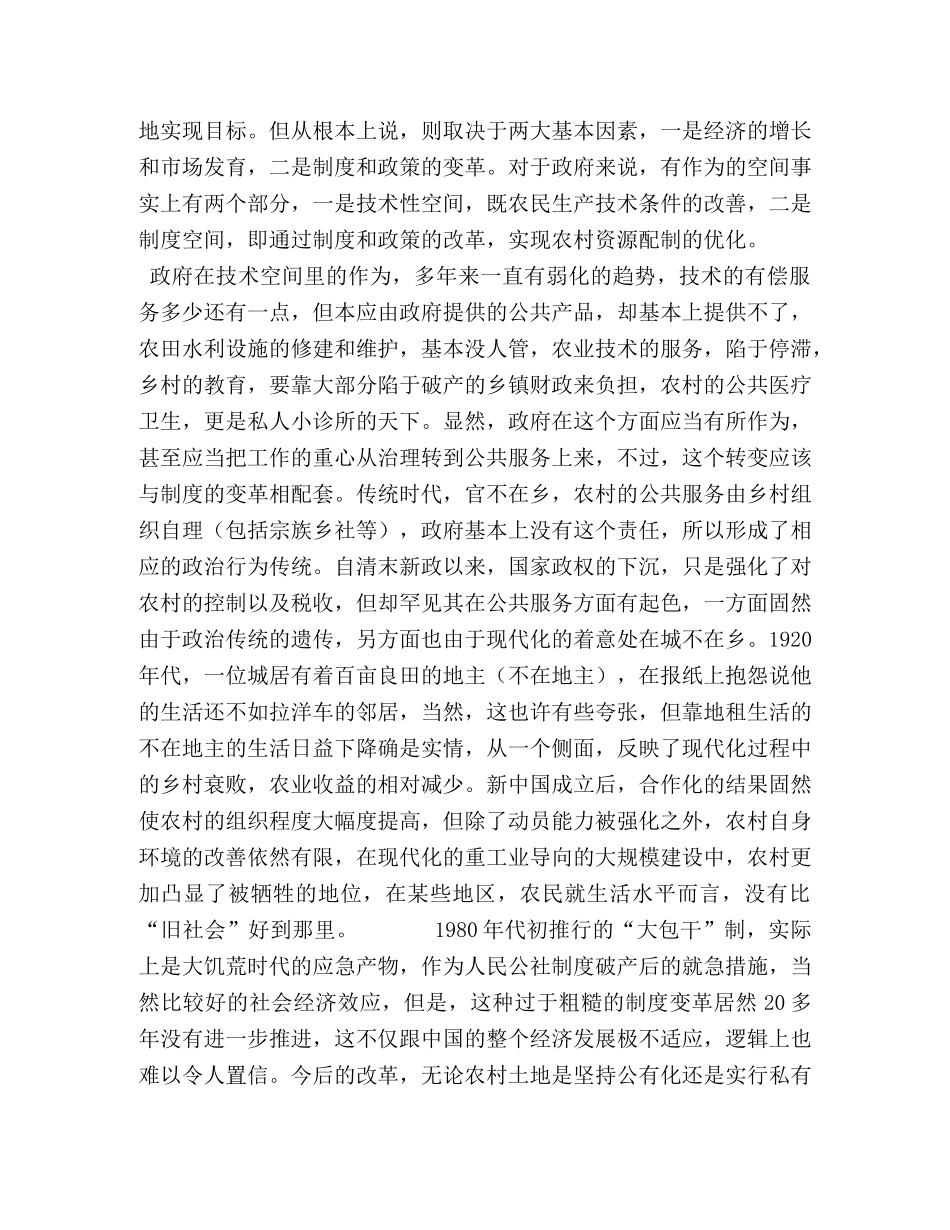“阿是穴”疗法的用处和局限中医针灸术里,有一种叫做“阿是穴”的穴位,不属于《针灸甲乙经》上的经络穴位名录,但也会被医者用到。据说这种穴位的来由是,哪儿痛,医生用手一按,患者应声叫:“啊——是!”而得名。显然,如果拿针治病的人,只知道扎阿是穴,就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疗法。古来医人类似于医国,只扎阿是穴的现象,在乡村治理方面也不鲜见。已经有许多年了,在所谓的“三农问题”中,农民负担问题最为人们所关注,农民叫,大小媒体叫,某些递折子的学者更是嚷得凶,中部地区出现的少数群体性农民抗争,成了他们博取上头垂顾的资本。没错,农民的负担是重,有些地区已经重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对于农民来说,对自身遭际最直接的感受,也就是他们的负担,但是,是不是将加在农民头上的所有负担,包括作为公民所应交纳的起码的税收统统减掉,农民就会从此富裕起来呢?所有了解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农民负担问题只是现时农村问题的表象,就事论事,无论以税费改革还是以补贴的方式解决之,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阿是穴疗法,充其量只是暂时从精神上缓解痛苦。近来,政府对于农民负担的“旱情”施下不少雨露,农业税的取消,补贴的到位,让饥渴中的农民喜出望外。一位朋友告诉我,最近他下去调查发现,农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好事居然是真,有的农民甚至怀疑是不是要打台湾了,所以(中央)才对他们这么好。不过,上面的雨露固然令农民有望外之喜,但比起近来粮食涨价所带给农民的实惠,却有小巫大巫之别,也就是说,减税和补贴只是减轻了农民的被剥夺和被抛弃感,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还是来自市场的粮食涨价。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具体的说,是如何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只要存在增收的客观因素,比如粮食的涨价,或者技术条件的改善,比如种子的改良、养殖和种植技术的输入、贷款的增加等等,都可以部分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地实现目标。但从根本上说,则取决于两大基本因素,一是经济的增长和市场发育,二是制度和政策的变革。对于政府来说,有作为的空间事实上有两个部分,一是技术性空间,既农民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善,二是制度空间,即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实现农村资源配制的优化。政府在技术空间里的作为,多年来一直有弱化的趋势,技术的有偿服务多少还有一点,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基本上提供不了,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基本没人管,农业技术的服务,陷于停滞,乡村的教育,要靠大部分陷于破产的乡镇财政来负担,农村的公共医疗卫生,更是私人小诊所的天下。显然,政府在这个方面应当有所作为,甚至应当把工作的重心从治理转到公共服务上来,不过,这个转变应该与制度的变革相配套。传统时代,官不在乡,农村的公共服务由乡村组织自理(包括宗族乡社等),政府基本上没有这个责任,所以形成了相应的政治行为传统。自清末新政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只是强化了对农村的控制以及税收,但却罕见其在公共服务方面有起色,一方面固然由于政治传统的遗传,另方面也由于现代化的着意处在城不在乡。1920年代,一位城居有着百亩良田的地主(不在地主),在报纸上抱怨说他的生活还不如拉洋车的邻居,当然,这也许有些夸张,但靠地租生活的不在地主的生活日益下降确是实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衰败,农业收益的相对减少。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的结果固然使农村的组织程度大幅度提高,但除了动员能力被强化之外,农村自身环境的改善依然有限,在现代化的重工业导向的大规模建设中,农村更加凸显了被牺牲的地位,在某些地区,农民就生活水平而言,没有比“旧社会”好到那里。1980年代初推行的“大包干”制,实际上是大饥荒时代的应急产物,作为人民公社制度破产后的就急措施,当然比较好的社会经济效应,但是,这种过于粗糙的制度变革居然20多年没有进一步推进,这不仅跟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极不适应,逻辑上也难以令人置信。今后的改革,无论农村土地是坚持公有化还是实行私有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