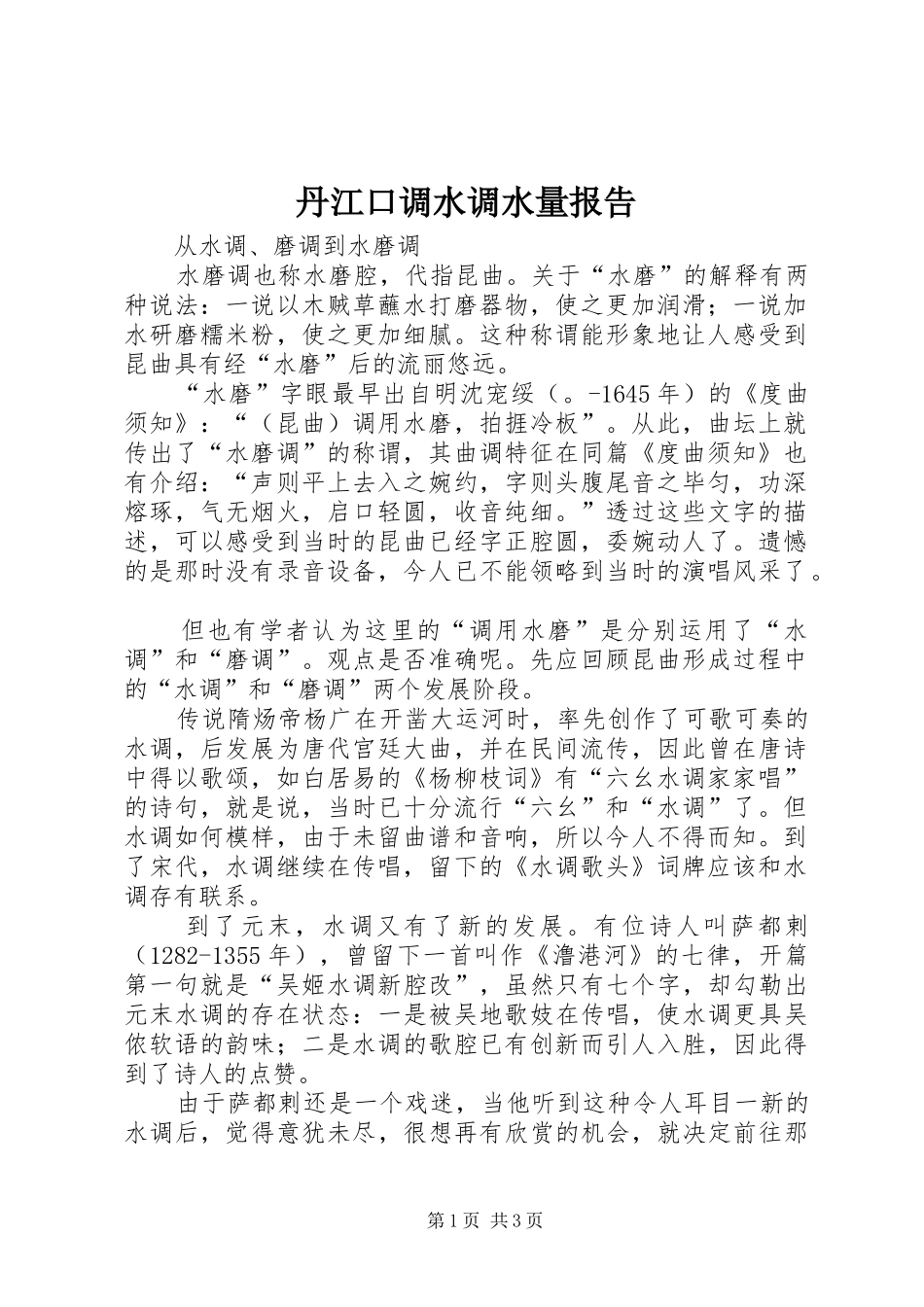丹江口调水调水量报告从水调、磨调到水磨调水磨调也称水磨腔,代指昆曲。关于“水磨”的解释有两种说法:一说以木贼草蘸水打磨器物,使之更加润滑;一说加水研磨糯米粉,使之更加细腻。这种称谓能形象地让人感受到昆曲具有经“水磨”后的流丽悠远。“水磨”字眼最早出自明沈宠绥(。-1645年)的《度曲须知》:“(昆曲)调用水磨,拍捱冷板”。从此,曲坛上就传出了“水磨调”的称谓,其曲调特征在同篇《度曲须知》也有介绍:“声则平上去入之婉约,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透过这些文字的描述,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昆曲已经字正腔圆,委婉动人了。遗憾的是那时没有录音设备,今人已不能领略到当时的演唱风采了。但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调用水磨”是分别运用了“水调”和“磨调”。观点是否准确呢。先应回顾昆曲形成过程中的“水调”和“磨调”两个发展阶段。传说隋炀帝杨广在开凿大运河时,率先创作了可歌可奏的水调,后发展为唐代宫廷大曲,并在民间流传,因此曾在唐诗中得以歌颂,如白居易的《杨柳枝词》有“六幺水调家家唱”的诗句,就是说,当时已十分流行“六幺”和“水调”了。但水调如何模样,由于未留曲谱和音响,所以今人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水调继续在传唱,留下的《水调歌头》词牌应该和水调存有联系。到了元末,水调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位诗人叫萨都剌(1282-1355年),曾留下一首叫作《澛港河》的七律,开篇第一句就是“吴姬水调新腔改”,虽然只有七个字,却勾勒出元末水调的存在状态:一是被吴地歌妓在传唱,使水调更具吴侬软语的韵味;二是水调的歌腔已有创新而引人入胜,因此得到了诗人的点赞。由于萨都剌还是一个戏迷,当他听到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水调后,觉得意犹未尽,很想再有欣赏的机会,就决定前往那第1页共3页个闻名遐迩的玉山佳处,那里有名甲天下的家班,还有高朋满座的雅集,他就奔向昆山的娄江之滨,不但饱赏美曲,而且还诗兴大发,在《玉山草堂雅集》中留下了他撰写的生动篇章。应该说,当时的“水调”离昆山腔的雏形很接近了,后经顾坚、顾阿瑛、杨维桢等曲家一起打磨,昆山腔终于横空出世。“磨调”字眼最先出自魏良辅(生卒时间不详)的《南词引正》:“北曲与南曲大相悬绝…………有磨调、弦索调,乃东坡所仿……伎人将南曲配弦索,直为方底圆盖也。”《南词引正》大致写于明嘉隆年间,是对早期曲坛的回忆文字。时称北曲为“弦索调”,明曲家王骥德(1558-1623年)在《曲律》中说:“北之歌也,必和以弦索”。由于当时的北曲常用弦索乐器伴奏,故命名之。那么“磨调”所指应该是南曲。可以推测当时磨调和弦索调并存于世,由于南曲纤细,北曲高亢,成为性格互补的两种腔调,后来,魏良辅将它们熔于一炉,丰富了昆曲的表现力,完成了“集南北曲之大成”的昆曲改良任务。但在设计唱腔时,魏良辅反感“伎人将南曲配弦索”,就是混杂了南北曲,造成了“方底圆盖”的不伦不类。其实,魏良辅写作《南词引正》时,对于南曲还有多种称谓,如南戏、南词、南辞等,而“磨调”是一种俗称,大概是由“水调”引申而来,因那时的南曲已有一字多音,一波三折的缠磨形态了,就顺着“水调”叫出了“磨调”。至于“乃东坡所传”,只是魏良辅的一家之见,想想也有可能。苏轼(字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生于北宋,考中进士后,先在开封当官,后大宋南迁后,又在苏杭一带活动,有机会接触弦索调(北曲)和磨调(南曲),由于文人喜爱唱曲,就分别仿制了磨调和弦索调两种唱腔,而得以流传下来。在曲圣魏良辅的眼里,东坡先生还有传曲之功,所以记名立传。人说昆曲历史600年,这是从魏良辅改良昆曲成功算起的时段,其实,漫长的孕育阶段应从隋唐开始形成的“水调”算起,足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水调”由隋炀帝杨广首创,后在唐宫发扬光大,紧接着被文人纷纷仿制,使这种腔调越来第2页共3页越趋向于高雅的品格,至南宋(苏东坡在世的年代)已经蜕变成“磨调”了,成为南曲的代称。此时,“水调”已经不存在,而被前赴后继的曲家改良成“磨调”了。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沈宠绥写作《度曲须知》时所说的昆曲“调用水磨”,不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