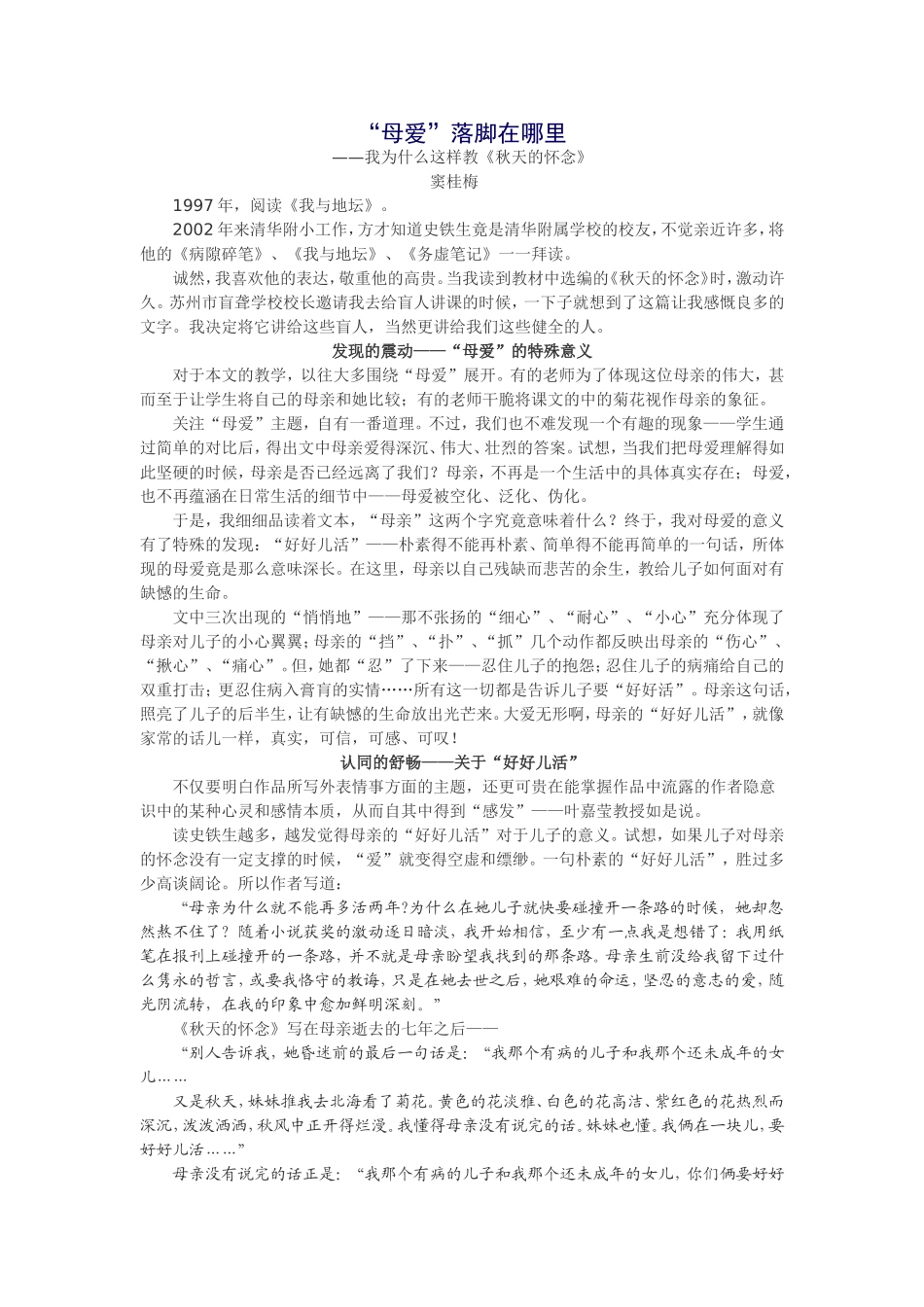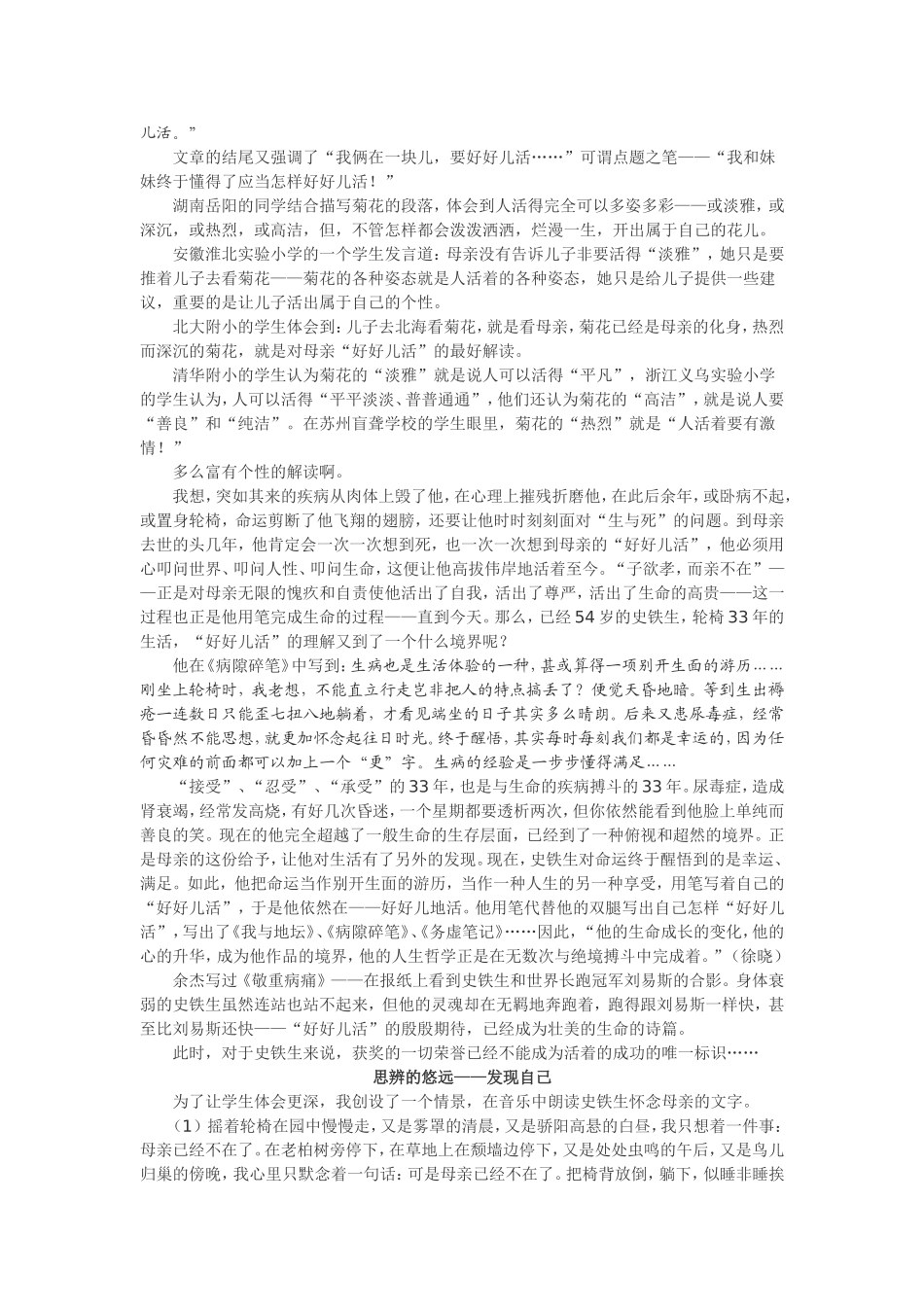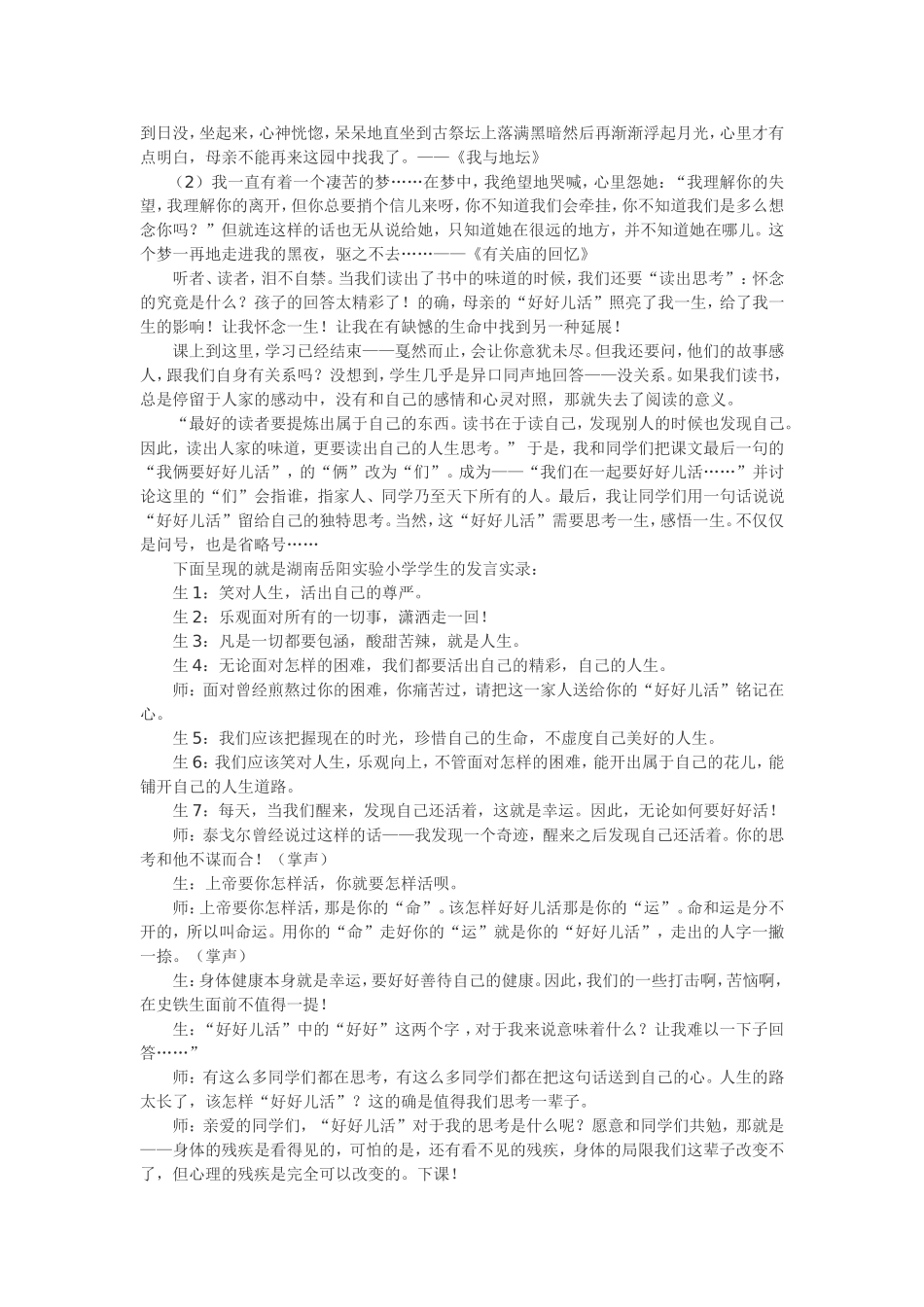“母爱”落脚在哪里——我为什么这样教《秋天的怀念》窦桂梅1997年,阅读《我与地坛》。2002年来清华附小工作,方才知道史铁生竟是清华附属学校的校友,不觉亲近许多,将他的《病隙碎笔》、《我与地坛》、《务虚笔记》一一拜读。诚然,我喜欢他的表达,敬重他的高贵。当我读到教材中选编的《秋天的怀念》时,激动许久。苏州市盲聋学校校长邀请我去给盲人讲课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这篇让我感慨良多的文字。我决定将它讲给这些盲人,当然更讲给我们这些健全的人。发现的震动——“母爱”的特殊意义对于本文的教学,以往大多围绕“母爱”展开。有的老师为了体现这位母亲的伟大,甚而至于让学生将自己的母亲和她比较;有的老师干脆将课文的中的菊花视作母亲的象征。关注“母爱”主题,自有一番道理。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学生通过简单的对比后,得出文中母亲爱得深沉、伟大、壮烈的答案。试想,当我们把母爱理解得如此坚硬的时候,母亲是否已经远离了我们?母亲,不再是一个生活中的具体真实存在;母爱,也不再蕴涵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母爱被空化、泛化、伪化。于是,我细细品读着文本,“母亲”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终于,我对母爱的意义有了特殊的发现:“好好儿活”——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句话,所体现的母爱竟是那么意味深长。在这里,母亲以自己残缺而悲苦的余生,教给儿子如何面对有缺憾的生命。文中三次出现的“悄悄地”——那不张扬的“细心”、“耐心”、“小心”充分体现了母亲对儿子的小心翼翼;母亲的“挡”、“扑”、“抓”几个动作都反映出母亲的“伤心”、“揪心”、“痛心”。但,她都“忍”了下来——忍住儿子的抱怨;忍住儿子的病痛给自己的双重打击;更忍住病入膏肓的实情……所有这一切都是告诉儿子要“好好活”。母亲这句话,照亮了儿子的后半生,让有缺憾的生命放出光芒来。大爱无形啊,母亲的“好好儿活”,就像家常的话儿一样,真实,可信,可感、可叹!认同的舒畅——关于“好好儿活”不仅要明白作品所写外表情事方面的主题,还更可贵在能掌握作品中流露的作者隐意识中的某种心灵和感情本质,从而自其中得到“感发”——叶嘉莹教授如是说。读史铁生越多,越发觉得母亲的“好好儿活”对于儿子的意义。试想,如果儿子对母亲的怀念没有一定支撑的时候,“爱”就变得空虚和缥缈。一句朴素的“好好儿活”,胜过多少高谈阔论。所以作者写道:“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秋天的怀念》写在母亲逝去的七年之后——“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母亲没有说完的话正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你们俩要好好儿活。”文章的结尾又强调了“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可谓点题之笔——“我和妹妹终于懂得了应当怎样好好儿活!”湖南岳阳的同学结合描写菊花的段落,体会到人活得完全可以多姿多彩——或淡雅,或深沉,或热烈,或高洁,但,不管怎样都会泼泼洒洒,烂漫一生,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儿。安徽淮北实验小学的一个学生发言道:母亲没有告诉儿子非要活得“淡雅”,她只是要推着儿子去看菊花——菊花的各种姿态就是人活着的各种姿态,她只是给儿子提供一些建议,重要的是让儿子活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北大附小的学生体会到:儿子去北海看菊花,就是看母亲,菊花已经是母亲的化身,热烈而深沉的菊花,就是对母亲“好好儿活”的最好解读。清华附小的学生认为菊花的“淡雅”就是说人可以活得“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