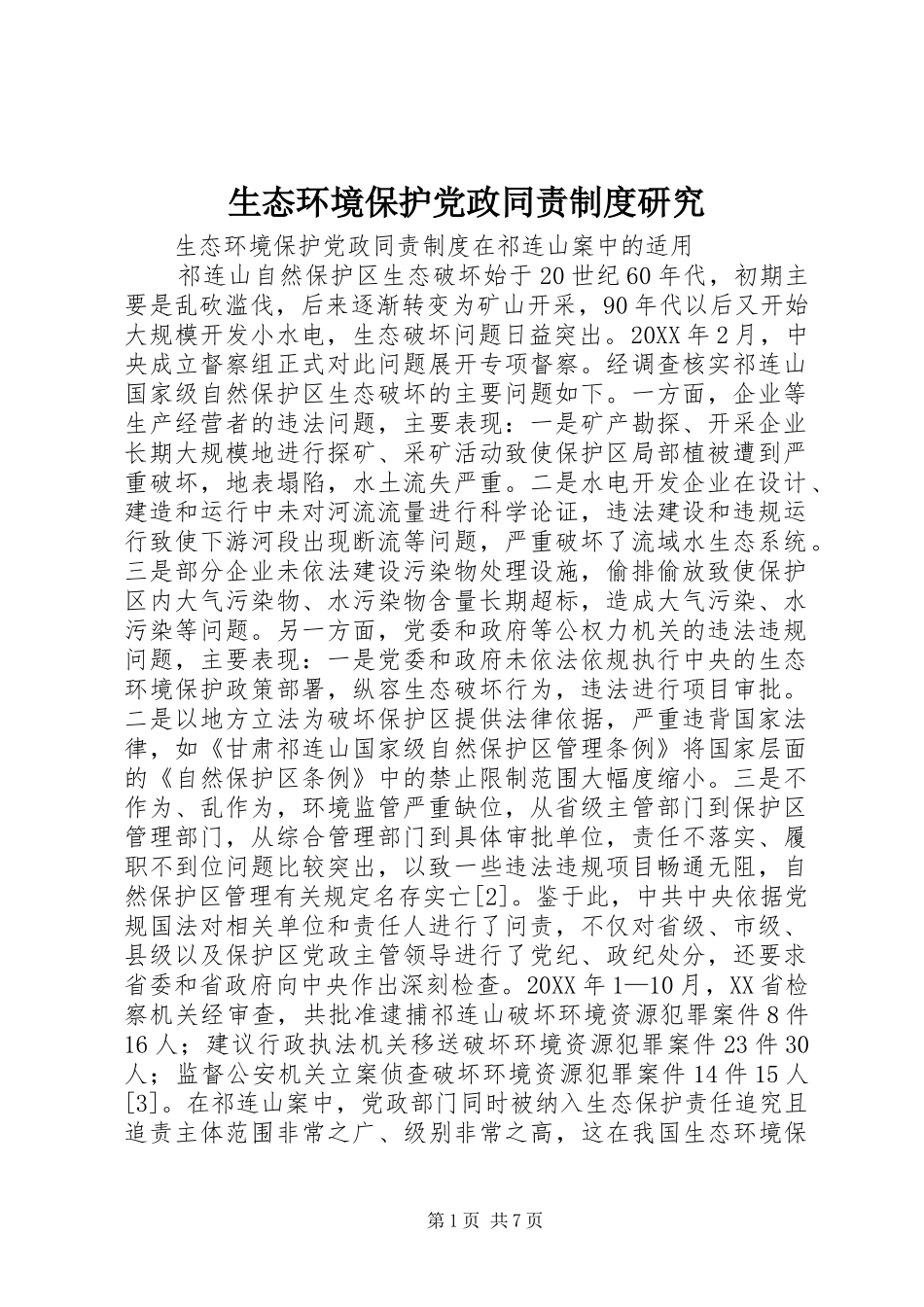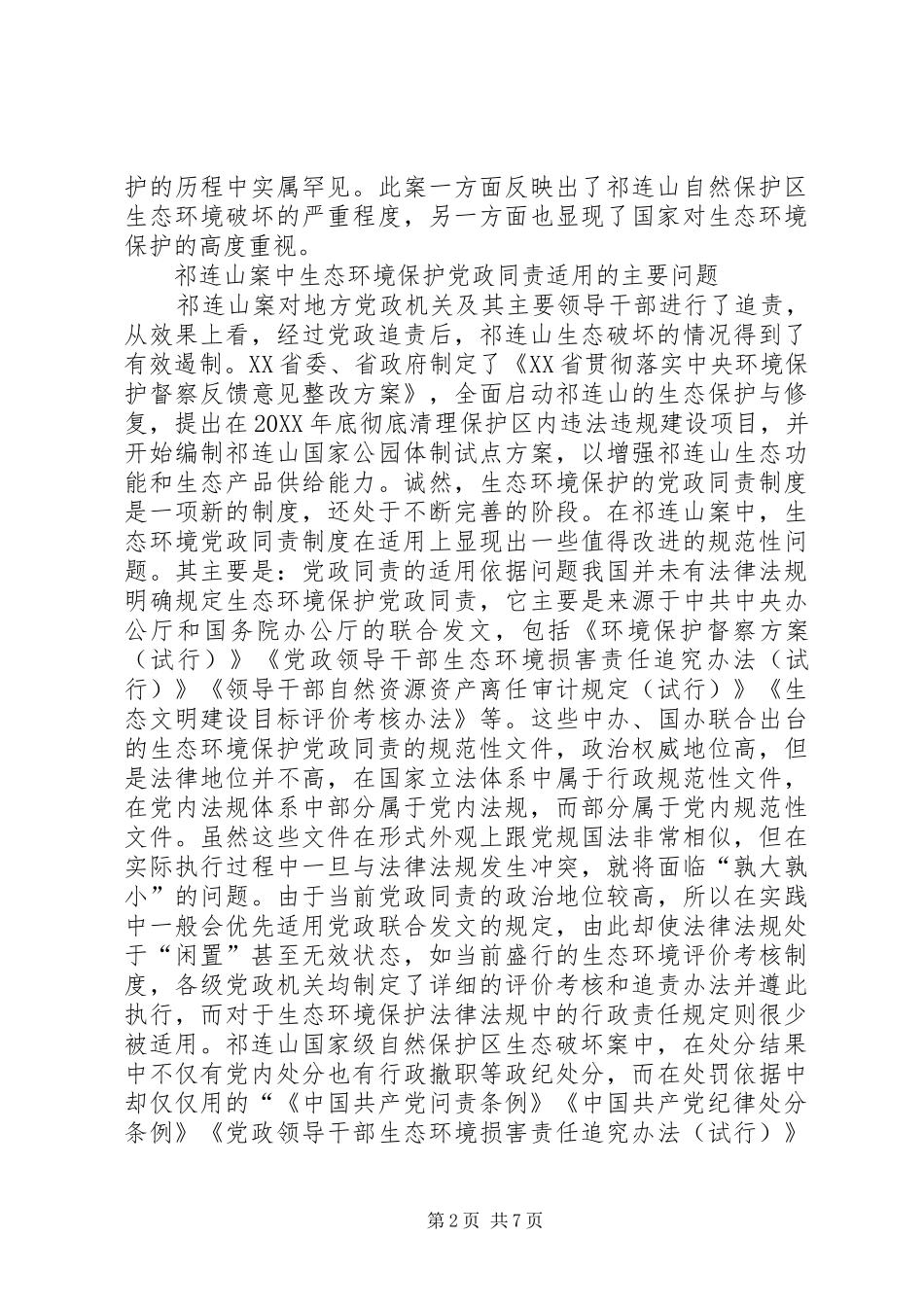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制度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制度在祁连山案中的适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主要是乱砍滥伐,后来逐渐转变为矿山开采,90年代以后又开始大规模开发小水电,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20XX年2月,中央成立督察组正式对此问题展开专项督察。经调查核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方面,企业等生产经营者的违法问题,主要表现:一是矿产勘探、开采企业长期大规模地进行探矿、采矿活动致使保护区局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地表塌陷,水土流失严重。二是水电开发企业在设计、建造和运行中未对河流流量进行科学论证,违法建设和违规运行致使下游河段出现断流等问题,严重破坏了流域水生态系统。三是部分企业未依法建设污染物处理设施,偷排偷放致使保护区内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含量长期超标,造成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另一方面,党委和政府等公权力机关的违法违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党委和政府未依法依规执行中央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部署,纵容生态破坏行为,违法进行项目审批。二是以地方立法为破坏保护区提供法律依据,严重违背国家法律,如《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将国家层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中的禁止限制范围大幅度缩小。三是不作为、乱作为,环境监管严重缺位,从省级主管部门到保护区管理部门,从综合管理部门到具体审批单位,责任不落实、履职不到位问题比较突出,以致一些违法违规项目畅通无阻,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规定名存实亡[2]。鉴于此,中共中央依据党规国法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了问责,不仅对省级、市级、县级以及保护区党政主管领导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还要求省委和省政府向中央作出深刻检查。20XX年1—10月,XX省检察机关经审查,共批准逮捕祁连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8件16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3件30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4件15人[3]。在祁连山案中,党政部门同时被纳入生态保护责任追究且追责主体范围非常之广、级别非常之高,这在我国生态环境保第1页共7页护的历程中实属罕见。此案一方面反映出了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显现了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祁连山案中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适用的主要问题祁连山案对地方党政机关及其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追责,从效果上看,经过党政追责后,祁连山生态破坏的情况得到了有效遏制。XX省委、省政府制定了《XX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全面启动祁连山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出在20XX年底彻底清理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并开始编制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增强祁连山生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诚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制度是一项新的制度,还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在祁连山案中,生态环境党政同责制度在适用上显现出一些值得改进的规范性问题。其主要是:党政同责的适用依据问题我国并未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它主要是来源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联合发文,包括《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等。这些中办、国办联合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规范性文件,政治权威地位高,但是法律地位并不高,在国家立法体系中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党内法规体系中部分属于党内法规,而部分属于党内规范性文件。虽然这些文件在形式外观上跟党规国法非常相似,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旦与法律法规发生冲突,就将面临“孰大孰小”的问题。由于当前党政同责的政治地位较高,所以在实践中一般会优先适用党政联合发文的规定,由此却使法律法规处于“闲置”甚至无效状态,如当前盛行的生态环境评价考核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均制定了详细的评价考核和追责办法并遵此执行,而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的行政责任规定则很少被适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案中,在处分结果中不仅有党内处分也有行政撤职等政纪处分,而在处罚依据中却仅仅用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