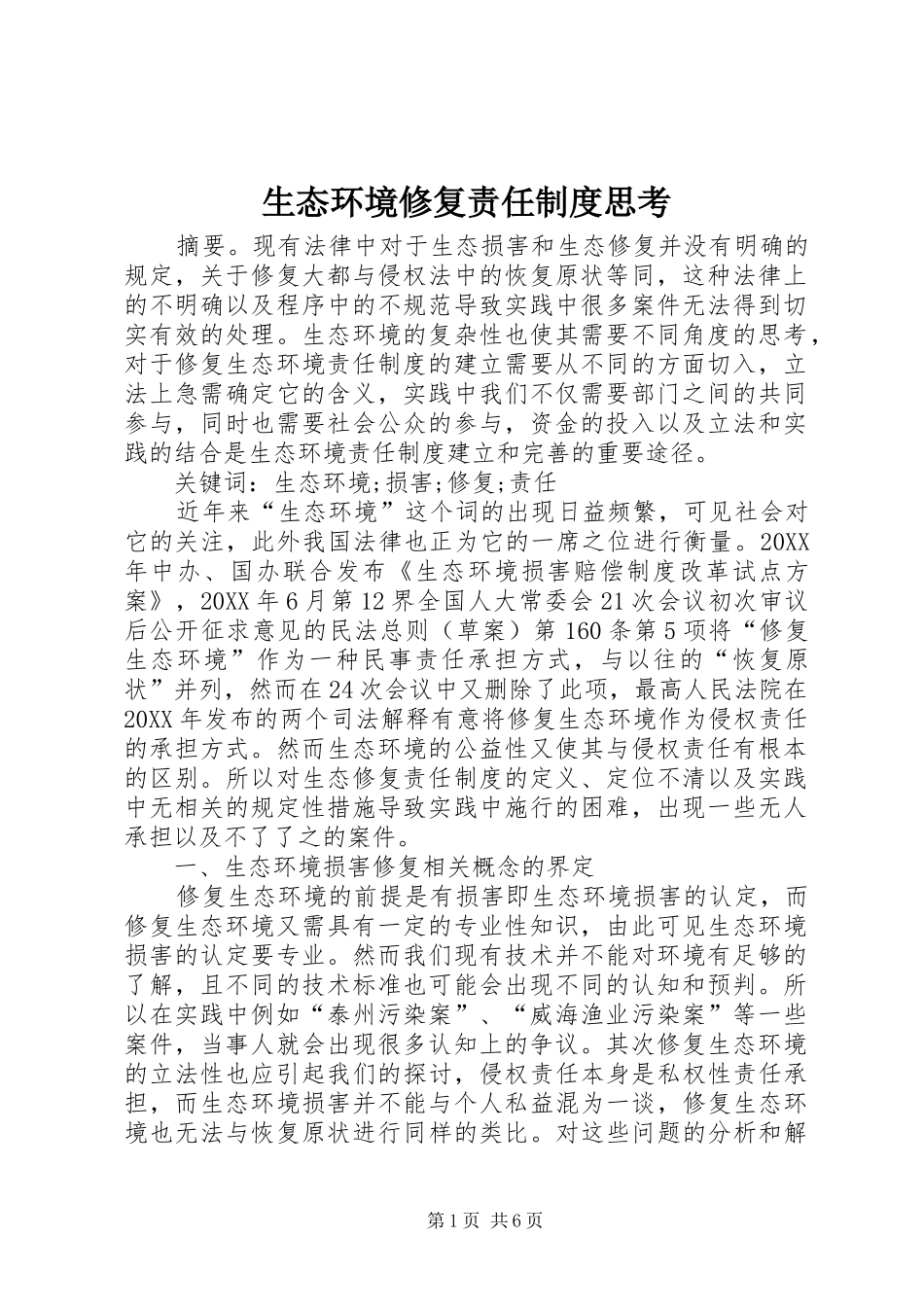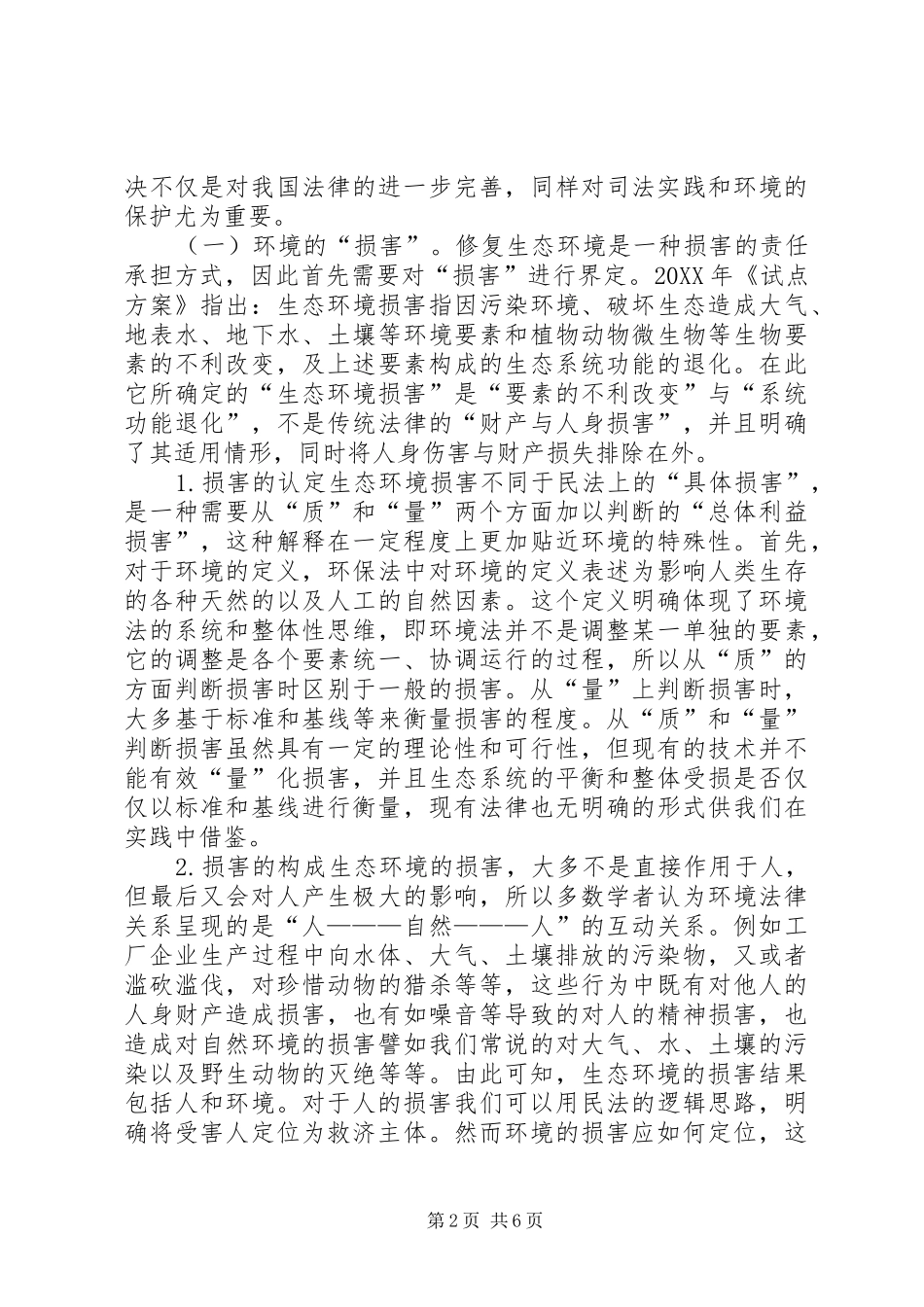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思考摘要。现有法律中对于生态损害和生态修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关于修复大都与侵权法中的恢复原状等同,这种法律上的不明确以及程序中的不规范导致实践中很多案件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处理。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也使其需要不同角度的思考,对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建立需要从不同的方面切入,立法上急需确定它的含义,实践中我们不仅需要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同时也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资金的投入以及立法和实践的结合是生态环境责任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重要途径。关键词: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近年来“生态环境”这个词的出现日益频繁,可见社会对它的关注,此外我国法律也正为它的一席之位进行衡量。20XX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XX年6月第12界全国人大常委会21次会议初次审议后公开征求意见的民法总则(草案)第160条第5项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与以往的“恢复原状”并列,然而在24次会议中又删除了此项,最高人民法院在20XX年发布的两个司法解释有意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然而生态环境的公益性又使其与侵权责任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对生态修复责任制度的定义、定位不清以及实践中无相关的规定性措施导致实践中施行的困难,出现一些无人承担以及不了了之的案件。一、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相关概念的界定修复生态环境的前提是有损害即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而修复生态环境又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知识,由此可见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要专业。然而我们现有技术并不能对环境有足够的了解,且不同的技术标准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认知和预判。所以在实践中例如“泰州污染案”、“威海渔业污染案”等一些案件,当事人就会出现很多认知上的争议。其次修复生态环境的立法性也应引起我们的探讨,侵权责任本身是私权性责任承担,而生态环境损害并不能与个人私益混为一谈,修复生态环境也无法与恢复原状进行同样的类比。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第1页共6页决不仅是对我国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同样对司法实践和环境的保护尤为重要。(一)环境的“损害”。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因此首先需要对“损害”进行界定。20XX年《试点方案》指出:生态环境损害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在此它所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是“要素的不利改变”与“系统功能退化”,不是传统法律的“财产与人身损害”,并且明确了其适用情形,同时将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排除在外。1.损害的认定生态环境损害不同于民法上的“具体损害”,是一种需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判断的“总体利益损害”,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环境的特殊性。首先,对于环境的定义,环保法中对环境的定义表述为影响人类生存的各种天然的以及人工的自然因素。这个定义明确体现了环境法的系统和整体性思维,即环境法并不是调整某一单独的要素,它的调整是各个要素统一、协调运行的过程,所以从“质”的方面判断损害时区别于一般的损害。从“量”上判断损害时,大多基于标准和基线等来衡量损害的程度。从“质”和“量”判断损害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可行性,但现有的技术并不能有效“量”化损害,并且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整体受损是否仅仅以标准和基线进行衡量,现有法律也无明确的形式供我们在实践中借鉴。2.损害的构成生态环境的损害,大多不是直接作用于人,但最后又会对人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多数学者认为环境法律关系呈现的是“人———自然———人”的互动关系。例如工厂企业生产过程中向水体、大气、土壤排放的污染物,又或者滥砍滥伐,对珍惜动物的猎杀等等,这些行为中既有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也有如噪音等导致的对人的精神损害,也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譬如我们常说的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以及野生动物的灭绝等等。由此可知,生态环境的损害结果包括人和环境。对于人的损害我们可以用民法的逻辑思路,明确将受害人定位为救济主体。然而环境的损害应如何定位,这第2页共6页也是将生态环境修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