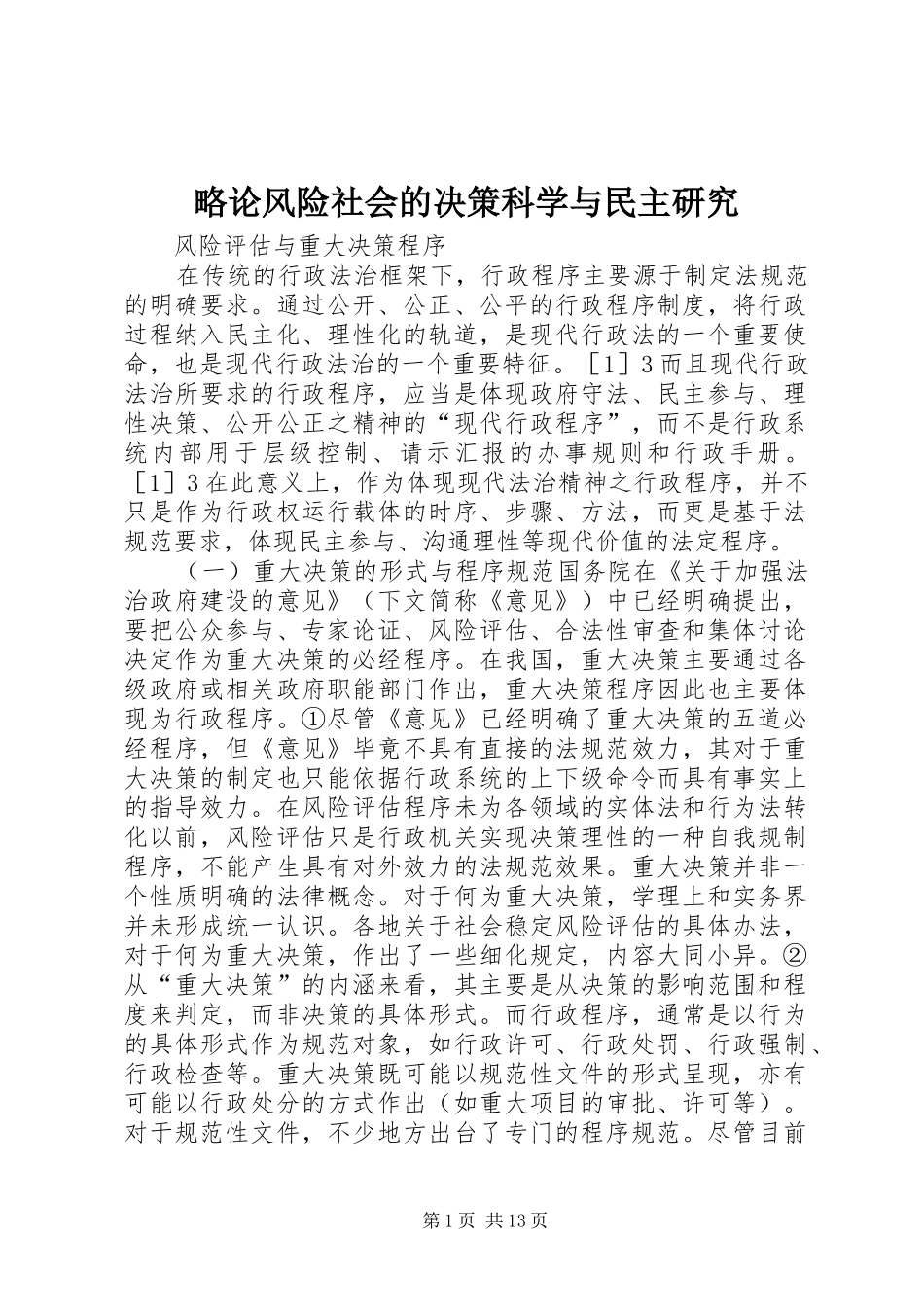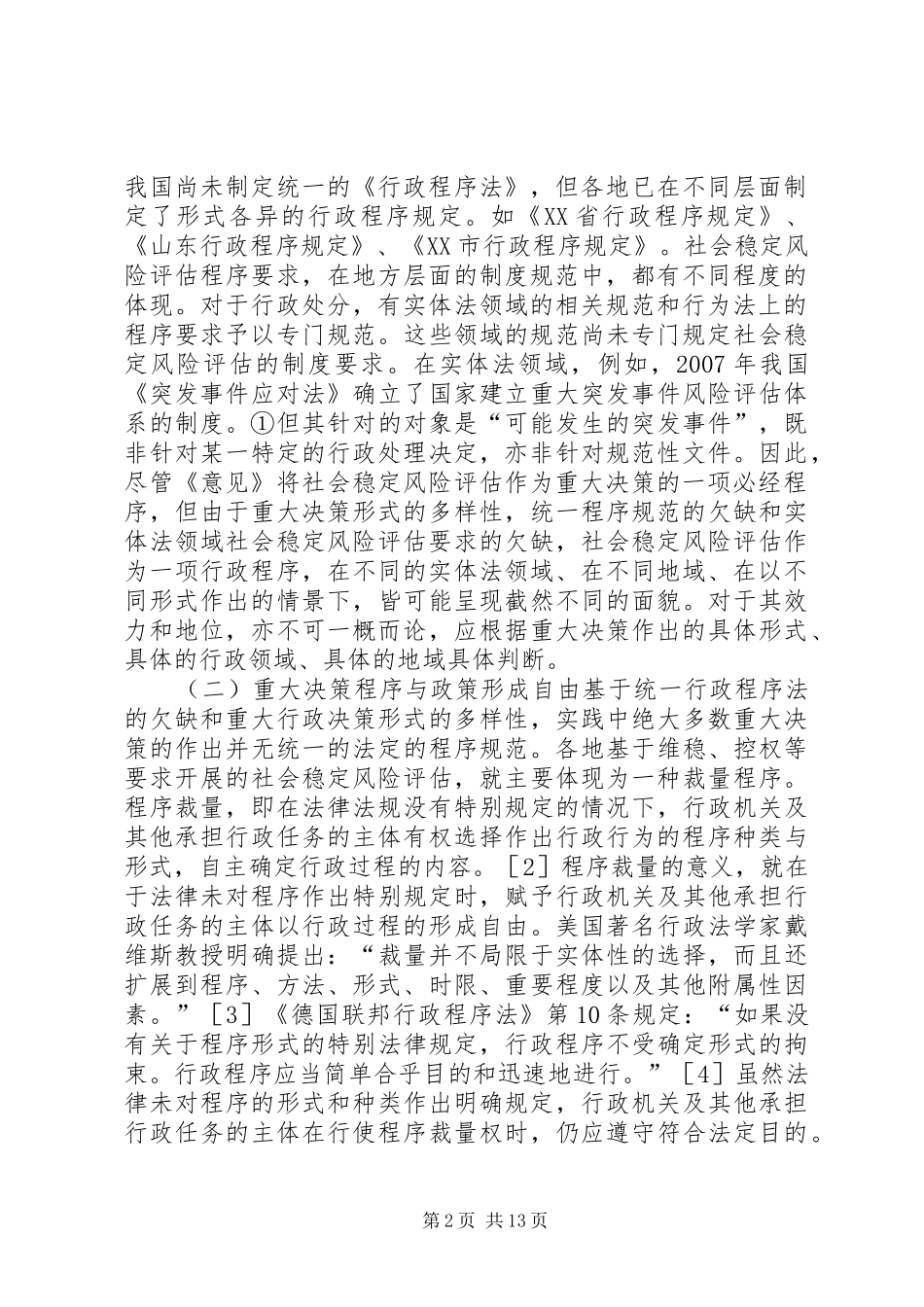略论风险社会的决策科学与民主研究风险评估与重大决策程序在传统的行政法治框架下,行政程序主要源于制定法规范的明确要求。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行政程序制度,将行政过程纳入民主化、理性化的轨道,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重要使命,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1]3而且现代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行政程序,应当是体现政府守法、民主参与、理性决策、公开公正之精神的“现代行政程序”,而不是行政系统内部用于层级控制、请示汇报的办事规则和行政手册。[1]3在此意义上,作为体现现代法治精神之行政程序,并不只是作为行政权运行载体的时序、步骤、方法,而更是基于法规范要求,体现民主参与、沟通理性等现代价值的法定程序。(一)重大决策的形式与程序规范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我国,重大决策主要通过各级政府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出,重大决策程序因此也主要体现为行政程序。①尽管《意见》已经明确了重大决策的五道必经程序,但《意见》毕竟不具有直接的法规范效力,其对于重大决策的制定也只能依据行政系统的上下级命令而具有事实上的指导效力。在风险评估程序未为各领域的实体法和行为法转化以前,风险评估只是行政机关实现决策理性的一种自我规制程序,不能产生具有对外效力的法规范效果。重大决策并非一个性质明确的法律概念。对于何为重大决策,学理上和实务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各地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具体办法,对于何为重大决策,作出了一些细化规定,内容大同小异。②从“重大决策”的内涵来看,其主要是从决策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判定,而非决策的具体形式。而行政程序,通常是以行为的具体形式作为规范对象,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重大决策既可能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呈现,亦有可能以行政处分的方式作出(如重大项目的审批、许可等)。对于规范性文件,不少地方出台了专门的程序规范。尽管目前第1页共13页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各地已在不同层面制定了形式各异的行政程序规定。如《XX省行政程序规定》、《山东行政程序规定》、《XX市行政程序规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要求,在地方层面的制度规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对于行政处分,有实体法领域的相关规范和行为法上的程序要求予以专门规范。这些领域的规范尚未专门规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要求。在实体法领域,例如,2007年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了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的制度。①但其针对的对象是“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既非针对某一特定的行政处理决定,亦非针对规范性文件。因此,尽管《意见》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的一项必经程序,但由于重大决策形式的多样性,统一程序规范的欠缺和实体法领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的欠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项行政程序,在不同的实体法领域、在不同地域、在以不同形式作出的情景下,皆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对于其效力和地位,亦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重大决策作出的具体形式、具体的行政领域、具体的地域具体判断。(二)重大决策程序与政策形成自由基于统一行政程序法的欠缺和重大行政决策形式的多样性,实践中绝大多数重大决策的作出并无统一的法定的程序规范。各地基于维稳、控权等要求开展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就主要体现为一种裁量程序。程序裁量,即在法律法规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有权选择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种类与形式,自主确定行政过程的内容。[2]程序裁量的意义,就在于法律未对程序作出特别规定时,赋予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以行政过程的形成自由。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戴维斯教授明确提出:“裁量并不局限于实体性的选择,而且还扩展到程序、方法、形式、时限、重要程度以及其他附属性因素。”[3]《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10条规定:“如果没有关于程序形式的特别法律规定,行政程序不受确定形式的拘束。行政程序应当简单合乎目的和迅速地进行。”[4]虽然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