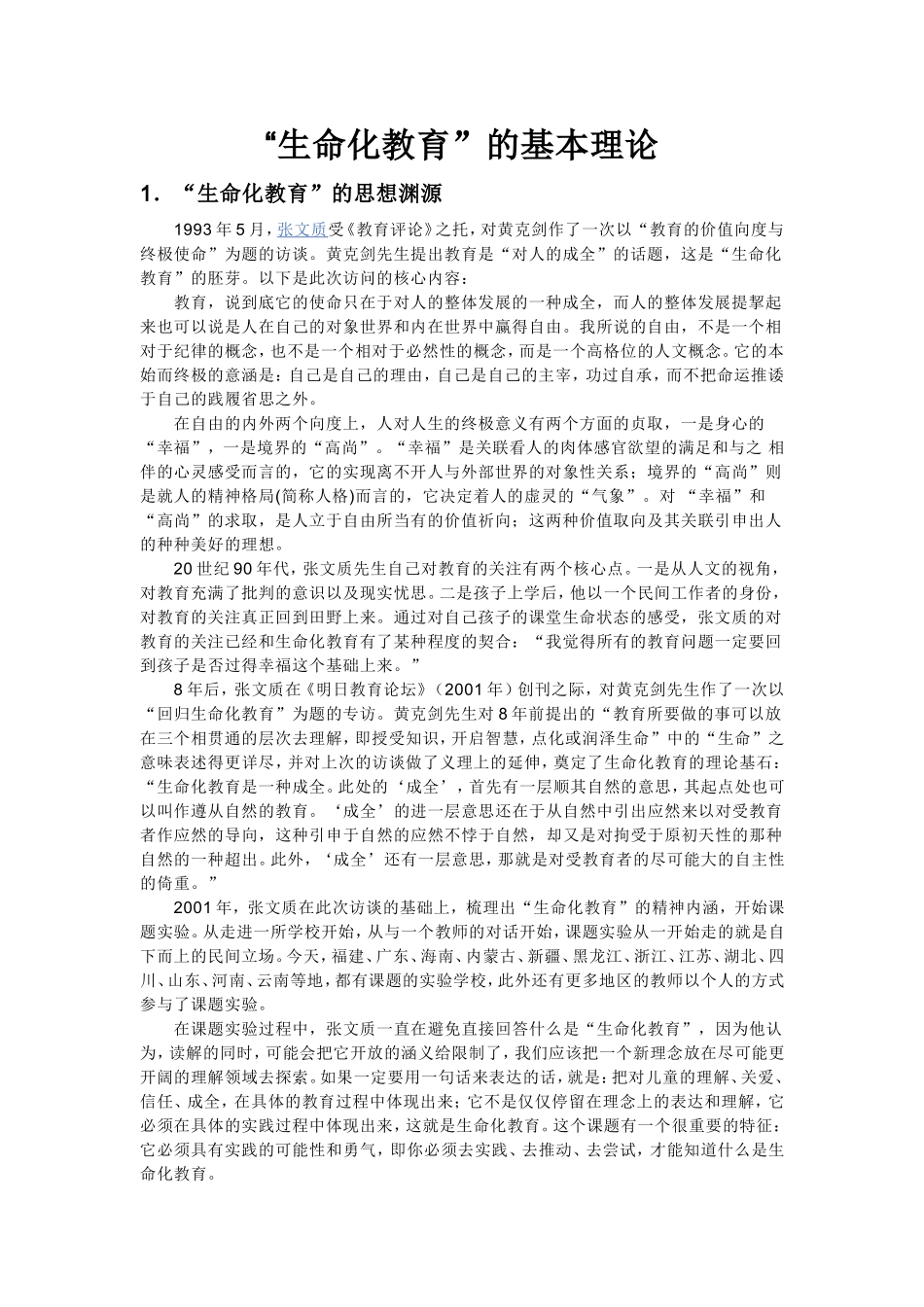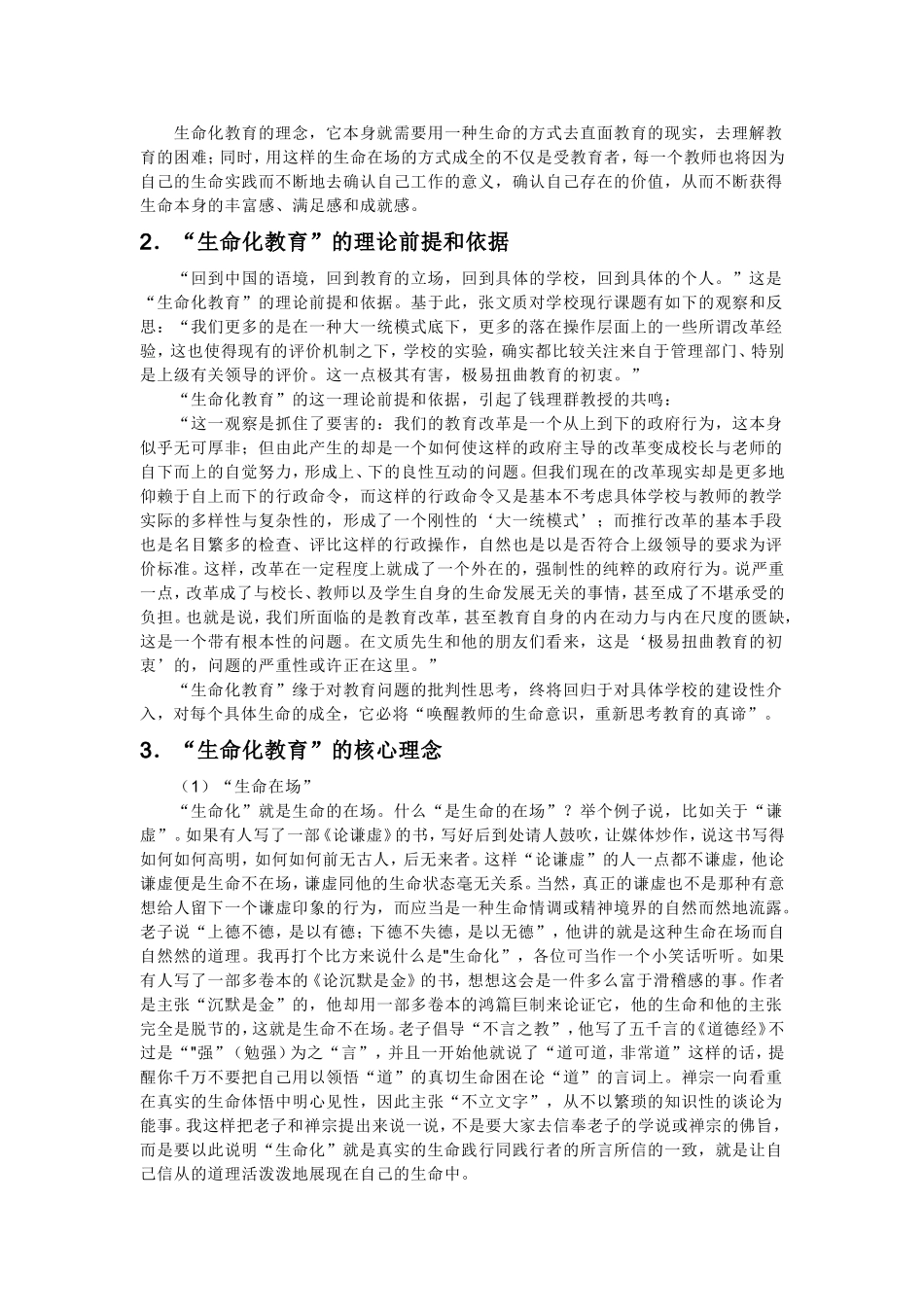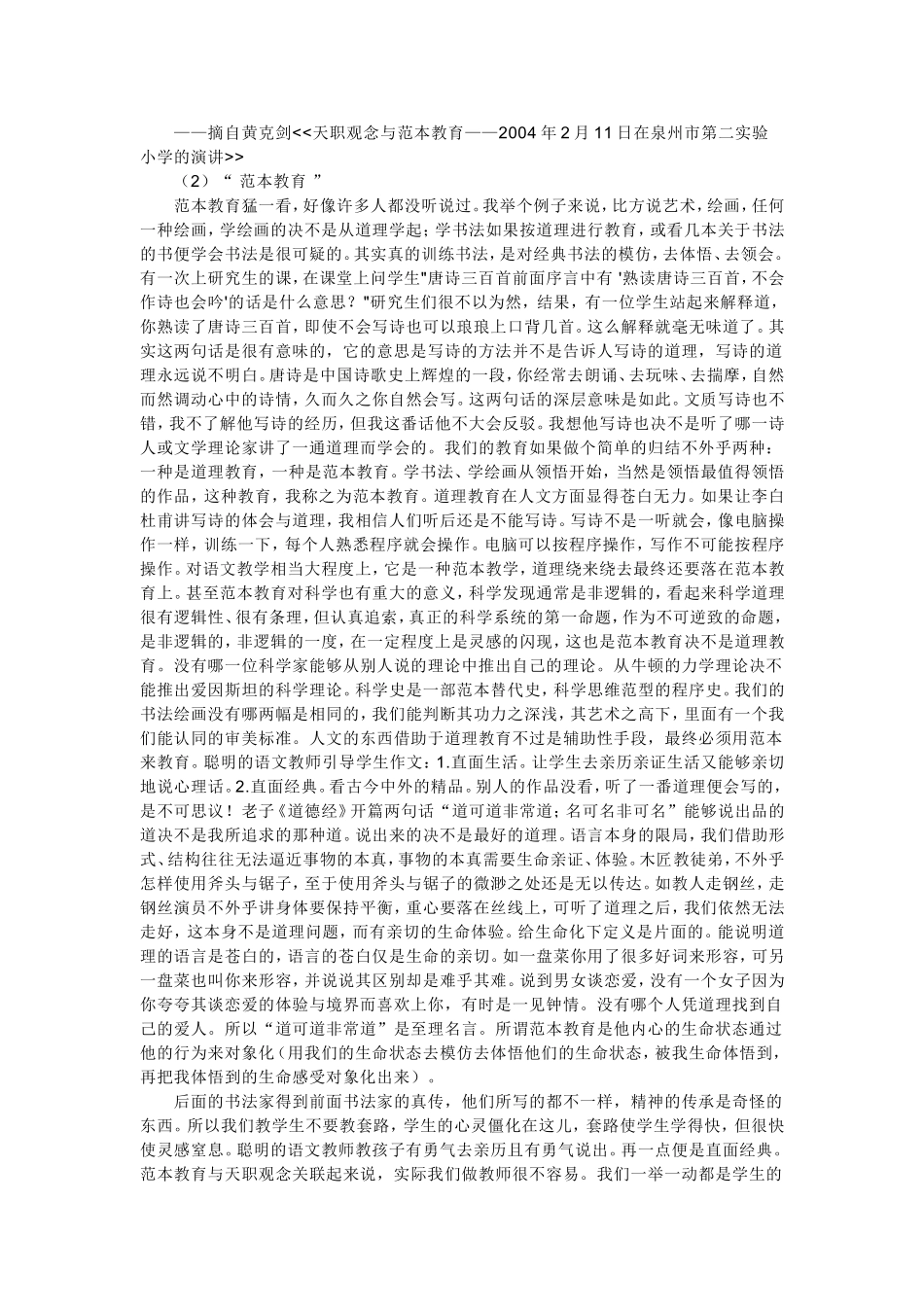“生命化教育”的基本理论1.“生命化教育”的思想渊源1993年5月,张文质受《教育评论》之托,对黄克剑作了一次以“教育的价值向度与终极使命”为题的访谈。黄克剑先生提出教育是“对人的成全”的话题,这是“生命化教育”的胚芽。以下是此次访问的核心内容:教育,说到底它的使命只在于对人的整体发展的一种成全,而人的整体发展提挈起来也可以说是人在自己的对象世界和内在世界中赢得自由。我所说的自由,不是一个相对于纪律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相对于必然性的概念,而是一个高格位的人文概念。它的本始而终极的意涵是:自己是自己的理由,自己是自己的主宰,功过自承,而不把命运推诿于自己的践履省思之外。在自由的内外两个向度上,人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有两个方面的贞取,一是身心的“幸福”,一是境界的“高尚”。“幸福”是关联看人的肉体感官欲望的满足和与之相伴的心灵感受而言的,它的实现离不开人与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境界的“高尚”则是就人的精神格局(简称人格)而言的,它决定着人的虚灵的“气象”。对“幸福”和“高尚”的求取,是人立于自由所当有的价值祈向;这两种价值取向及其关联引申出人的种种美好的理想。20世纪90年代,张文质先生自己对教育的关注有两个核心点。一是从人文的视角,对教育充满了批判的意识以及现实忧思。二是孩子上学后,他以一个民间工作者的身份,对教育的关注真正回到田野上来。通过对自己孩子的课堂生命状态的感受,张文质的对教育的关注已经和生命化教育有了某种程度的契合:“我觉得所有的教育问题一定要回到孩子是否过得幸福这个基础上来。”8年后,张文质在《明日教育论坛》(2001年)创刊之际,对黄克剑先生作了一次以“回归生命化教育”为题的专访。黄克剑先生对8年前提出的“教育所要做的事可以放在三个相贯通的层次去理解,即授受知识,开启智慧,点化或润泽生命”中的“生命”之意味表述得更详尽,并对上次的访谈做了义理上的延伸,奠定了生命化教育的理论基石:“生命化教育是一种成全。此处的‘成全’,首先有一层顺其自然的意思,其起点处也可以叫作遵从自然的教育。‘成全’的进一层意思还在于从自然中引出应然来以对受教育者作应然的导向,这种引申于自然的应然不悖于自然,却又是对拘受于原初天性的那种自然的一种超出。此外,‘成全’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对受教育者的尽可能大的自主性的倚重。”2001年,张文质在此次访谈的基础上,梳理出“生命化教育”的精神内涵,开始课题实验。从走进一所学校开始,从与一个教师的对话开始,课题实验从一开始走的就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立场。今天,福建、广东、海南、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山东、河南、云南等地,都有课题的实验学校,此外还有更多地区的教师以个人的方式参与了课题实验。在课题实验过程中,张文质一直在避免直接回答什么是“生命化教育”,因为他认为,读解的同时,可能会把它开放的涵义给限制了,我们应该把一个新理念放在尽可能更开阔的理解领域去探索。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表达的话,就是:把对儿童的理解、关爱、信任、成全,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体现出来;它不是仅仅停留在理念上的表达和理解,它必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这就是生命化教育。这个课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必须具有实践的可能性和勇气,即你必须去实践、去推动、去尝试,才能知道什么是生命化教育。生命化教育的理念,它本身就需要用一种生命的方式去直面教育的现实,去理解教育的困难;同时,用这样的生命在场的方式成全的不仅是受教育者,每一个教师也将因为自己的生命实践而不断地去确认自己工作的意义,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不断获得生命本身的丰富感、满足感和成就感。2.“生命化教育”的理论前提和依据“回到中国的语境,回到教育的立场,回到具体的学校,回到具体的个人。”这是“生命化教育”的理论前提和依据。基于此,张文质对学校现行课题有如下的观察和反思:“我们更多的是在一种大一统模式底下,更多的落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些所谓改革经验,这也使得现有的评价机制之下,学校的实验,确实都比较关注来自于管理部门、特别是上级有关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