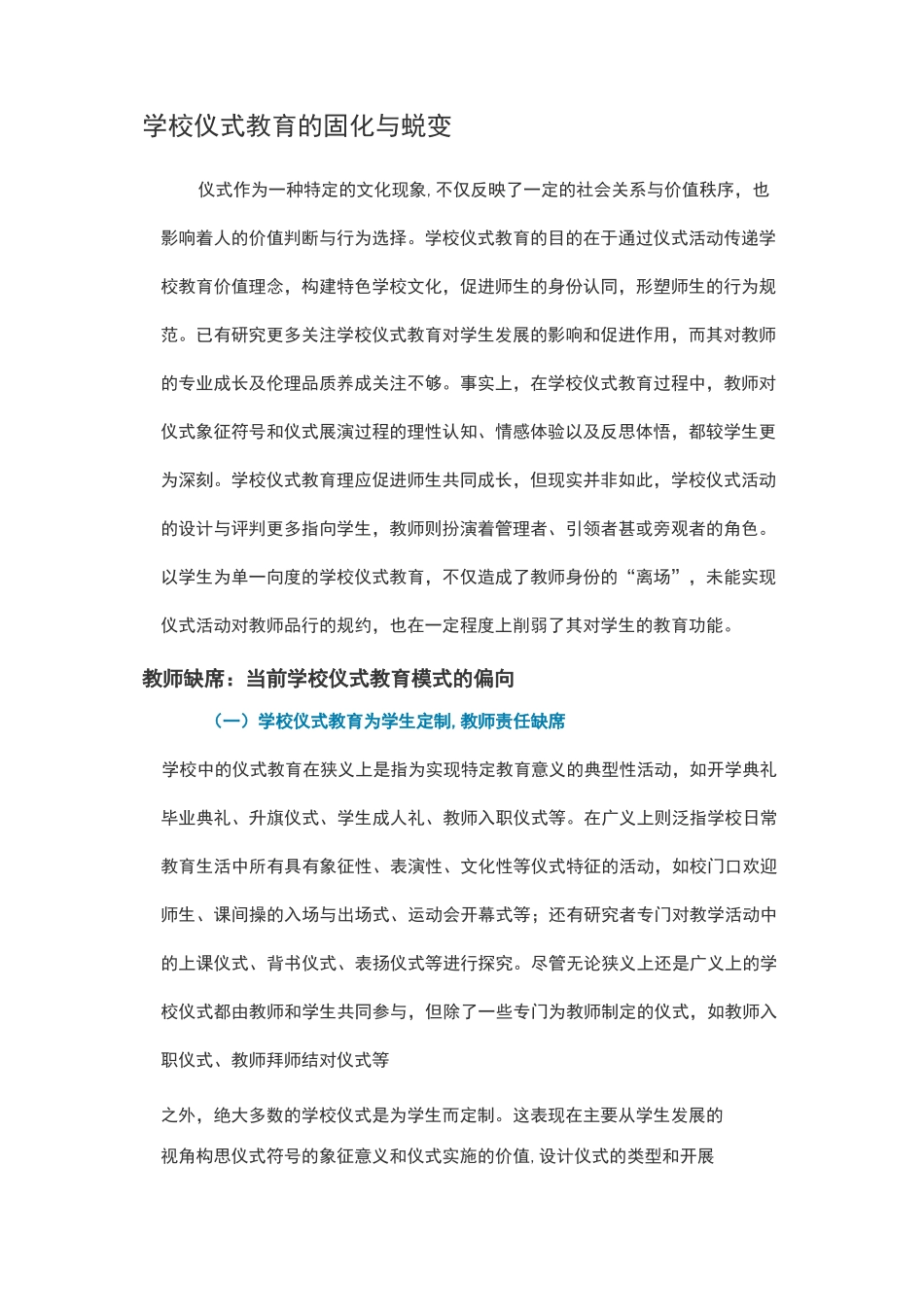学校仪式教育的固化与蜕变仪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不仅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与价值秩序,也影响着人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学校仪式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仪式活动传递学校教育价值理念,构建特色学校文化,促进师生的身份认同,形塑师生的行为规范。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学校仪式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而其对教师的专业成长及伦理品质养成关注不够。事实上,在学校仪式教育过程中,教师对仪式象征符号和仪式展演过程的理性认知、情感体验以及反思体悟,都较学生更为深刻。学校仪式教育理应促进师生共同成长,但现实并非如此,学校仪式活动的设计与评判更多指向学生,教师则扮演着管理者、引领者甚或旁观者的角色。以学生为单一向度的学校仪式教育,不仅造成了教师身份的“离场”,未能实现仪式活动对教师品行的规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学生的教育功能。教师缺席:当前学校仪式教育模式的偏向(一)学校仪式教育为学生定制,教师责任缺席学校中的仪式教育在狭义上是指为实现特定教育意义的典型性活动,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升旗仪式、学生成人礼、教师入职仪式等。在广义上则泛指学校日常教育生活中所有具有象征性、表演性、文化性等仪式特征的活动,如校门口欢迎师生、课间操的入场与出场式、运动会开幕式等;还有研究者专门对教学活动中的上课仪式、背书仪式、表扬仪式等进行探究。尽管无论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的学校仪式都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但除了一些专门为教师制定的仪式,如教师入职仪式、教师拜师结对仪式等之外,绝大多数的学校仪式是为学生而定制。这表现在主要从学生发展的视角构思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仪式实施的价值,设计仪式的类型和开展程式;仪式展演进程中,更关注学生是否遵从仪式行为规范;对仪式教育效果的衡量,更关注学生是否认同仪式蕴含的学校价值文化,是否达成规约学生行为的目的。与之相应,为学生定制的仪式教育活动更强调学生的主体责任,而淡化了教师的仪式责任,教师虽然处于仪式活动场域,但并未深刻认识到自身在仪式活动中应有的情感体验和行为规范,从而自觉接受仪式行为的规约。教师责任缺席的学校仪式教育弱化了教师的仪式感,使仪式教育功能局限于单一的学生指向。(二)学校仪式教育中教师"他者”身份显著,"自我”身份离场作为学校仪式活动的有机构成主体,教师兼有“自我”和“他者”的双重身份。以“自我”身份存在的教师,与学生共同感知仪式文化熏染、产生仪式情感体验、接受仪式行为规约,不仅借此形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更成为学校教育理念和价值文化的示范者、引领者和传播者。以“他者”身份存在的教师主要扮演三种角色。一是仪式活动的设计者,既负责设计突显学校文化传统和育人特色的典型仪式活动,也负责设计具有班级文化特色的仪式活动。二是仪式活动的组织者,负责引导、组织学生,以保障仪式活动的有序进行。三是仪式活动的评价者,负责对学生在仪式活动中的表现及活动后的变化作出评判。学校仪式实践中,教师往往尽职尽责地履行“他者”身份的职责,而“遗忘”了仪式活动场域中“自我”身份的存在,这一方面源于为学生定制的仪式活动设计将教师排除在外,造成教师“自我”身份的“被动”离场。另一方面,教师在仪式活动中更易认同甚至享受仪式符号权力,制止学生的不当仪式行为,而缺乏对自身仪式行为的自觉审视,这属于教师"自我”身份的“主动”离场。久而久之,仪式活动便固化为与教师无关的学生仪式展演。(三)学校仪式教育单一向度传递,教师成长缺失教师缺席的仪式教育显性存在,而这似乎长期得到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认可,成为学校仪式文化的一种默许假设,具有不可对抗性和无可争议性。这种公众默许会在潜意识中引导成员的行为,告诉他们如何直觉、思考,该注意什么,事情的意义如何,情绪上有何反应,采取何种行动等。于是,学校的仪式教育便呈现这样一种样态:学校管理者关注如何设计和实施更具时代性、创新性、校本化及育人价值的仪式活动,以展示学校的文化特色;教师关注如何组织、实施好仪式活动,以体现其对学生的教育功能;学生及家长则恪守学校要求,配合完成仪式活动任务。这种单一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