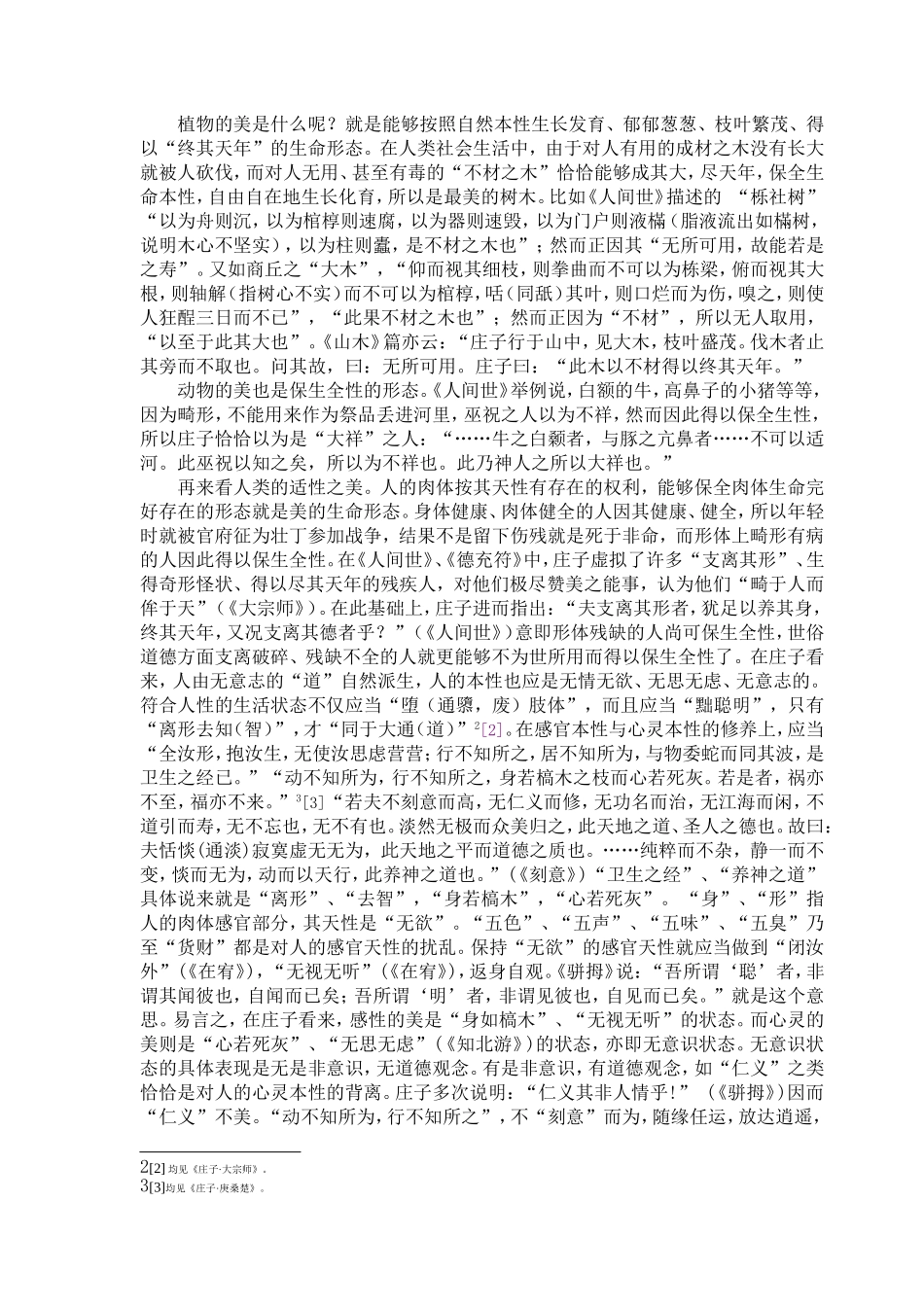庄子“适性为美”思想的生态美学意义2011年5月14日22:19庄子认为,美并不仅仅是人的专利,天下万物都有自己的美,这种美就是万物对自己生命本性的顺应,或者说是物种本性的伸张,这就叫“适性为美”;物性不一,因而物种的美也多种多样,千万不可一概而论,以此羡彼,“适他之适”,“役人之役”更不能以此求彼,按自己的审美标准去对待、强求其他物种的美,取代其他物种的审美尺度;在此基础上,庄子主张站在不同物种生命本性的立场,追求和维护天下万物顺应各自本性之美的共生共在,达到天人和谐,万物共荣。庄子的“适性为美”思想,实开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先河。在他之后,西晋郭象作《庄子注》,东晋支遁作《逍遥游论》,进一步发展了其“适性为美”思想,北齐刘昼对此也有所丰富,对我们今天讨论生态美学颇有启示、参考意义。一庄子作为老子的精神传人,其美学思想首先表现为对老子美学的继承。老子认为大道至美,“孔德之容,唯道是从”1[1],庄子则借老子之口进一步发挥说:“游心于物之初”的“道”,即“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以下只注篇名)。“道”在物体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其自然本性的“性”。老子的得道之美,到庄子手中就改造为适性之美。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正面的表述叫做“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情”,实也。“性命之情”,即“性命之实”的意思。“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也就是顺应、切合生命本性之实的意思。庄子说:“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正正”,曹础基《庄子浅注》认为系“至正”之误。联系上文批评杨朱、墨子“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曹说可从。庄子认为,那最完美的“至正”形态,就是不失物种的生命本性之实。庄子又说:“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臧”是与“仁义”对待的一个道德名词,约相当于“善”。什么是“善”呢?不是“仁义”,而是“任其性命之情”。而“善”可以带来情感上的“美”,所以“任其性命之情”亦可视为庄子对“美”的界定。《在宥》篇指出:“且夫说(通悦)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注视,注重)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犭仓囊而乱天下也。”庄子意在说明,当天下人都能“安其性命之情”时,“明”、“聪”、“知(智)”等“八者”可有可无,即便存在,也不会使人失性;当天下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时,这“八者”的存在恰恰足以扰乱天下。而当时的社会正是人人“不安其性命之情”的社会,所以不应允许这扰乱人性的“八者”存在。总之,物种符合自己生命本性的那种状态,就是美的形态。在《骈拇》、《大宗师》篇中,庄子批评社会上常见的“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的现象,强调物种“自适其适”的美。联系整个《庄子》的论述,庄子所说的“自适其适”的“自”不仅指人,而是泛指一切生物,主要包括植物、动物和人三类。于是物种的适性之美,就表现为植物、动物、人的保生全性之美。1[1]祁志祥:《老子美学:“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植物的美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按照自然本性生长发育、郁郁葱葱、枝叶繁茂、得以“终其天年”的生命形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由于对人有用的成材之木没有长大就被人砍伐,而对人无用、甚至有毒的“不材之木”恰恰能够成其大,尽天年,保全生命本性,自由自在地生长化育,所以是最美的树木。比如《人间世》描述的“栎社树”“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脂液流出如樠树,说明木心不坚实),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然而正因其“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又如商丘之“大木”,“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指树心不实)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同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