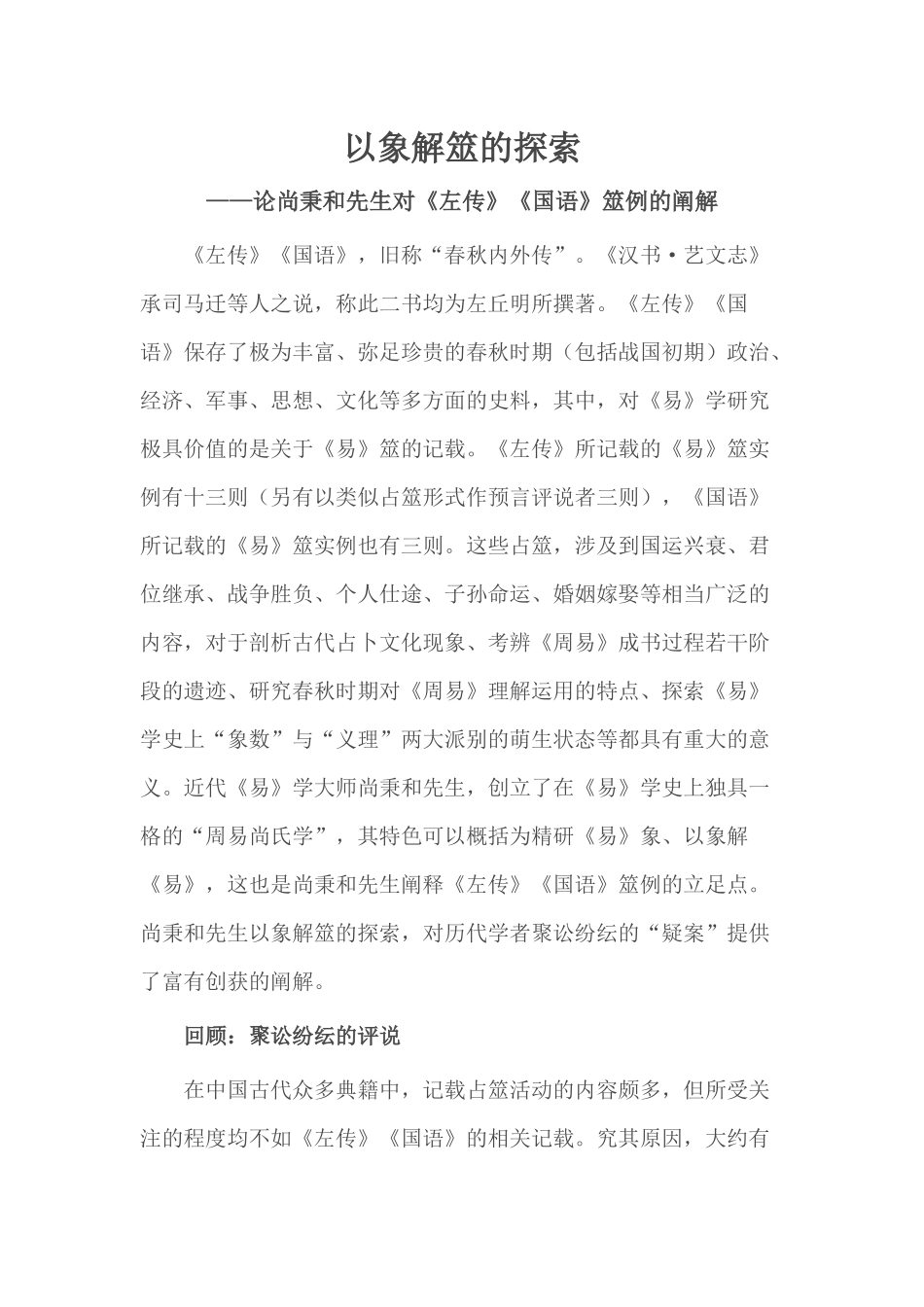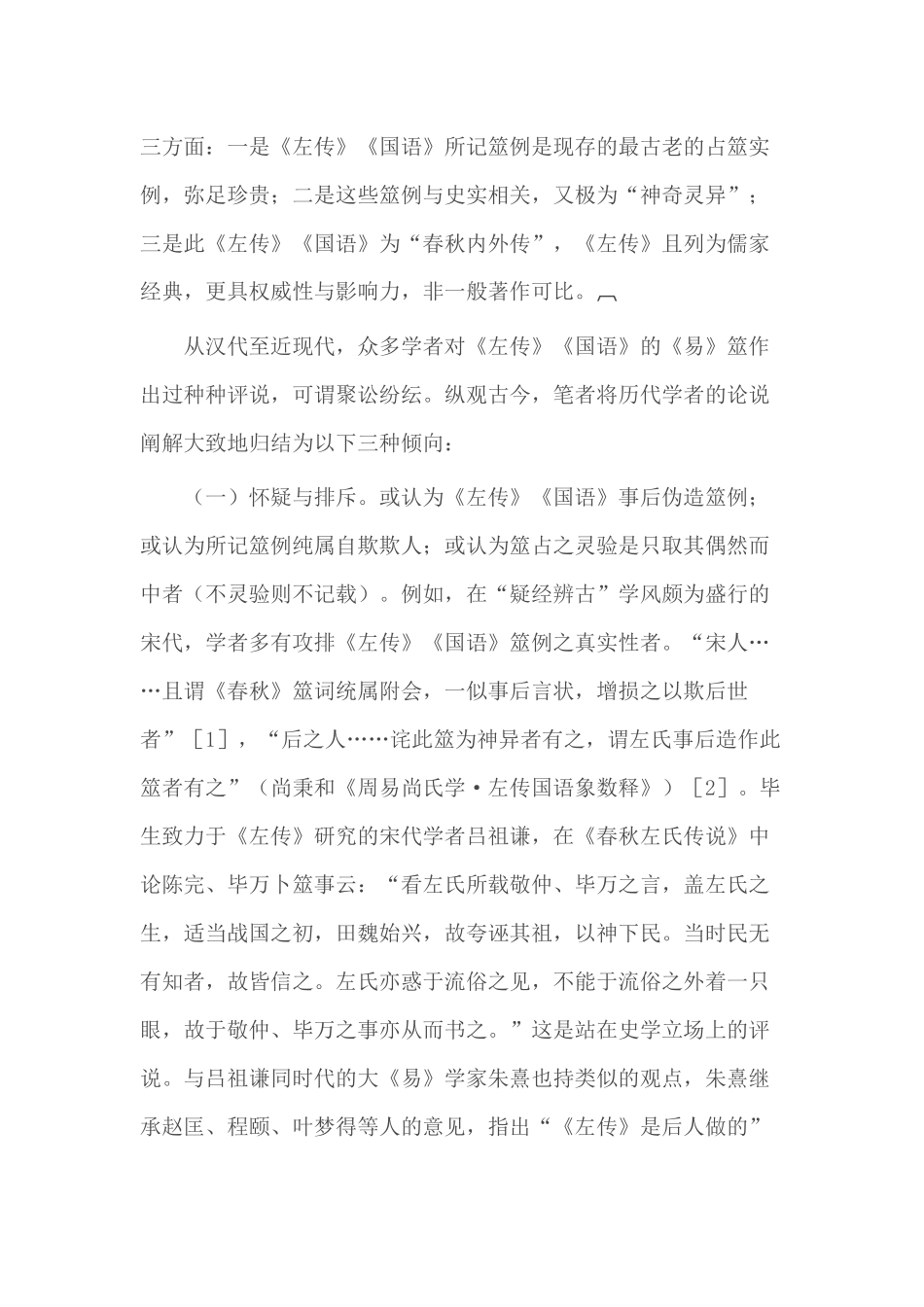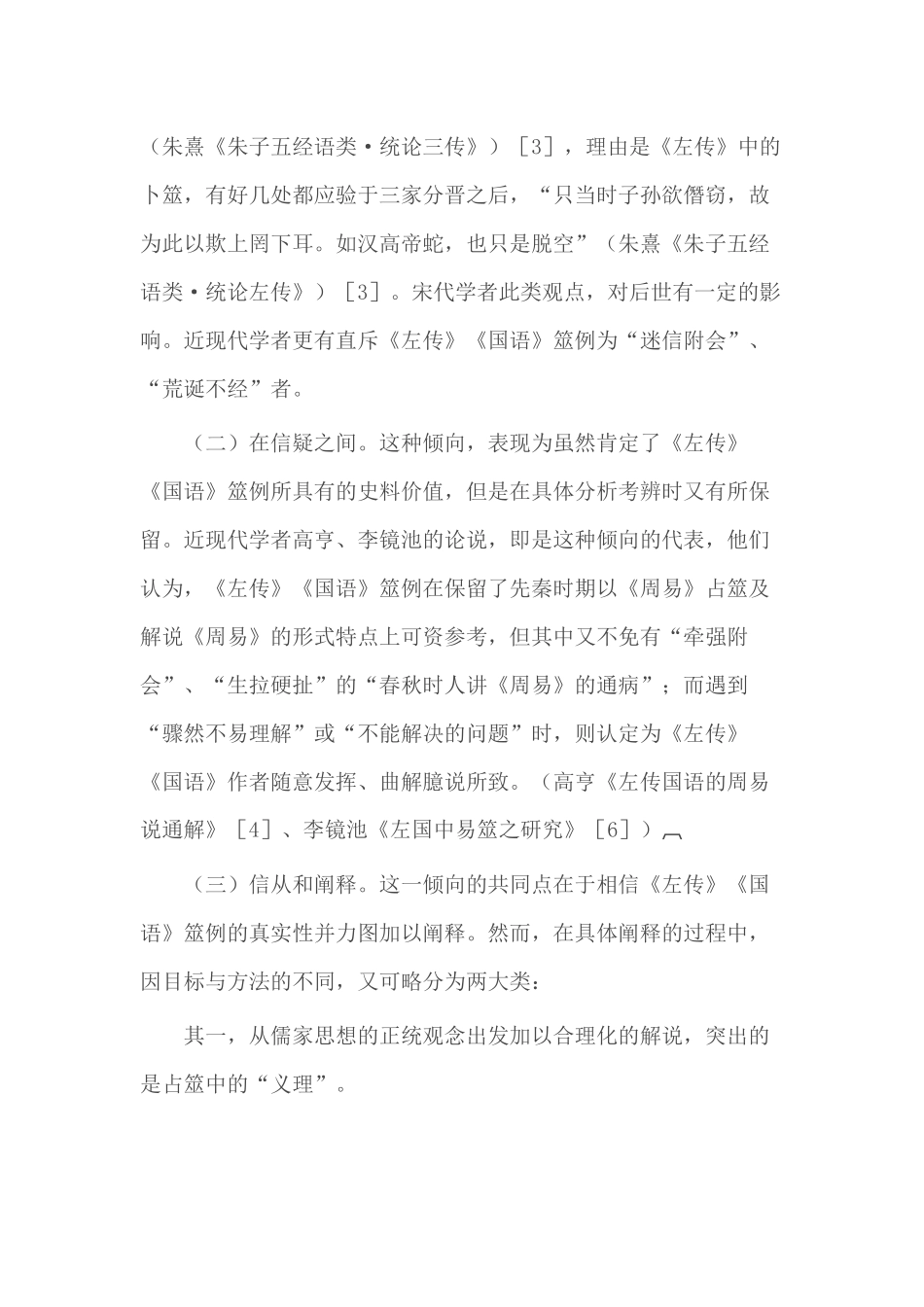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左传》《国语》,旧称“春秋内外传”。《汉书·艺文志》承司马迁等人之说,称此二书均为左丘明所撰著。《左传》《国语》保存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春秋时期(包括战国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史料,其中,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是关于《易》筮的记载。《左传》所记载的《易》筮实例有十三则(另有以类似占筮形式作预言评说者三则),《国语》所记载的《易》筮实例也有三则。这些占筮,涉及到国运兴衰、君位继承、战争胜负、个人仕途、子孙命运、婚姻嫁娶等相当广泛的内容,对于剖析古代占卜文化现象、考辨《周易》成书过程若干阶段的遗迹、研究春秋时期对《周易》理解运用的特点、探索《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两大派别的萌生状态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创立了在《易》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周易尚氏学”,其特色可以概括为精研《易》象、以象解《易》,这也是尚秉和先生阐释《左传》《国语》筮例的立足点。尚秉和先生以象解筮的探索,对历代学者聚讼纷纭的“疑案”提供了富有创获的阐解。回顾:聚讼纷纭的评说在中国古代众多典籍中,记载占筮活动的内容颇多,但所受关注的程度均不如《左传》《国语》的相关记载。究其原因,大约有三方面:一是《左传》《国语》所记筮例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占筮实例,弥足珍贵;二是这些筮例与史实相关,又极为“神奇灵异”;三是此《左传》《国语》为“春秋内外传”,《左传》且列为儒家经典,更具权威性与影响力,非一般著作可比。从汉代至近现代,众多学者对《左传》《国语》的《易》筮作出过种种评说,可谓聚讼纷纭。纵观古今,笔者将历代学者的论说阐解大致地归结为以下三种倾向:(一)怀疑与排斥。或认为《左传》《国语》事后伪造筮例;或认为所记筮例纯属自欺欺人;或认为筮占之灵验是只取其偶然而中者(不灵验则不记载)。例如,在“疑经辨古”学风颇为盛行的宋代,学者多有攻排《左传》《国语》筮例之真实性者。“宋人……且谓《春秋》筮词统属附会,一似事后言状,增损之以欺后世者”[1],“后之人……诧此筮为神异者有之,谓左氏事后造作此筮者有之”(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左传国语象数释》)[2]。毕生致力于《左传》研究的宋代学者吕祖谦,在《春秋左氏传说》中论陈完、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生,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这是站在史学立场上的评说。与吕祖谦同时代的大《易》学家朱熹也持类似的观点,朱熹继承赵匡、程颐、叶梦得等人的意见,指出“《左传》是后人做的”(朱熹《朱子五经语类·统论三传》)[3],理由是《左传》中的卜筮,有好几处都应验于三家分晋之后,“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耳。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朱熹《朱子五经语类·统论左传》)[3]。宋代学者此类观点,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近现代学者更有直斥《左传》《国语》筮例为“迷信附会”、“荒诞不经”者。(二)在信疑之间。这种倾向,表现为虽然肯定了《左传》《国语》筮例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但是在具体分析考辨时又有所保留。近现代学者高亨、李镜池的论说,即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们认为,《左传》《国语》筮例在保留了先秦时期以《周易》占筮及解说《周易》的形式特点上可资参考,但其中又不免有“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春秋时人讲《周易》的通病”;而遇到“骤然不易理解”或“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则认定为《左传》《国语》作者随意发挥、曲解臆说所致。(高亨《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4]、李镜池《左国中易筮之研究》[6])(三)信从和阐释。这一倾向的共同点在于相信《左传》《国语》筮例的真实性并力图加以阐释。然而,在具体阐释的过程中,因目标与方法的不同,又可略分为两大类:其一,从儒家思想的正统观念出发加以合理化的解说,突出的是占筮中的“义理”。杜预为其代表性人物。被称为“《左传》功臣”的西晋学者杜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