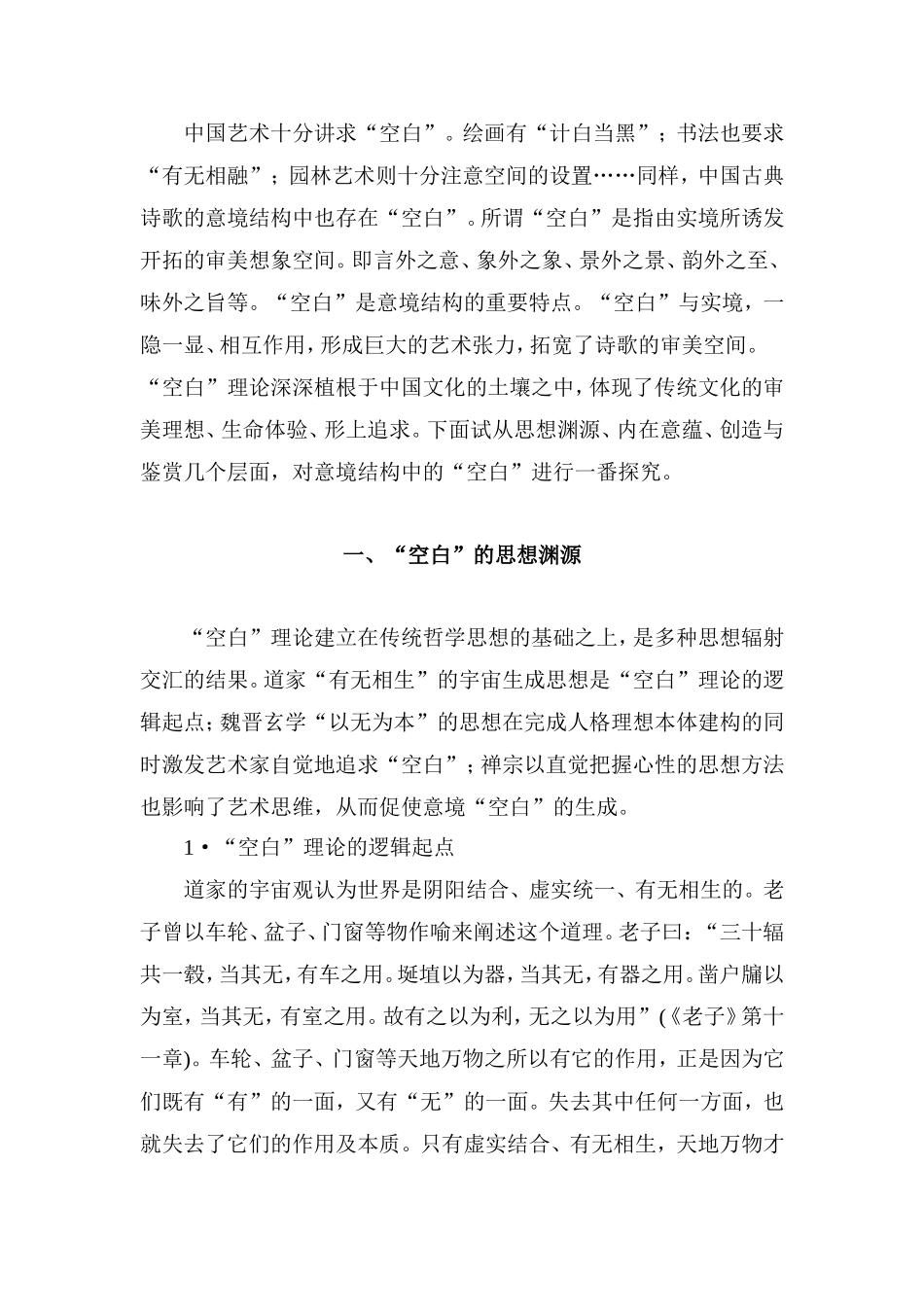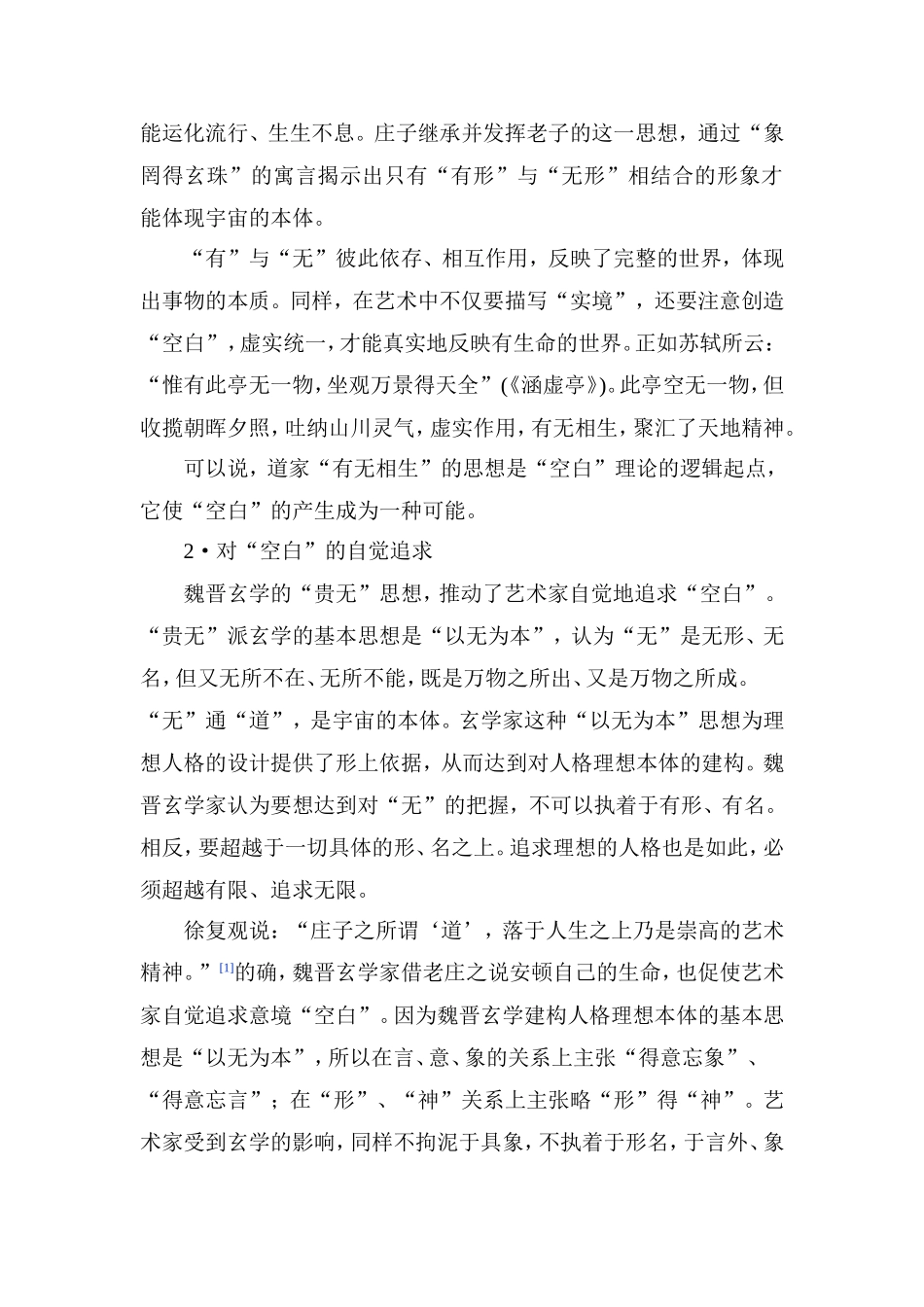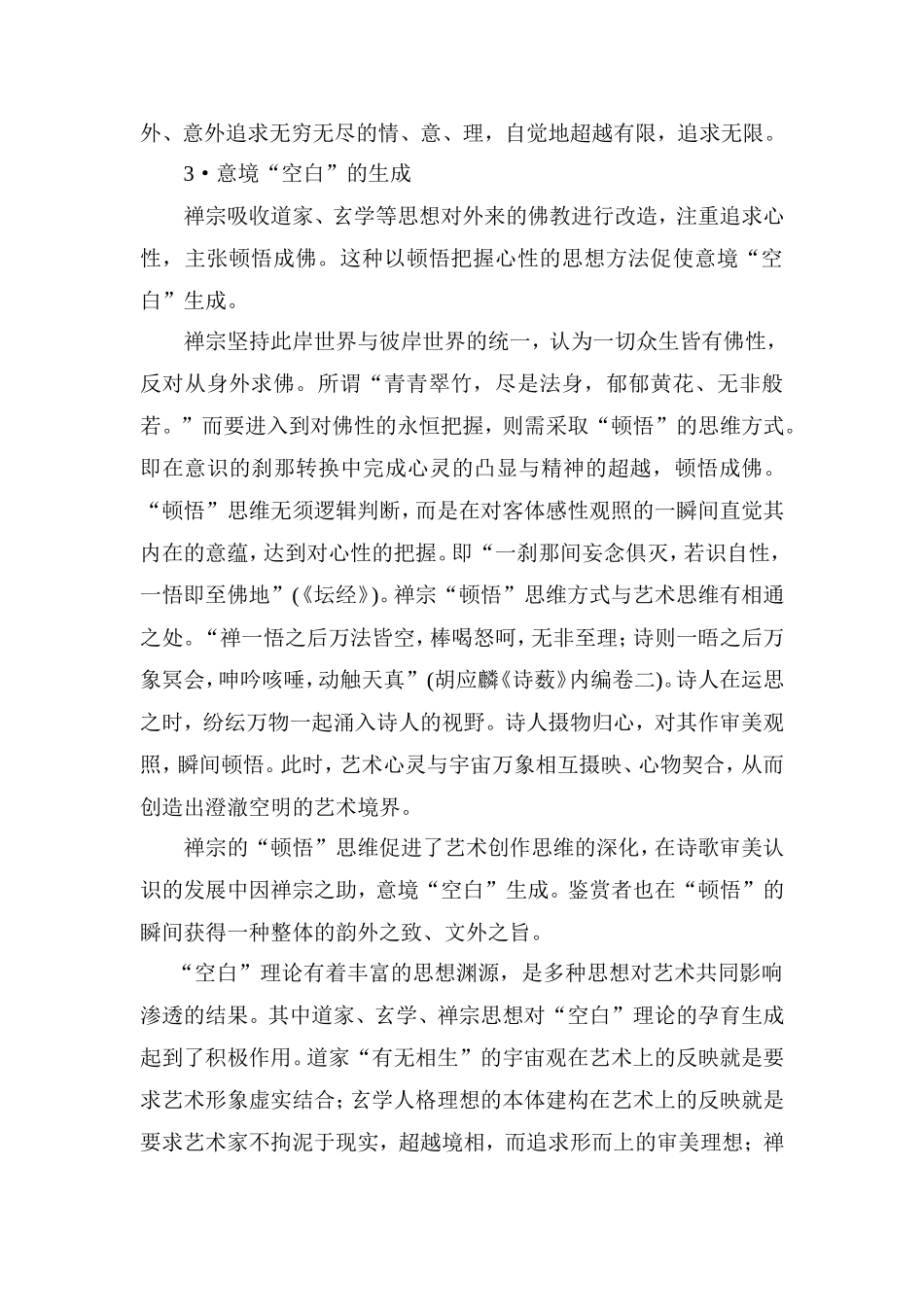中国艺术十分讲求“空白”。绘画有“计白当黑”;书法也要求“有无相融”;园林艺术则十分注意空间的设置……同样,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结构中也存在“空白”。所谓“空白”是指由实境所诱发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即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至、味外之旨等。“空白”是意境结构的重要特点。“空白”与实境,一隐一显、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拓宽了诗歌的审美空间。“空白”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生命体验、形上追求。下面试从思想渊源、内在意蕴、创造与鉴赏几个层面,对意境结构中的“空白”进行一番探究。一、“空白”的思想渊源“空白”理论建立在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是多种思想辐射交汇的结果。道家“有无相生”的宇宙生成思想是“空白”理论的逻辑起点;魏晋玄学“以无为本”的思想在完成人格理想本体建构的同时激发艺术家自觉地追求“空白”;禅宗以直觉把握心性的思想方法也影响了艺术思维,从而促使意境“空白”的生成。1·“空白”理论的逻辑起点道家的宇宙观认为世界是阴阳结合、虚实统一、有无相生的。老子曾以车轮、盆子、门窗等物作喻来阐述这个道理。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车轮、盆子、门窗等天地万物之所以有它的作用,正是因为它们既有“有”的一面,又有“无”的一面。失去其中任何一方面,也就失去了它们的作用及本质。只有虚实结合、有无相生,天地万物才能运化流行、生生不息。庄子继承并发挥老子的这一思想,通过“象罔得玄珠”的寓言揭示出只有“有形”与“无形”相结合的形象才能体现宇宙的本体。“有”与“无”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反映了完整的世界,体现出事物的本质。同样,在艺术中不仅要描写“实境”,还要注意创造“空白”,虚实统一,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正如苏轼所云:“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涵虚亭》)。此亭空无一物,但收揽朝晖夕照,吐纳山川灵气,虚实作用,有无相生,聚汇了天地精神。可以说,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是“空白”理论的逻辑起点,它使“空白”的产生成为一种可能。2·对“空白”的自觉追求魏晋玄学的“贵无”思想,推动了艺术家自觉地追求“空白”。“贵无”派玄学的基本思想是“以无为本”,认为“无”是无形、无名,但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既是万物之所出、又是万物之所成。“无”通“道”,是宇宙的本体。玄学家这种“以无为本”思想为理想人格的设计提供了形上依据,从而达到对人格理想本体的建构。魏晋玄学家认为要想达到对“无”的把握,不可以执着于有形、有名。相反,要超越于一切具体的形、名之上。追求理想的人格也是如此,必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徐复观说:“庄子之所谓‘道’,落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1]的确,魏晋玄学家借老庄之说安顿自己的生命,也促使艺术家自觉追求意境“空白”。因为魏晋玄学建构人格理想本体的基本思想是“以无为本”,所以在言、意、象的关系上主张“得意忘象”、“得意忘言”;在“形”、“神”关系上主张略“形”得“神”。艺术家受到玄学的影响,同样不拘泥于具象,不执着于形名,于言外、象外、意外追求无穷无尽的情、意、理,自觉地超越有限,追求无限。3·意境“空白”的生成禅宗吸收道家、玄学等思想对外来的佛教进行改造,注重追求心性,主张顿悟成佛。这种以顿悟把握心性的思想方法促使意境“空白”生成。禅宗坚持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统一,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反对从身外求佛。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而要进入到对佛性的永恒把握,则需采取“顿悟”的思维方式。即在意识的刹那转换中完成心灵的凸显与精神的超越,顿悟成佛。“顿悟”思维无须逻辑判断,而是在对客体感性观照的一瞬间直觉其内在的意蕴,达到对心性的把握。即“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禅宗“顿悟”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有相通之处。“禅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晤之后万象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