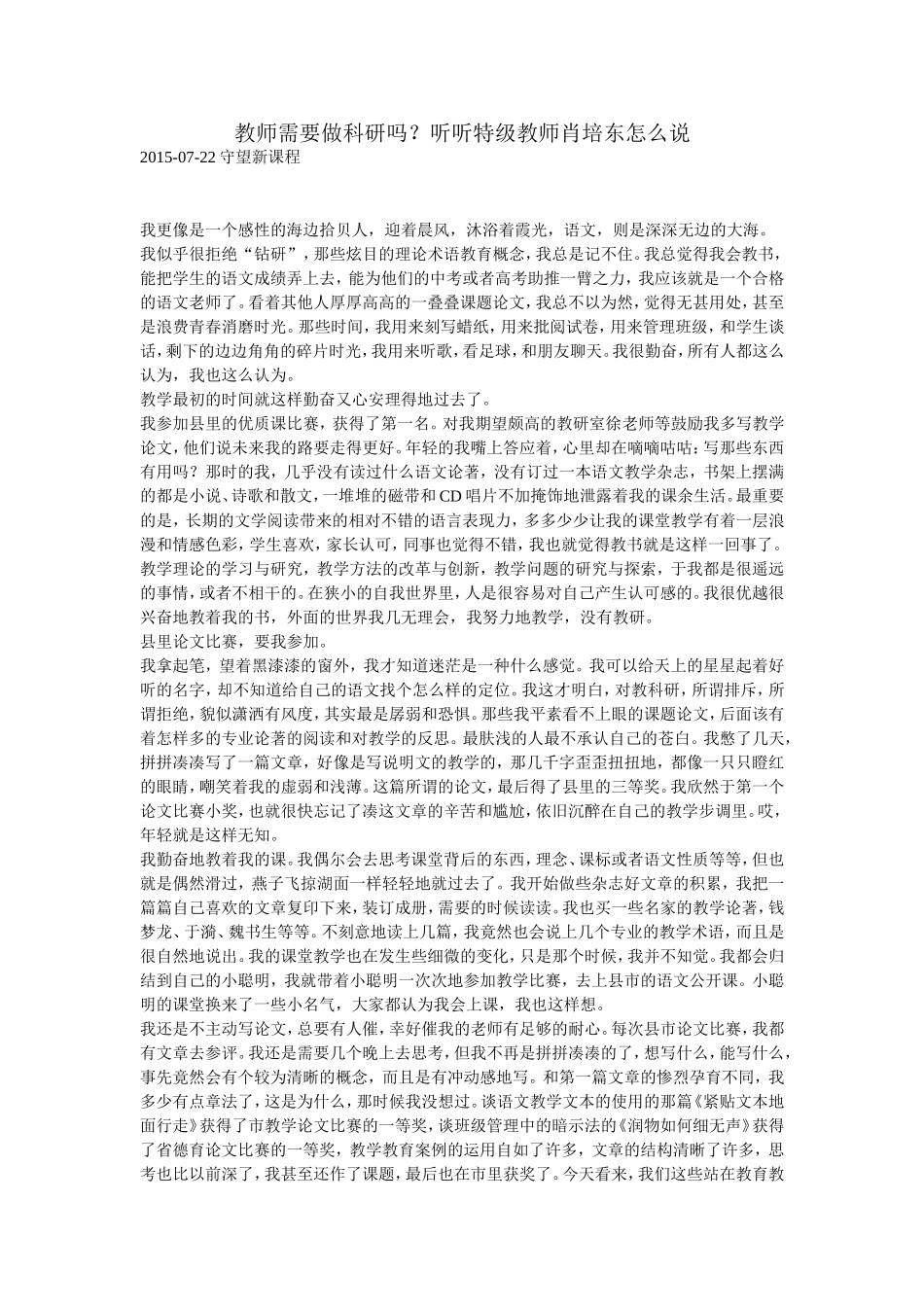教师需要做科研吗?听听特级教师肖培东怎么说2015-07-22守望新课程我更像是一个感性的海边拾贝人,迎着晨风,沐浴着霞光,语文,则是深深无边的大海。我似乎很拒绝“钻研”,那些炫目的理论术语教育概念,我总是记不住。我总觉得我会教书,能把学生的语文成绩弄上去,能为他们的中考或者高考助推一臂之力,我应该就是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了。看着其他人厚厚高高的一叠叠课题论文,我总不以为然,觉得无甚用处,甚至是浪费青春消磨时光。那些时间,我用来刻写蜡纸,用来批阅试卷,用来管理班级,和学生谈话,剩下的边边角角的碎片时光,我用来听歌,看足球,和朋友聊天。我很勤奋,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我也这么认为。教学最初的时间就这样勤奋又心安理得地过去了。我参加县里的优质课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对我期望颇高的教研室徐老师等鼓励我多写教学论文,他们说未来我的路要走得更好。年轻的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嘀嘀咕咕:写那些东西有用吗?那时的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语文论著,没有订过一本语文教学杂志,书架上摆满的都是小说、诗歌和散文,一堆堆的磁带和CD唱片不加掩饰地泄露着我的课余生活。最重要的是,长期的文学阅读带来的相对不错的语言表现力,多多少少让我的课堂教学有着一层浪漫和情感色彩,学生喜欢,家长认可,同事也觉得不错,我也就觉得教书就是这样一回事了。教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教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于我都是很遥远的事情,或者不相干的。在狭小的自我世界里,人是很容易对自己产生认可感的。我很优越很兴奋地教着我的书,外面的世界我几无理会,我努力地教学,没有教研。县里论文比赛,要我参加。我拿起笔,望着黑漆漆的窗外,我才知道迷茫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可以给天上的星星起着好听的名字,却不知道给自己的语文找个怎么样的定位。我这才明白,对教科研,所谓排斥,所谓拒绝,貌似潇洒有风度,其实最是孱弱和恐惧。那些我平素看不上眼的课题论文,后面该有着怎样多的专业论著的阅读和对教学的反思。最肤浅的人最不承认自己的苍白。我憋了几天,拼拼凑凑写了一篇文章,好像是写说明文的教学的,那几千字歪歪扭扭地,都像一只只瞪红的眼睛,嘲笑着我的虚弱和浅薄。这篇所谓的论文,最后得了县里的三等奖。我欣然于第一个论文比赛小奖,也就很快忘记了凑这文章的辛苦和尴尬,依旧沉醉在自己的教学步调里。哎,年轻就是这样无知。我勤奋地教着我的课。我偶尔会去思考课堂背后的东西,理念、课标或者语文性质等等,但也就是偶然滑过,燕子飞掠湖面一样轻轻地就过去了。我开始做些杂志好文章的积累,我把一篇篇自己喜欢的文章复印下来,装订成册,需要的时候读读。我也买一些名家的教学论著,钱梦龙、于漪、魏书生等等。不刻意地读上几篇,我竟然也会说上几个专业的教学术语,而且是很自然地说出。我的课堂教学也在发生些细微的变化,只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觉。我都会归结到自己的小聪明,我就带着小聪明一次次地参加教学比赛,去上县市的语文公开课。小聪明的课堂换来了一些小名气,大家都认为我会上课,我也这样想。我还是不主动写论文,总要有人催,幸好催我的老师有足够的耐心。每次县市论文比赛,我都有文章去参评。我还是需要几个晚上去思考,但我不再是拼拼凑凑的了,想写什么,能写什么,事先竟然会有个较为清晰的概念,而且是有冲动感地写。和第一篇文章的惨烈孕育不同,我多少有点章法了,这是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想过。谈语文教学文本的使用的那篇《紧贴文本地面行走》获得了市教学论文比赛的一等奖,谈班级管理中的暗示法的《润物如何细无声》获得了省德育论文比赛的一等奖,教学教育案例的运用自如了许多,文章的结构清晰了许多,思考也比以前深了,我甚至还作了课题,最后也在市里获奖了。今天看来,我们这些站在教育教学工作的最前线的教师,其实是有一个优势条件的,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科研选题。即便是以听课、评课为例,我们也可以利用观察来完成自己的某些研究。我的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很难说是教科研的成果,至多是我教学教育思考后的应急作业,只是不同于最初的苍白,我开始有意识地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