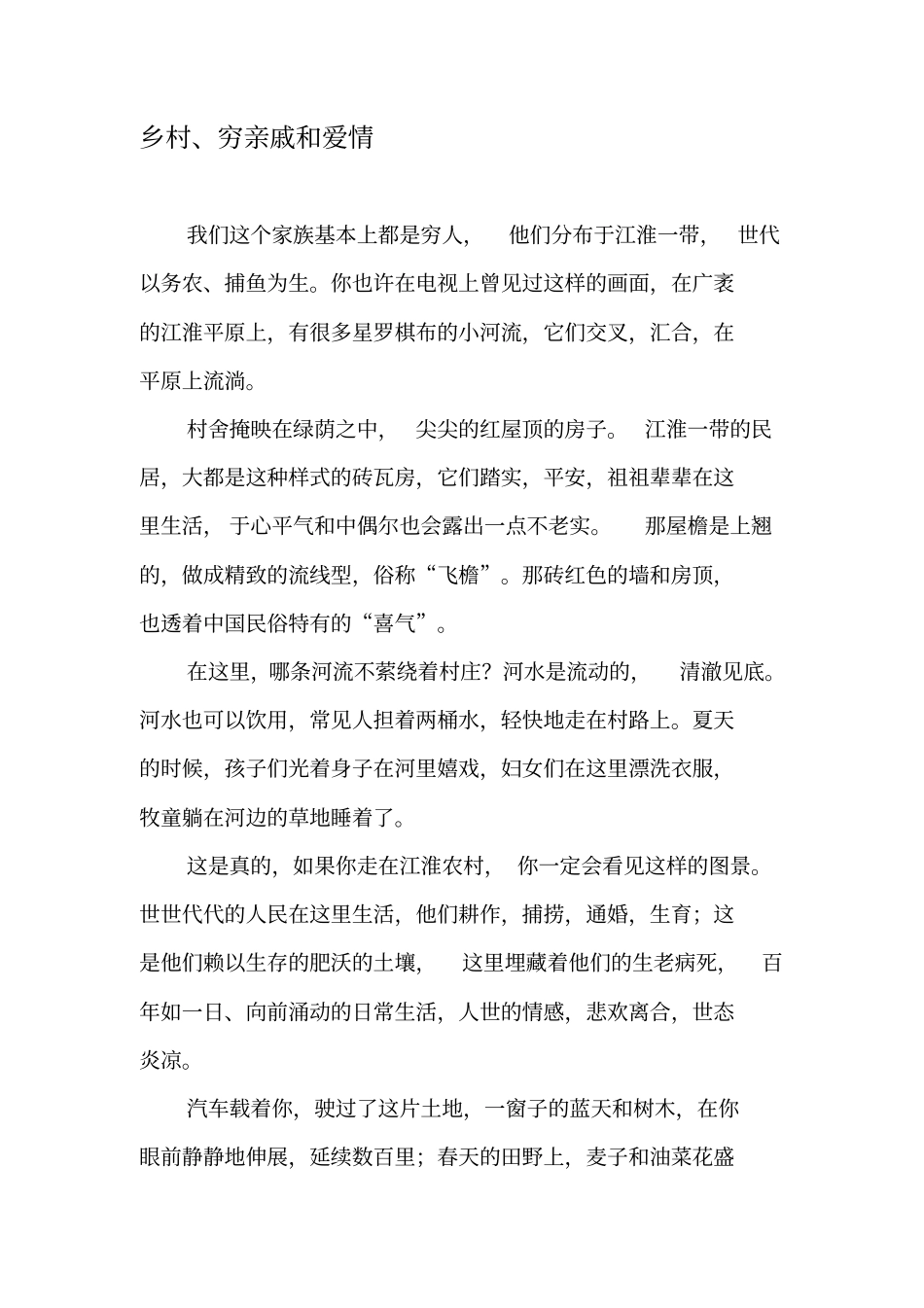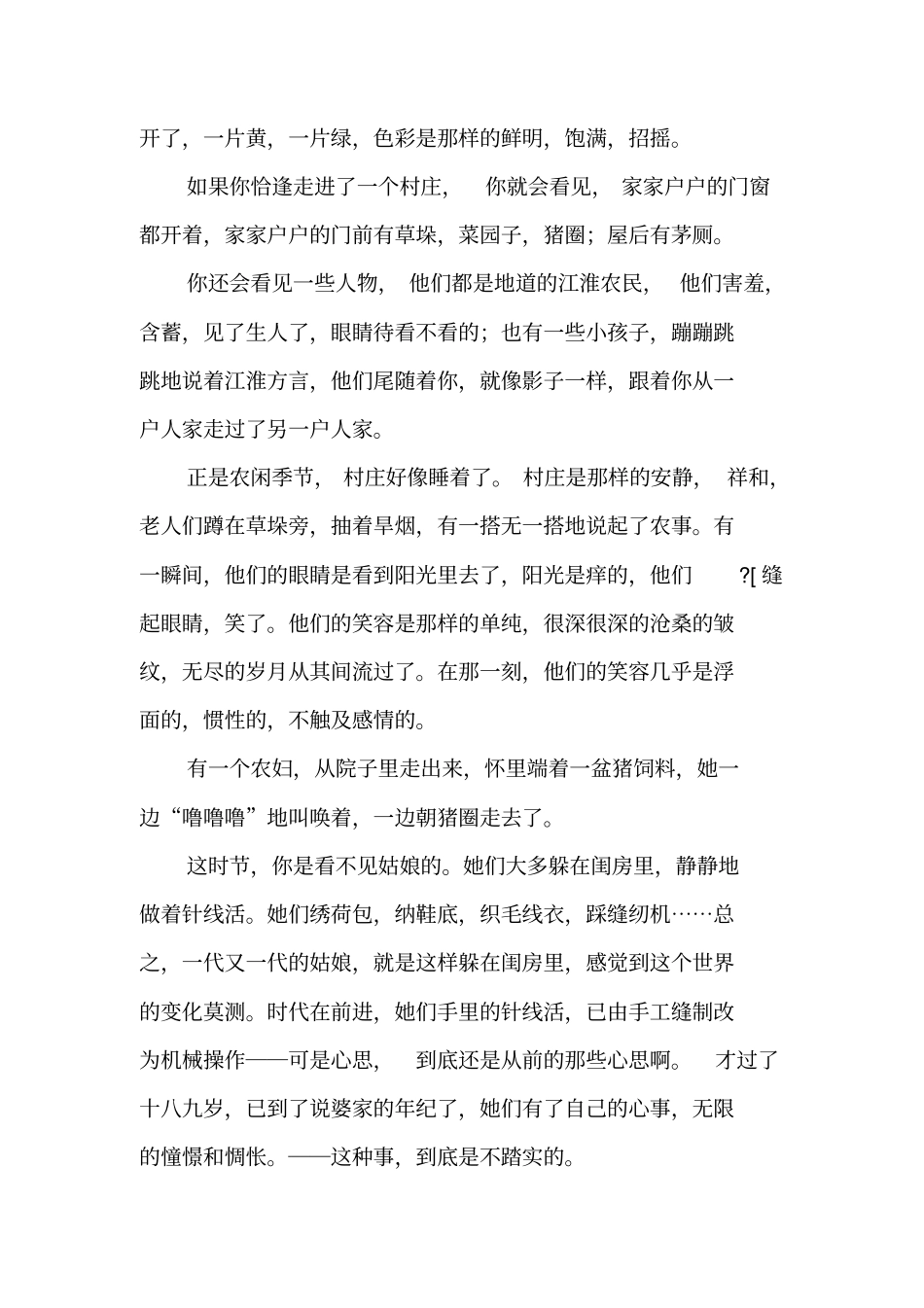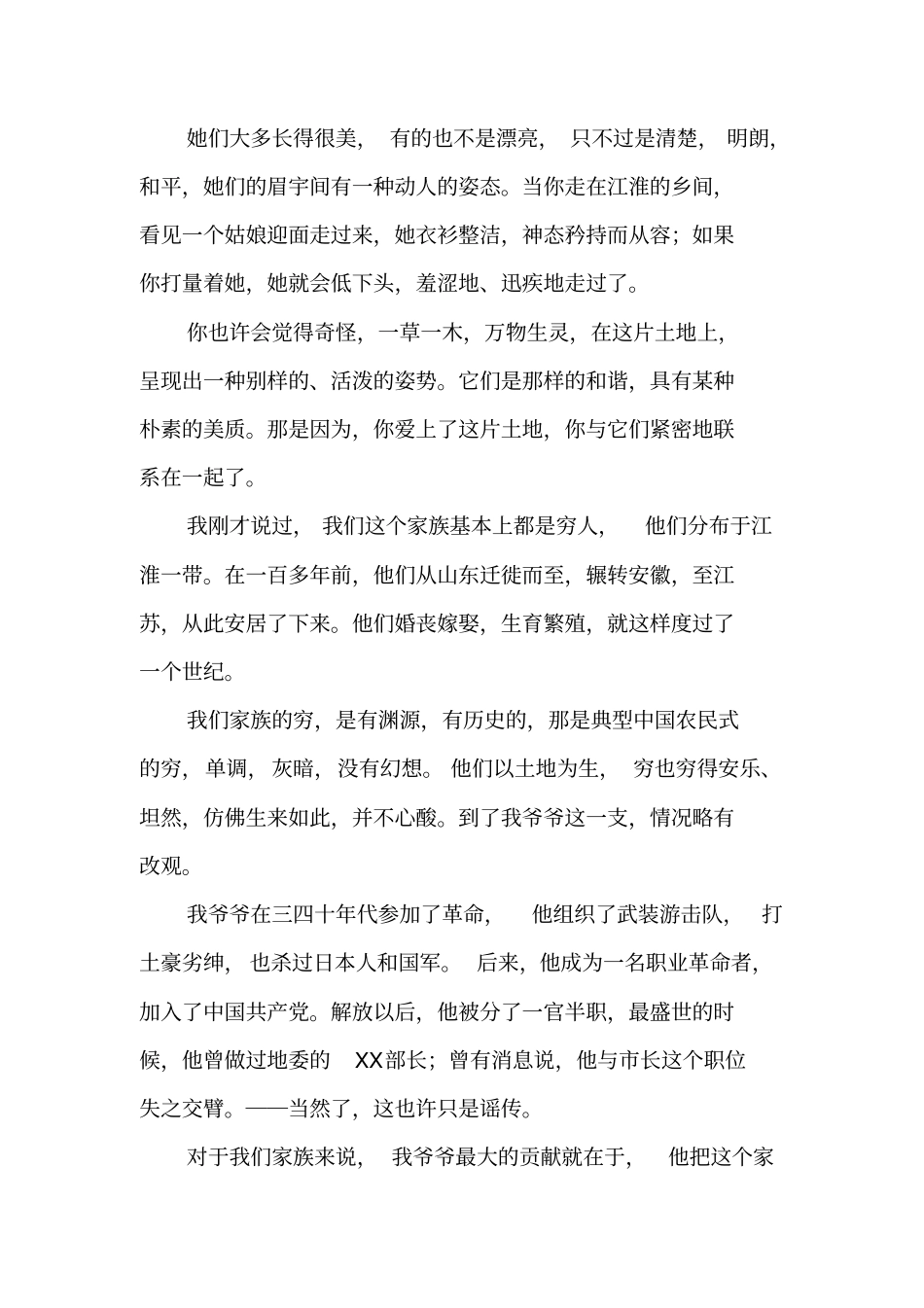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我们这个家族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们分布于江淮一带,世代以务农、捕鱼为生。你也许在电视上曾见过这样的画面,在广袤的江淮平原上,有很多星罗棋布的小河流,它们交叉,汇合,在平原上流淌。村舍掩映在绿荫之中,尖尖的红屋顶的房子。江淮一带的民居,大都是这种样式的砖瓦房,它们踏实,平安,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于心平气和中偶尔也会露出一点不老实。那屋檐是上翘的,做成精致的流线型,俗称“飞檐”。那砖红色的墙和房顶,也透着中国民俗特有的“喜气”。在这里,哪条河流不萦绕着村庄?河水是流动的,清澈见底。河水也可以饮用,常见人担着两桶水,轻快地走在村路上。夏天的时候,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河里嬉戏,妇女们在这里漂洗衣服,牧童躺在河边的草地睡着了。这是真的,如果你走在江淮农村,你一定会看见这样的图景。世世代代的人民在这里生活,他们耕作,捕捞,通婚,生育;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这里埋藏着他们的生老病死,百年如一日、向前涌动的日常生活,人世的情感,悲欢离合,世态炎凉。汽车载着你,驶过了这片土地,一窗子的蓝天和树木,在你眼前静静地伸展,延续数百里;春天的田野上,麦子和油菜花盛开了,一片黄,一片绿,色彩是那样的鲜明,饱满,招摇。如果你恰逢走进了一个村庄,你就会看见,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开着,家家户户的门前有草垛,菜园子,猪圈;屋后有茅厕。你还会看见一些人物,他们都是地道的江淮农民,他们害羞,含蓄,见了生人了,眼睛待看不看的;也有一些小孩子,蹦蹦跳跳地说着江淮方言,他们尾随着你,就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从一户人家走过了另一户人家。正是农闲季节,村庄好像睡着了。村庄是那样的安静,祥和,老人们蹲在草垛旁,抽着旱烟,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起了农事。有一瞬间,他们的眼睛是看到阳光里去了,阳光是痒的,他们?[缝起眼睛,笑了。他们的笑容是那样的单纯,很深很深的沧桑的皱纹,无尽的岁月从其间流过了。在那一刻,他们的笑容几乎是浮面的,惯性的,不触及感情的。有一个农妇,从院子里走出来,怀里端着一盆猪饲料,她一边“噜噜噜”地叫唤着,一边朝猪圈走去了。这时节,你是看不见姑娘的。她们大多躲在闺房里,静静地做着针线活。她们绣荷包,纳鞋底,织毛线衣,踩缝纫机⋯⋯总之,一代又一代的姑娘,就是这样躲在闺房里,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莫测。时代在前进,她们手里的针线活,已由手工缝制改为机械操作――可是心思,到底还是从前的那些心思啊。才过了十八九岁,已到了说婆家的年纪了,她们有了自己的心事,无限的憧憬和惆怅。――这种事,到底是不踏实的。她们大多长得很美,有的也不是漂亮,只不过是清楚,明朗,和平,她们的眉宇间有一种动人的姿态。当你走在江淮的乡间,看见一个姑娘迎面走过来,她衣衫整洁,神态矜持而从容;如果你打量着她,她就会低下头,羞涩地、迅疾地走过了。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一草一木,万物生灵,在这片土地上,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活泼的姿势。它们是那样的和谐,具有某种朴素的美质。那是因为,你爱上了这片土地,你与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我刚才说过,我们这个家族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们分布于江淮一带。在一百多年前,他们从山东迁徙而至,辗转安徽,至江苏,从此安居了下来。他们婚丧嫁娶,生育繁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世纪。我们家族的穷,是有渊源,有历史的,那是典型中国农民式的穷,单调,灰暗,没有幻想。他们以土地为生,穷也穷得安乐、坦然,仿佛生来如此,并不心酸。到了我爷爷这一支,情况略有改观。我爷爷在三四十年代参加了革命,他组织了武装游击队,打土豪劣绅,也杀过日本人和国军。后来,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他被分了一官半职,最盛世的时候,他曾做过地委的XX部长;曾有消息说,他与市长这个职位失之交臂。――当然了,这也许只是谣传。对于我们家族来说,我爷爷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把这个家族的一支带出了乡村,走向城市。他们是他的嫡系子孙,在城里出生,长大,接受教育。总之,这个家族就这样被分离了,其中的一支远离了土地。到了我和弟弟这一代,我们已经完全地被改造了。我们开始过上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