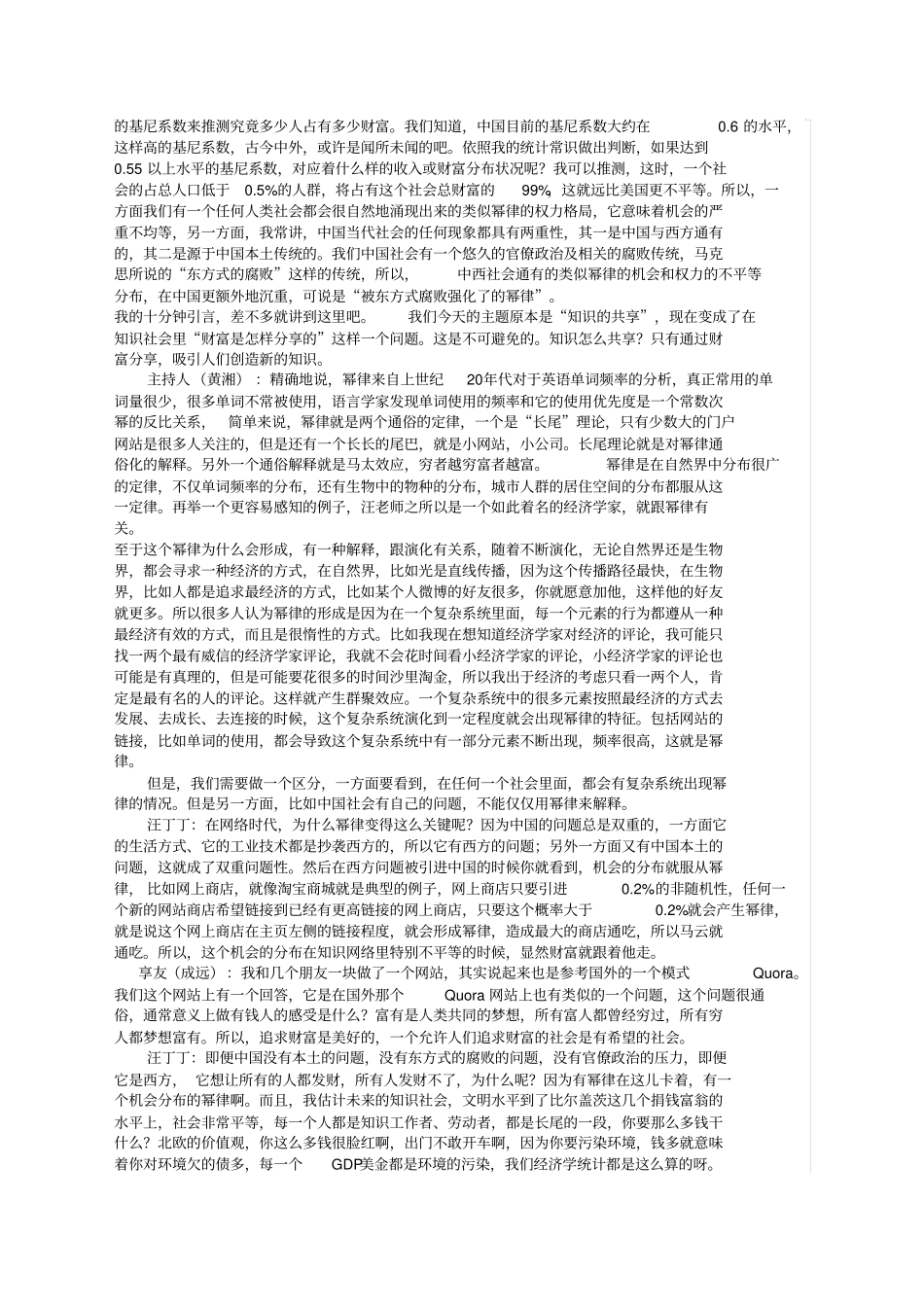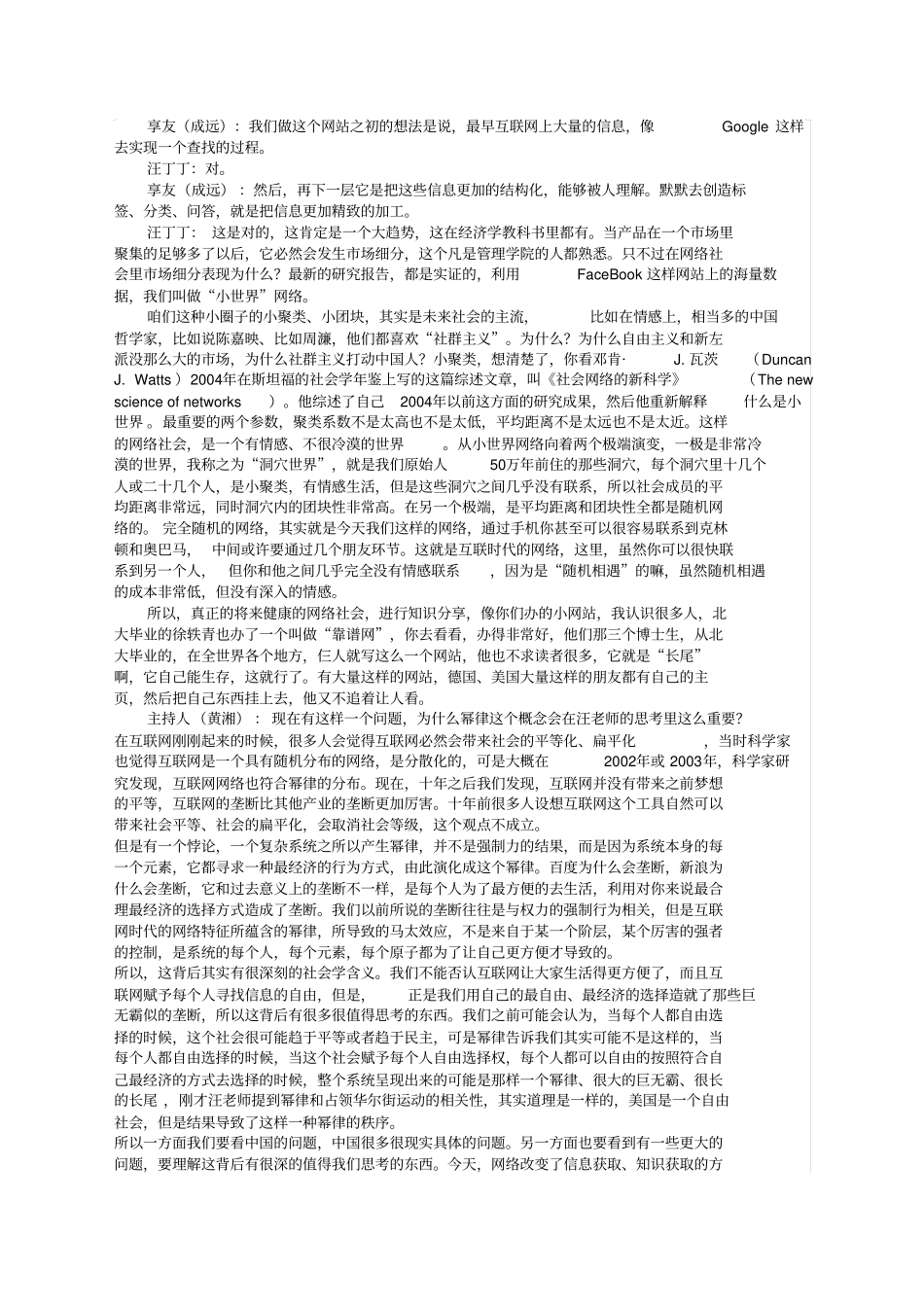汪丁丁: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享“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追求效率?祁克果100多年前就说过这个问题,他坐在哥本哈根大学校园躺椅上没事干,突然想起他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让别人觉得不方便,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便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必须拼力追求方便,上班要开车,不用自行车”——汪丁丁【财新网】(记者:黄湘谭娟实习生:吴文杰)2011年10月28日,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做客思享家线上沙龙,在万圣书园和思享家的享友们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这次谈话由财新传媒评论部编辑黄湘主持。活动开始后,汪丁丁先做了10分钟的发言。汪丁丁:其实,“知识社会”这一概念,在我记忆里,如果不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马克卢普1950年代的研究,那就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994年发表了一本书,《后资本主义社会》。他在这本书里预言,后资本主义社会(又称为“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实应当称为“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再有“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只有各种知识之间的碎片关系,这些碎片之间不可能形成利益长期一致的任何阶级,这是我的解释。后现代知识状况,这是利奥塔的书名,他在那本书里论证,后现代知识状况就是,每个人只拥有一小片知识,社会交往是由许多这样微小的知识之间的交流构成的,所谓“微小叙事”。这样的社会里,不再有“宏大叙事”。如果知识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力量可以维系这些知识碎片形成一个社会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不能靠强权维持这些碎片知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德鲁克也没谈到后现代社会的政治问题和政治架构。阿尔文·托夫勒后来想象了一下,我和他2006年有过一次对话。那时,中信出版社翻译了他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标题是《财富的革命》,我写了中译本序言。首发式的时候,中信出版社在编辑部办公室里安排我和他跨洋对话。他想象了知识社会的财富革命,不过他预言的后现代社会财富状况,大致上没有超过德鲁克的思路。其实,奥地利派学派的思想者,例如马克卢普,在1950年代发表鸿篇巨制,系统论述“知识经济”。接着马克卢普的思路,我在1995年写过一篇知识经济的文献综述,试图回答上述的问题: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成员,每一个人只知道他自己专业里的一小片知识,社会怎样维系为一个社会呢?基本原理是:因为,通常,一片知识与另一片知识之间,有内在的互补性。我在《经济研究》发表过一篇论文,标题就是“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知识的互补性是什么呢?例如,你想学习大学数学,必须先学习小学数学。因为,你不会相信大学数学是对中学数学和小学数学的“替代”,没人会相信这一点,是不是?所以,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各项知识之间,绝大部分是互补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先学中学和小学的数学,然后才可能学大学的数学。人类的大部分知识相互之间是互补的,我只找到极少数的个例,那里的知识是互替的,例如音乐的简谱和五线谱之间,互替性超过了互补性。由于知识有这种强烈的内在互补性,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分工,能依靠互补性加以协调和维系一个知识社会,因为这样人们互相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两人之间形成知识互补时,他们的合作就有规模收益,也就是整体大于各局部之和的意思。这一现象,在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里称为“超模态博弈”。所以,知识社会是可以维系的,它不是一堆碎片,但是它的政治结构很奇特。政治问题的核心,我们知道,是权力分配。现在,西方社会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几乎成为世界性的,这里有一个规律在起作用。一般而言,社会网络的权力结构是服从“幂律”的,这是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最开始的三讲的主题。大致而言,如果我们把网络里节点按照它们拥有的纽带数目排列在横轴上,我们用纵轴来表示对应于纽带数的节点数。节点的纽带数目,在网络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称为节点的“度”。这样,一个社会网络的全部节点沿着节点度数这一维度的分布密度,如果纵坐标取对数的话,很接近一条斜率是负值的直线。如果纵坐标不取对数,负的斜率就对应于一个幂指数(例如用“-r”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