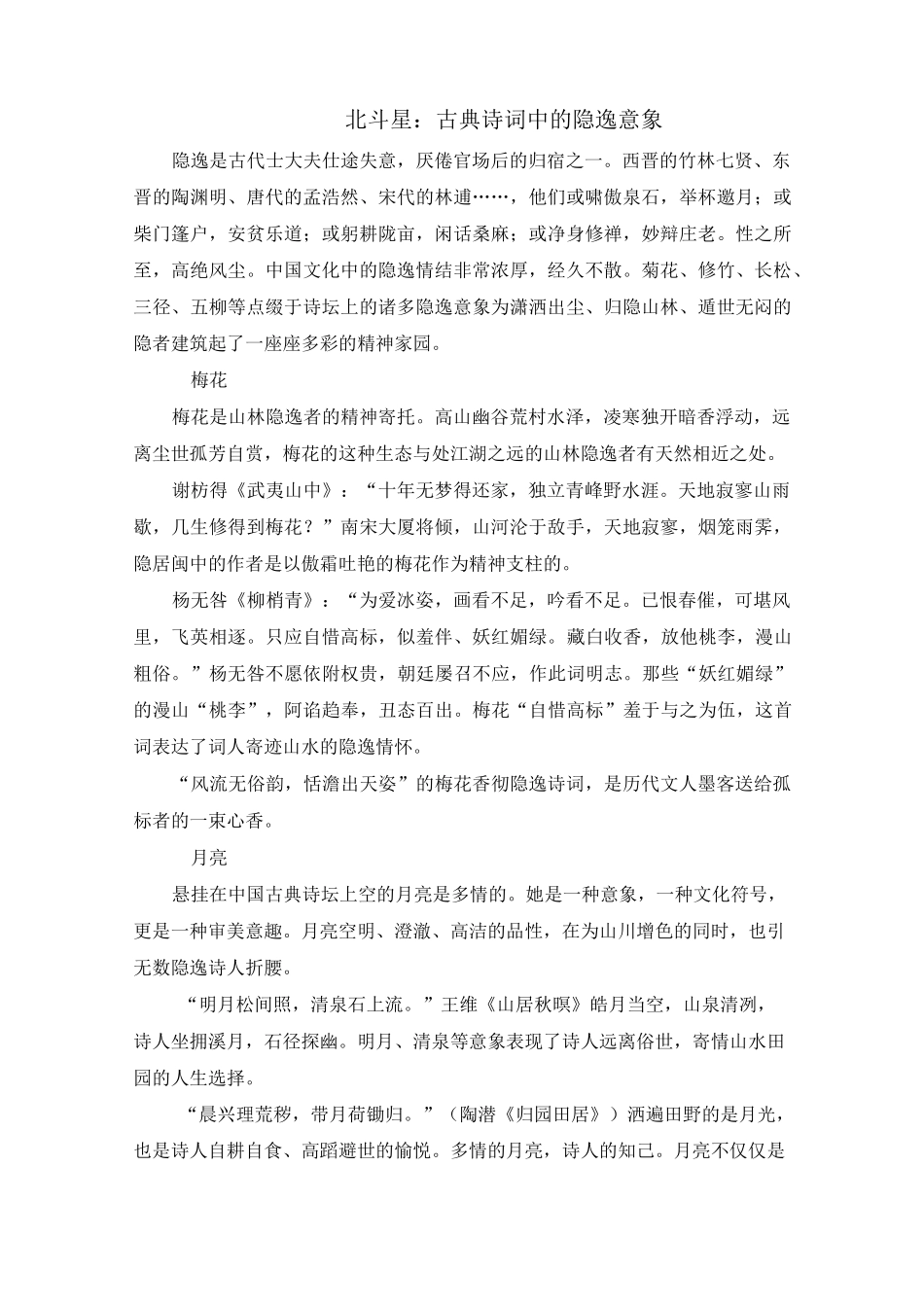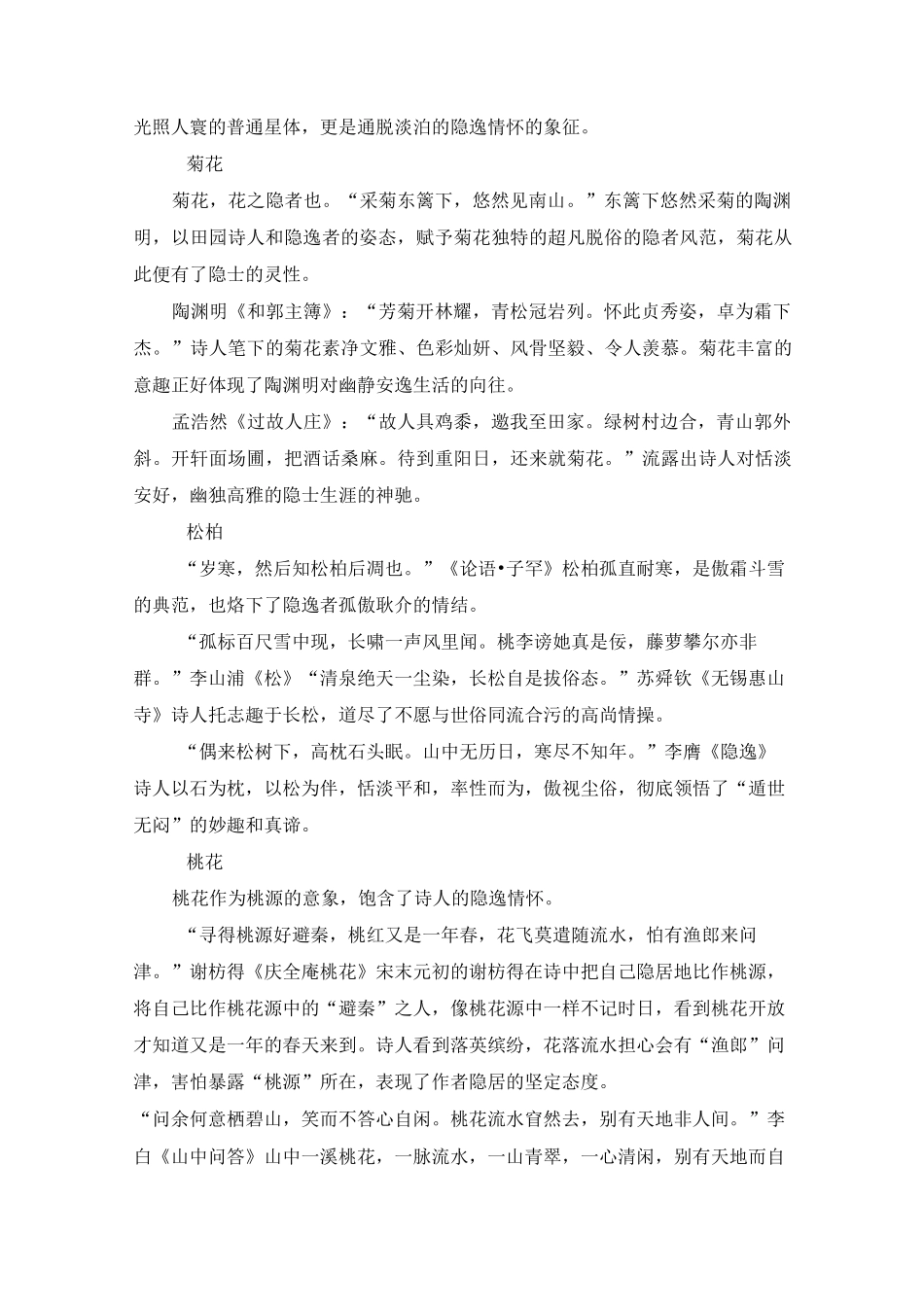北斗星:古典诗词中的隐逸意象隐逸是古代士大夫仕途失意,厌倦官场后的归宿之一。西晋的竹林七贤、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孟浩然、宋代的林逋……,他们或啸傲泉石,举杯邀月;或柴门篷户,安贫乐道;或躬耕陇亩,闲话桑麻;或净身修禅,妙辩庄老。性之所至,高绝风尘。中国文化中的隐逸情结非常浓厚,经久不散。菊花、修竹、长松、三径、五柳等点缀于诗坛上的诸多隐逸意象为潇洒出尘、归隐山林、遁世无闷的隐者建筑起了一座座多彩的精神家园。梅花梅花是山林隐逸者的精神寄托。高山幽谷荒村水泽,凌寒独开暗香浮动,远离尘世孤芳自赏,梅花的这种生态与处江湖之远的山林隐逸者有天然相近之处。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南宋大厦将倾,山河沦于敌手,天地寂寥,烟笼雨霁,隐居闽中的作者是以傲霜吐艳的梅花作为精神支柱的。杨无咎《柳梢青》:“为爱冰姿,画看不足,吟看不足。已恨春催,可堪风里,飞英相逐。只应自惜高标,似羞伴、妖红媚绿。藏白收香,放他桃李,漫山粗俗。”杨无咎不愿依附权贵,朝廷屡召不应,作此词明志。那些“妖红媚绿”的漫山“桃李”,阿谄趋奉,丑态百出。梅花“自惜高标”羞于与之为伍,这首词表达了词人寄迹山水的隐逸情怀。“风流无俗韵,恬澹出天姿”的梅花香彻隐逸诗词,是历代文人墨客送给孤标者的一束心香。月亮悬挂在中国古典诗坛上空的月亮是多情的。她是一种意象,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审美意趣。月亮空明、澄澈、高洁的品性,在为山川增色的同时,也引无数隐逸诗人折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皓月当空,山泉清冽,诗人坐拥溪月,石径探幽。明月、清泉等意象表现了诗人远离俗世,寄情山水田园的人生选择。“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潜《归园田居》)洒遍田野的是月光,也是诗人自耕自食、高蹈避世的愉悦。多情的月亮,诗人的知己。月亮不仅仅是光照人寰的普通星体,更是通脱淡泊的隐逸情怀的象征。菊花菊花,花之隐者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篱下悠然采菊的陶渊明,以田园诗人和隐逸者的姿态,赋予菊花独特的超凡脱俗的隐者风范,菊花从此便有了隐士的灵性。陶渊明《和郭主簿》:“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诗人笔下的菊花素净文雅、色彩灿妍、风骨坚毅、令人羡慕。菊花丰富的意趣正好体现了陶渊明对幽静安逸生活的向往。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流露出诗人对恬淡安好,幽独高雅的隐士生涯的神驰。松柏“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也。”《论语•子罕》松柏孤直耐寒,是傲霜斗雪的典范,也烙下了隐逸者孤傲耿介的情结。“孤标百尺雪中现,长啸一声风里闻。桃李谤她真是佞,藤萝攀尔亦非群。”李山浦《松》“清泉绝天一尘染,长松自是拔俗态。”苏舜钦《无锡惠山寺》诗人托志趣于长松,道尽了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李膺《隐逸》诗人以石为枕,以松为伴,恬淡平和,率性而为,傲视尘俗,彻底领悟了“遁世无闷”的妙趣和真谛。桃花桃花作为桃源的意象,饱含了诗人的隐逸情怀。“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谢枋得《庆全庵桃花》宋末元初的谢枋得在诗中把自己隐居地比作桃源,将自己比作桃花源中的“避秦”之人,像桃花源中一样不记时日,看到桃花开放才知道又是一年的春天来到。诗人看到落英缤纷,花落流水担心会有“渔郎”问津,害怕暴露“桃源”所在,表现了作者隐居的坚定态度。“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问答》山中一溪桃花,一脉流水,一山青翠,一心清闲,别有天地而自得其乐。桃花流水,自自然然,清明亮丽,不汲汲于荣,不寂寂于逝的风调,令人联想到宠辱不惊,淡泊处世的隐士风采。全诗借“桃花流水”抒发诗人高蹈尘外,醉心山林的隐逸情怀。麋鹿麋鹿素有“瑞兽”之誉。性喜山泽,体态雄伟,角如梅枝,尾似长鞭,或静如处子,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