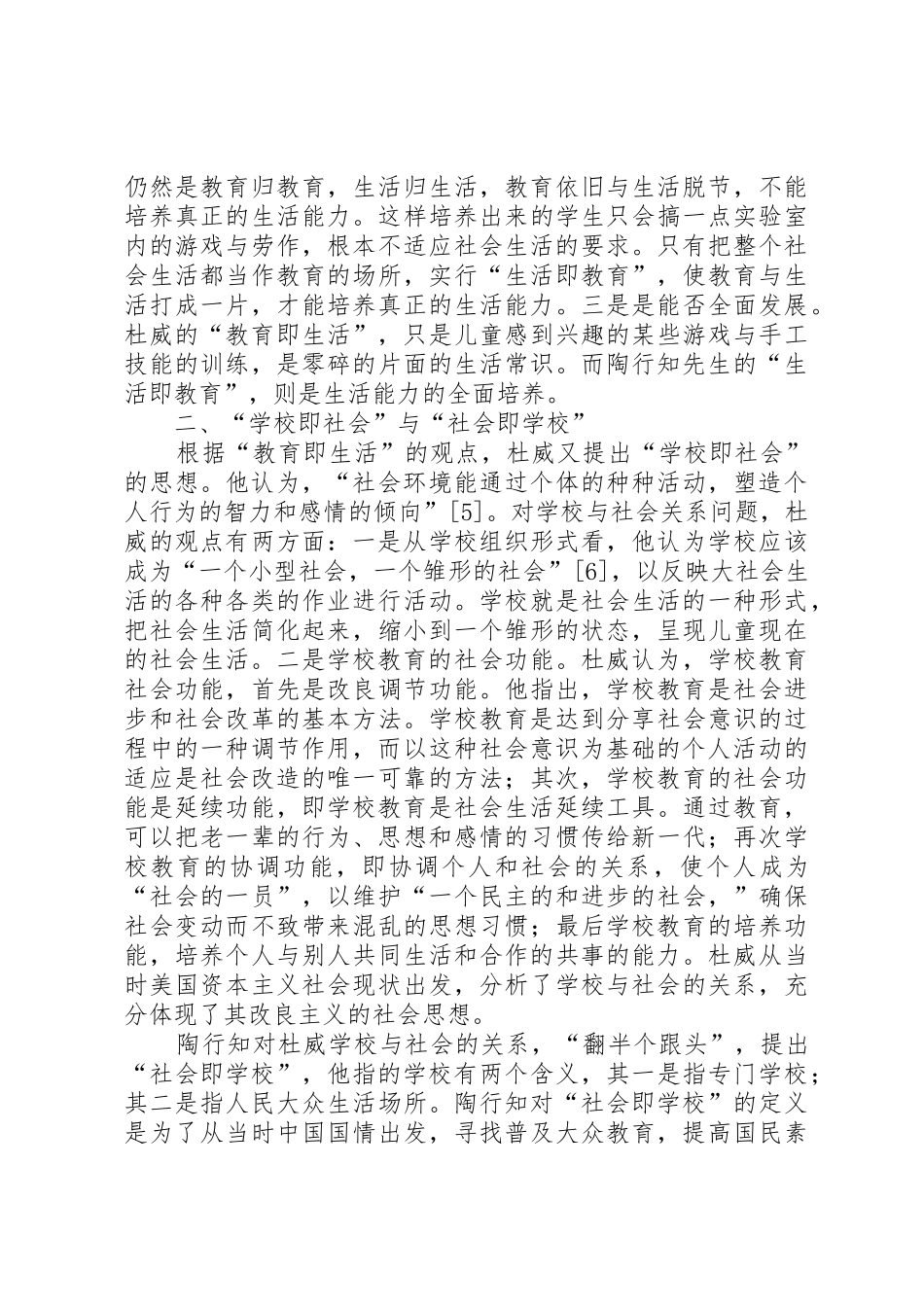观上海世博会报告(与爱知及汉诺威的比较)建国以来,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常常都与杜威的思想联系起来,有的说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翻版,也有的则竭力避开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我认为,说陶行知思想就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翻版有一叶障目之憾,说他没有受过杜威的影响也不符合事实。确切地说,对陶行知的思想的评价,既要看到与杜威教育思想的联系,更要看到与它的区别。陶行知于1914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受业于杜威先生。1917年回国后,曾试图用杜威的教育理论来解决中国人民大众受教育的问题。搞了几年,毫无收效。从此他认识到搬用杜威的一套,在中国,根本起不到普及教育、振兴社会的作用。在现实面前,他看到杜威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学校社会化”不过成了一句时髦的空话。回顾走弯路的那些日子,他沉痛地说,“我从美国回来,用杜威的一套到处碰了壁,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1]因此对杜威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同时把杜威的“从做中学”发展为“教学做合一”,教育与整个社会生活血脉相通。本文即从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比较入手,阐明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一、“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杜威站在自然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概念。他对教育与生活关系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生活离不开教育。他说:“生活即是发展;发展、生长,即是生活。”[2]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二是生长是生活的特征,而教育就是生长。“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3]所谓生长,就是指向未来的发展过程。教育的历史就是生长过程。三是教育是对生活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是对个人,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它是一个连续不断改造的过程。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把人的教育、人的生活,仅仅看成生物与环境交互的作用,把教育看作一种适应环境的过程。他没有把教育、生活摆在人的社会历史中来认识,不承认社会历史是由具有理性和意志的人所创造的这一特点,把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混为一谈,他的思想非常明显地包含着社会进化论思想。陶行知在教育与生活的问题上又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又“翻了半个跟头”,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把生活和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建立在人民大众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基础之上,并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平等和解放,其内含十分丰富。概括起来有三层意思:一是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陶行知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的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4]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之变化。他强调,只有“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才算得上是促进生活之变化的教育;三是教育随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生活无时不变,教育也随之发展,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克服了长期以来教育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现状,把教育与生活真正熔为一炉,促进教育改造生活,改造自然和社会,实现富民强国。他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颠倒过来,“翻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主张,从根本上推倒了教育与生活隔离的围墙。在这个问题上,陶先生与杜威有三个根本不同的看法;一是有没有解决人民生活困难、教育困难的实际精神。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把社会生活搬一些进学校,如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里,只安排儿童做些纺纱、织布、烹饪、木工、缝纫等作业活动,反复出现某些简单的动作,只使人们学到一些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初步技术,而并没有掌握好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生活所急需的实际本领,没有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生活能力。陶行知与杜威相反,十分注重人民生活的实际本领,主张教育为人民生活服务,要求教育结合人民生活的实际。二是能否培养真正的社会生活能力。陶行知先生认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鸟笼式”的教育,“鸟笼式”的生活,即使“把社会里的生活搬一些进来”,仍然是教育归教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