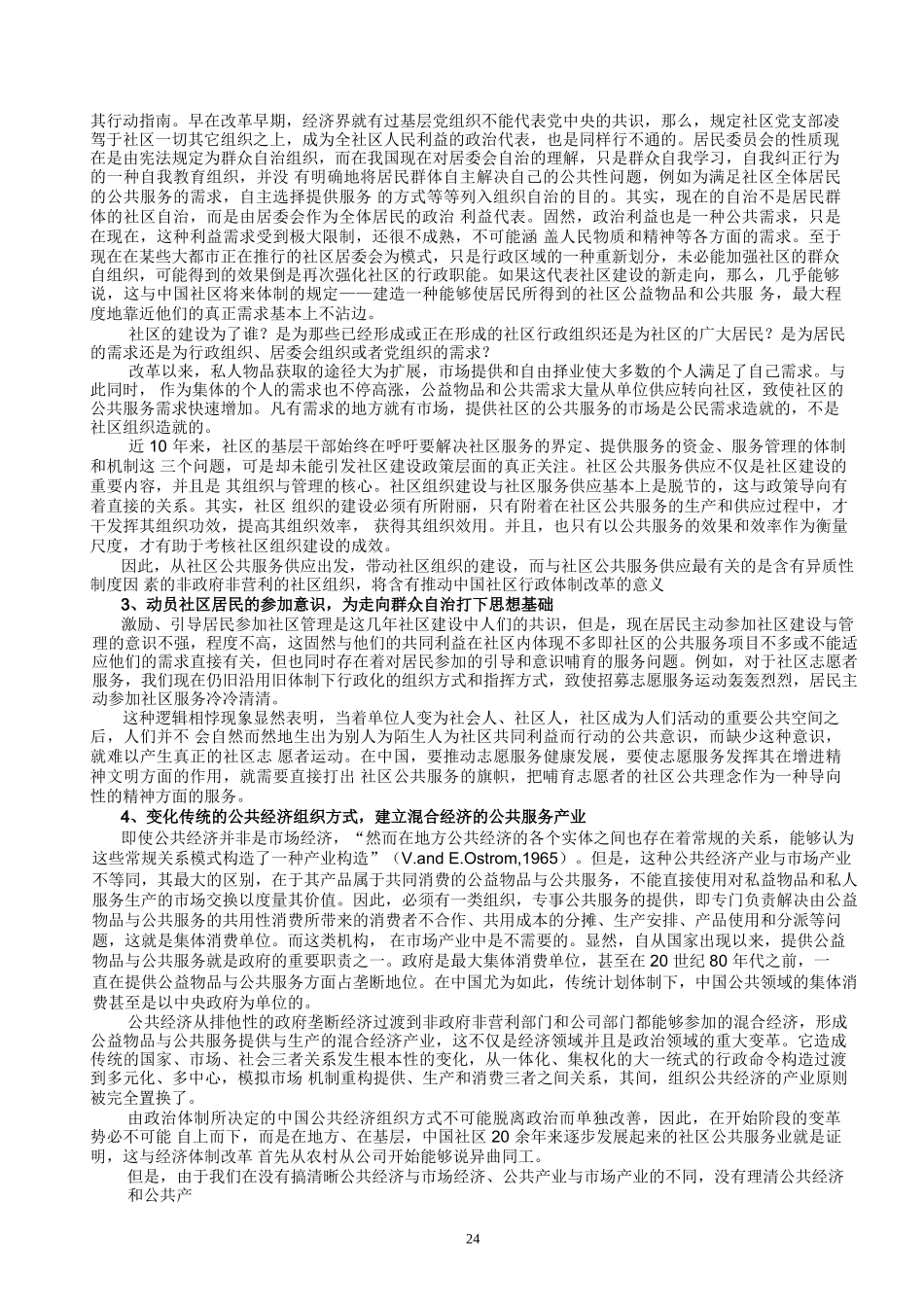其行动指南。早在改革早期,经济界就有过基层党组织不能代表党中央的共识,那么,规定社区党支部凌驾于社区一切其它组织之上,成为全社区人民利益的政治代表,也是同样行不通的。居民委员会的性质现在是由宪法规定为群众自治组织,而在我国现在对居委会自治的理解,只是群众自我学习,自我纠正行为的一种自我教育组织,并没有明确地将居民群体自主解决自己的公共性问题,例如为满足社区全体居民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自主选择提供服务的方式等等列入组织自治的目的。其实,现在的自治不是居民群体的社区自治,而是由居委会作为全体居民的政治利益代表。固然,政治利益也是一种公共需求,只是在现在,这种利益需求受到极大限制,还很不成熟,不可能涵盖人民物质和精神等各方面的需求。至于现在在某些大都市正在推行的社区居委会为模式,只是行政区域的一种重新划分,未必能加强社区的群众自组织,可能得到的效果倒是再次强化社区的行政职能。如果这代表社区建设的新走向,那么,几乎能够说,这与中国社区将来体制的规定——建造一种能够使居民所得到的社区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最大程度地靠近他们的真正需求基本上不沾边。社区的建设为了谁?是为那些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社区行政组织还是为社区的广大居民?是为居民的需求还是为行政组织、居委会组织或者党组织的需求?改革以来,私人物品获取的途径大为扩展,市场提供和自由择业使大多数的个人满足了自己需求。与此同时,作为集体的个人的需求也不停高涨,公益物品和公共需求大量从单位供应转向社区,致使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加。凡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提供社区的公共服务的市场是公民需求造就的,不是社区组织造就的。近10年来,社区的基层干部始终在呼吁要解决社区服务的界定、提供服务的资金、服务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这三个问题,可是却未能引发社区建设政策层面的真正关注。社区公共服务供应不仅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且是其组织与管理的核心。社区组织建设与社区服务供应基本上是脱节的,这与政策导向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社区组织的建设必须有所附丽,只有附着在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应过程中,才干发挥其组织功效,提高其组织效率,获得其组织效用。并且,也只有以公共服务的效果和效率作为衡量尺度,才有助于考核社区组织建设的成效。因此,从社区公共服务供应出发,带动社区组织的建设,而与社区公共服务供应最有关的是含有异质性制度因素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社区组织,将含有推动中国社区行政体制改革的意义3、动员社区居民的参加意识,为走向群众自治打下思想基础激励、引导居民参加社区管理是这几年社区建设中人们的共识,但是,现在居民主动参加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意识不强,程度不高,这固然与他们的共同利益在社区内体现不多即社区的公共服务项目不多或不能适应他们的需求直接有关,但也同时存在着对居民参加的引导和意识哺育的服务问题。例如,对于社区志愿者服务,我们现在仍旧沿用旧体制下行政化的组织方式和指挥方式,致使招募志愿服务运动轰轰烈烈,居民主动参加社区服务冷冷清清。这种逻辑相悖现象显然表明,当着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社区人,社区成为人们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之后,人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为别人为陌生人为社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公共意识,而缺少这种意识,就难以产生真正的社区志愿者运动。在中国,要推动志愿服务健康发展,要使志愿服务发挥其在增进精神文明方面的作用,就需要直接打出社区公共服务的旗帜,把哺育志愿者的社区公共理念作为一种导向性的精神方面的服务。4、变化传统的公共经济组织方式,建立混合经济的公共服务产业即使公共经济并非是市场经济,“然而在地方公共经济的各个实体之间也存在着常规的关系,能够认为这些常规关系模式构造了一种产业构造”(V.andE.Ostrom,1965)。但是,这种公共经济产业与市场产业不等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产品属于共同消费的公益物品与公共服务,不能直接使用对私益物品和私人服务生产的市场交换以度量其价值。因此,必须有一类组织,专事公共服务的提供,即专门负责解决由公益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共用性消费所带来的消费者不合作、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