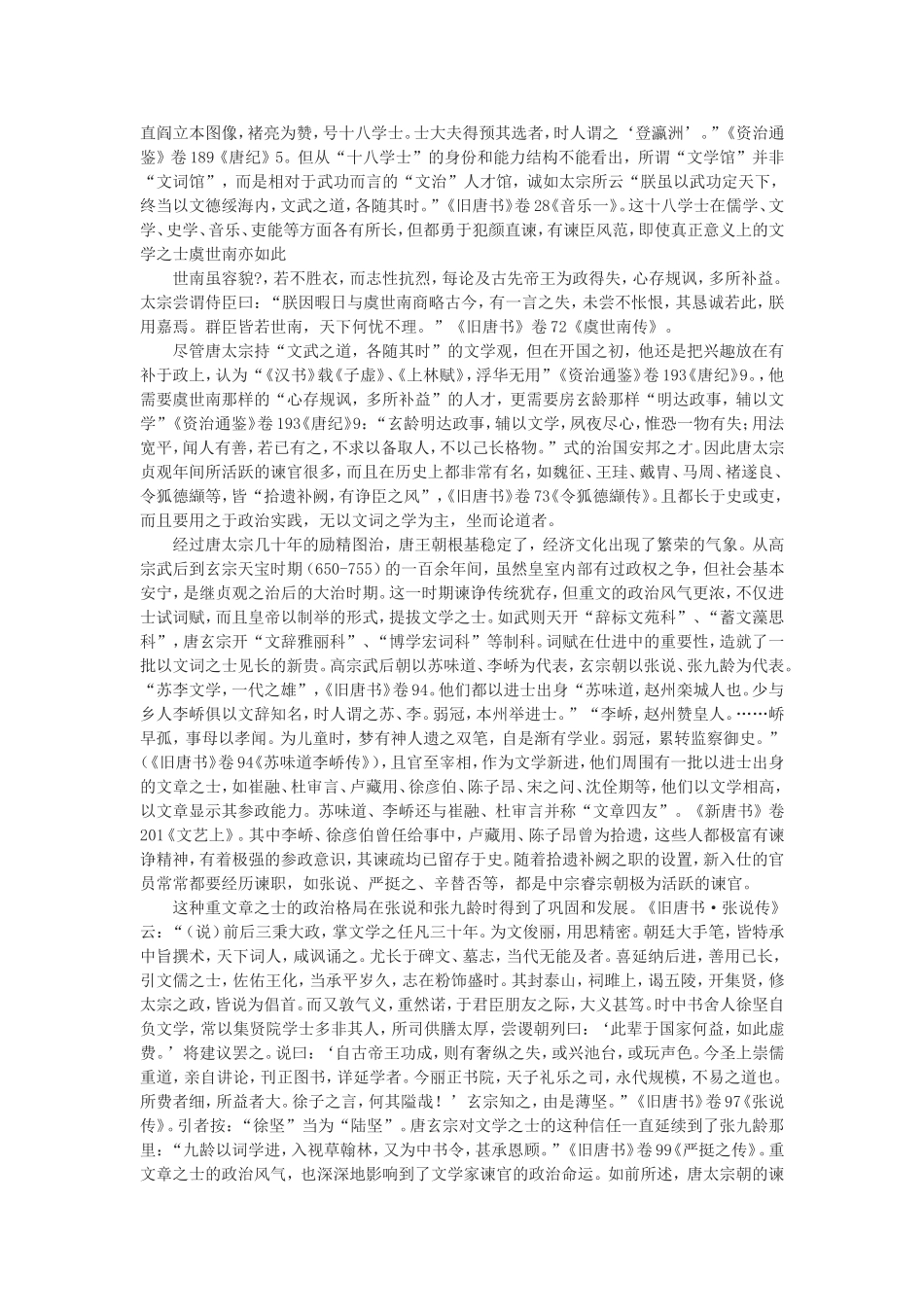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傅绍良内容提要: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从理论上说,唐代君王都重谏,把劝谏与纳谏作为为政之本,无论是开国之秋、大治之际,还是衰变之期、灭亡之时,统治者都将求言纳谏作为安邦图存的良药,因而从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发布过劝谏求谏的诏令,“求直言”诏不绝于史,“从谏则圣,共理惟贤”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55。是这些君王为政的共识。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各人政治素质的差异,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这些有纳谏意识的君王们并不能去奉行其理想的政治,或者说不能真正劝谏纳谏。概而言之,从开国到灭亡,唐代政治的谏诤之风呈波浪式发展。在唐代谏官的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参见拙文:《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唐代许多有作为的文学家都曾任谏官,或者说,唐代许多著名的谏官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因素与那些以文学见长的谏官们关系十分密切,它往往左右着那些任谏职的文人们的政治前途和人生命运。一唐高祖和唐太宗当唐代开国之初,常以秦隋之亡为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反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诈。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良足深诫。”唐高祖:《颁示孙伏伽谏书诏》,《全唐文》卷1。因此,他们都将求言劝谏作为政治的头等大事,这在上节的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开国时期居安思危的政治意识,使得唐太宗特别注重与臣下的关系,无论来自哪个阵营,也无论其官职的高低,只要有治国的才略,就委以重任,决无疑虑。王夫之评唐初之任官的情形云:“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简岑文本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拔濯而出者也。……盖新造之国,培养无渐渍之功,而隋末风教陵夷,时无岩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以为桢干,朝仪邦典与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访于亡国之臣,流品难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也。”《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之五,中华书局排印本,1975年,第668页。后世常引以为楷模。文宗以杜胔领度支称职,欲加户部尚书,因紫宸言之。陈夷行曰:“一切恩权,合归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对曰:“太宗用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谓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无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职,事事皆决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臣下发论则疑,凡臣下用之则宰相,不用则常僚,岂可自保。”《旧唐书》卷173《李珏传》。不过,唐太宗还以重文学著名。他曾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资治通鉴》卷189《唐纪》5。但从“十八学士”的身份和能力结构不能看出,所谓“文学馆”并非“文词馆”,而是相对于武功而言的“文治”人才馆,诚如太宗所云“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卷28《音乐一》。这十八学士在儒学、文学、史学、音乐、吏能等方面各有所长,但都勇于犯颜直谏,有谏臣风范,即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之士虞世南亦如此世南虽容貌?,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心存规讽,多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