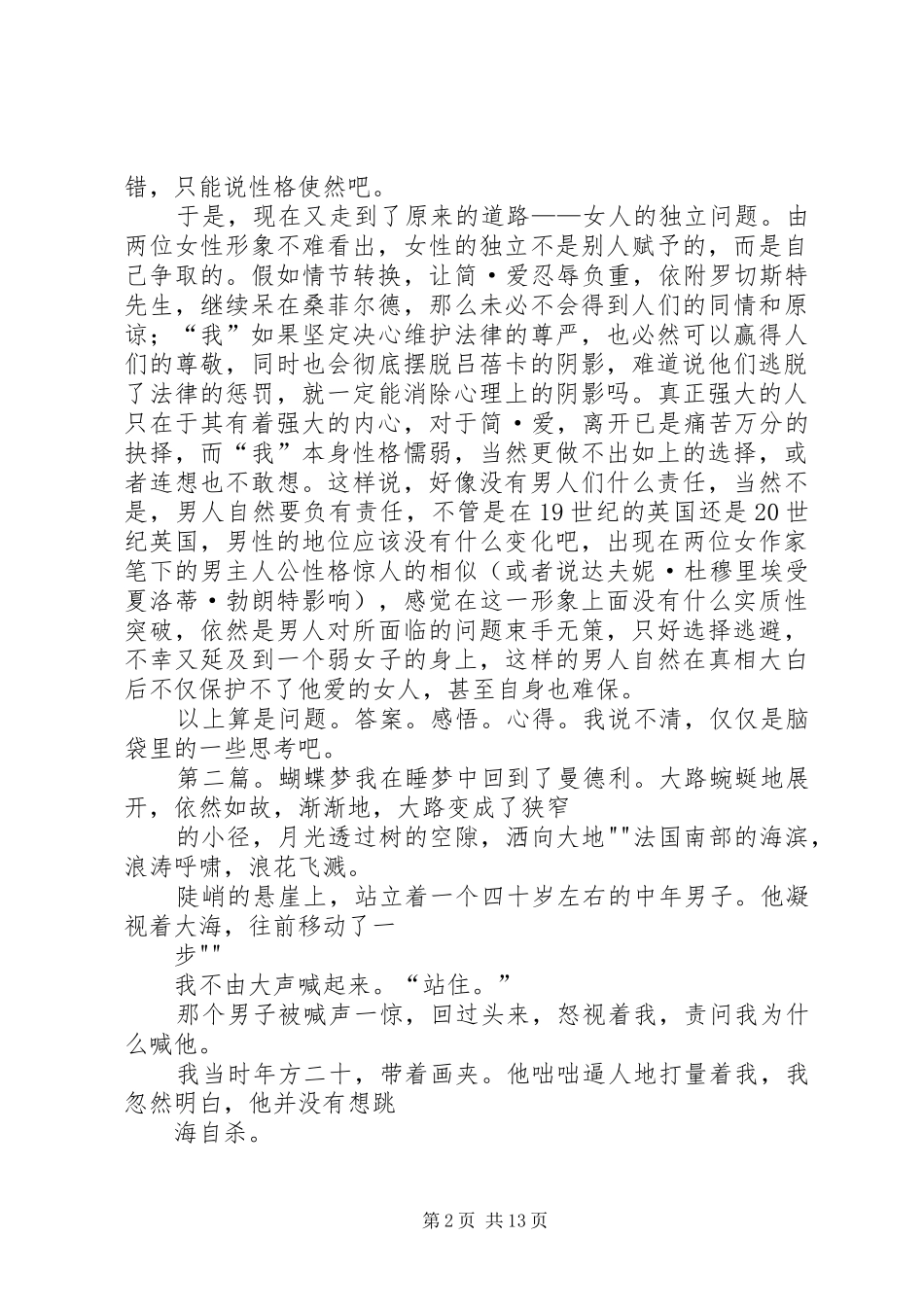关于《蝴蝶梦》的思考五篇范文第一篇:关于《蝴蝶梦》的思考关于《蝴蝶梦》的一些思考故事梗概。一件离奇的凶杀案(迈克西姆杀死了妻子吕蓓卡)为核心,向前追源——迈克西姆和吕蓓卡婚姻不幸,即吕蓓卡放浪不羁的生活(要把曼陀丽庄园变成她自己的“艳窟”)让丈夫迈克西姆忍无可忍,最后制造了她在驾舟出海时的“意外”事故;向后寻果——吕蓓卡的阴魂不散,在迈克西姆因心里不堪重负而离家并在蒙特卡洛(法)遇到为范·霍珀太太做跟班的“我”,一见钟情,之后“我”跟随迈克西姆回到曼陀丽庄园,于是,吕蓓卡的阴影时刻缠绕着“我”,甚至成为横亘在“我”和迈克西姆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不可否认,作品中吕蓓卡的形象非常耐人寻味,正如大多数人分析的那样——“此人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除在倒叙段落中被间接提到外,从未在书中出现,但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忠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丽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她的形象复杂丰富而又神秘莫测。但读书不是为了人云亦云,而是发见其中触动人内心情感的东西——或一番感悟,或一丝共鸣,亦或是一份同情、怜悯哪怕愤怒,足矣。以上在我看来只是“我”跟随迈克西姆回到曼陀丽庄园一年以后面临两难处境的一个大背景而已。一年的好奇、恐惧、云里雾里都随着吕蓓卡的尸体被发现而消散。了解到迈克西姆与吕蓓卡之间不堪的婚姻,认识到吕蓓卡丑恶的本质之后,“我”对自己和迈克西姆之间的罅隙有所释怀,然而却又不得不面对情与法的选择,很显然,作品中的“我”偏向了“情”。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简爱》里的女主角简·爱在得知罗切斯特先生一直都有一位合法妻子(尽管她是个疯子)之后,内心难以言喻的痛苦和耻辱一样——她爱罗切斯特先生,但她在情与法之间选择了“遵法”。我想,简·爱为什么不能和罗切斯特先生一走了之,远离是非,可她没有那样做。两人处于相似的境地,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我无法说他们谁对谁第1页共13页错,只能说性格使然吧。于是,现在又走到了原来的道路——女人的独立问题。由两位女性形象不难看出,女性的独立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己争取的。假如情节转换,让简·爱忍辱负重,依附罗切斯特先生,继续呆在桑菲尔德,那么未必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原谅;“我”如果坚定决心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必然可以赢得人们的尊敬,同时也会彻底摆脱吕蓓卡的阴影,难道说他们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就一定能消除心理上的阴影吗。真正强大的人只在于其有着强大的内心,对于简·爱,离开已是痛苦万分的抉择,而“我”本身性格懦弱,当然更做不出如上的选择,或者连想也不敢想。这样说,好像没有男人们什么责任,当然不是,男人自然要负有责任,不管是在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英国,男性的地位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吧,出现在两位女作家笔下的男主人公性格惊人的相似(或者说达夫妮·杜穆里埃受夏洛蒂·勃朗特影响),感觉在这一形象上面没有什么实质性突破,依然是男人对所面临的问题束手无策,只好选择逃避,不幸又延及到一个弱女子的身上,这样的男人自然在真相大白后不仅保护不了他爱的女人,甚至自身也难保。以上算是问题。答案。感悟。心得。我说不清,仅仅是脑袋里的一些思考吧。第二篇。蝴蝶梦我在睡梦中回到了曼德利。大路蜿蜒地展开,依然如故,渐渐地,大路变成了狭窄的小径,月光透过树的空隙,洒向大地""法国南部的海滨,浪涛呼啸,浪花飞溅。陡峭的悬崖上,站立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凝视着大海,往前移动了一步""我不由大声喊起来。“站住。”那个男子被喊声一惊,回过头来,怒视着我,责问我为什么喊他。我当时年方二十,带着画夹。他咄咄逼人地打量着我,我忽然明白,他并没有想跳海自杀。第2页共13页我连忙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他,觉得这人很怪。在蒙特卡洛的公主饭店,大厅内,我正陪主人范霍珀太太坐着,那个被我误认为要跳海的男子潇洒地走了进来。范霍珀太太高兴万分。“啊。是德文特先生。”她对豪富的德文特大献殷勤,德文特却很冷淡,相反,却很愿意和我说话。德文特走了。范霍珀太太告诉我。“可怜的人啊,他在怀念他死去的妻子。”第二天,在公主饭店的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