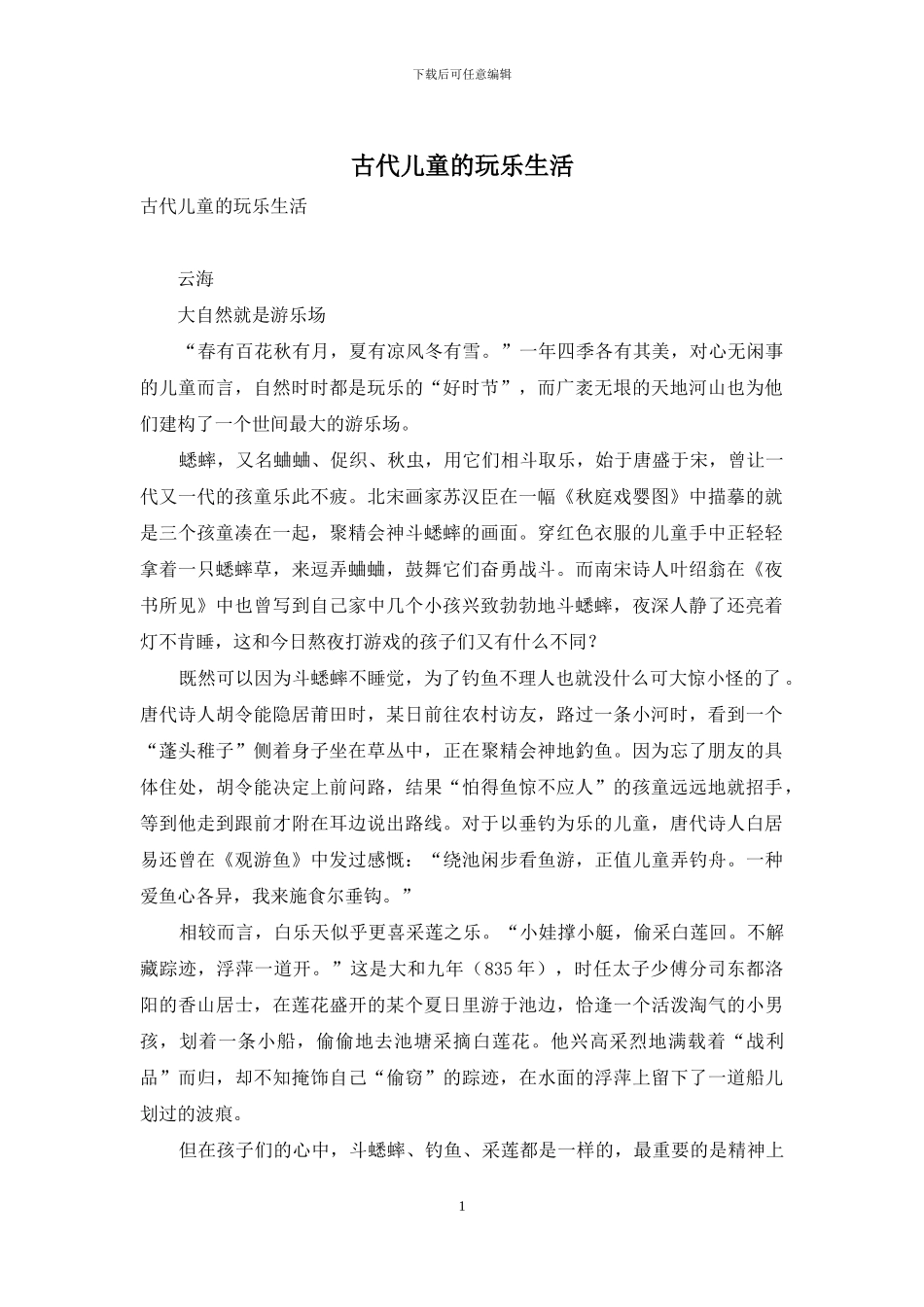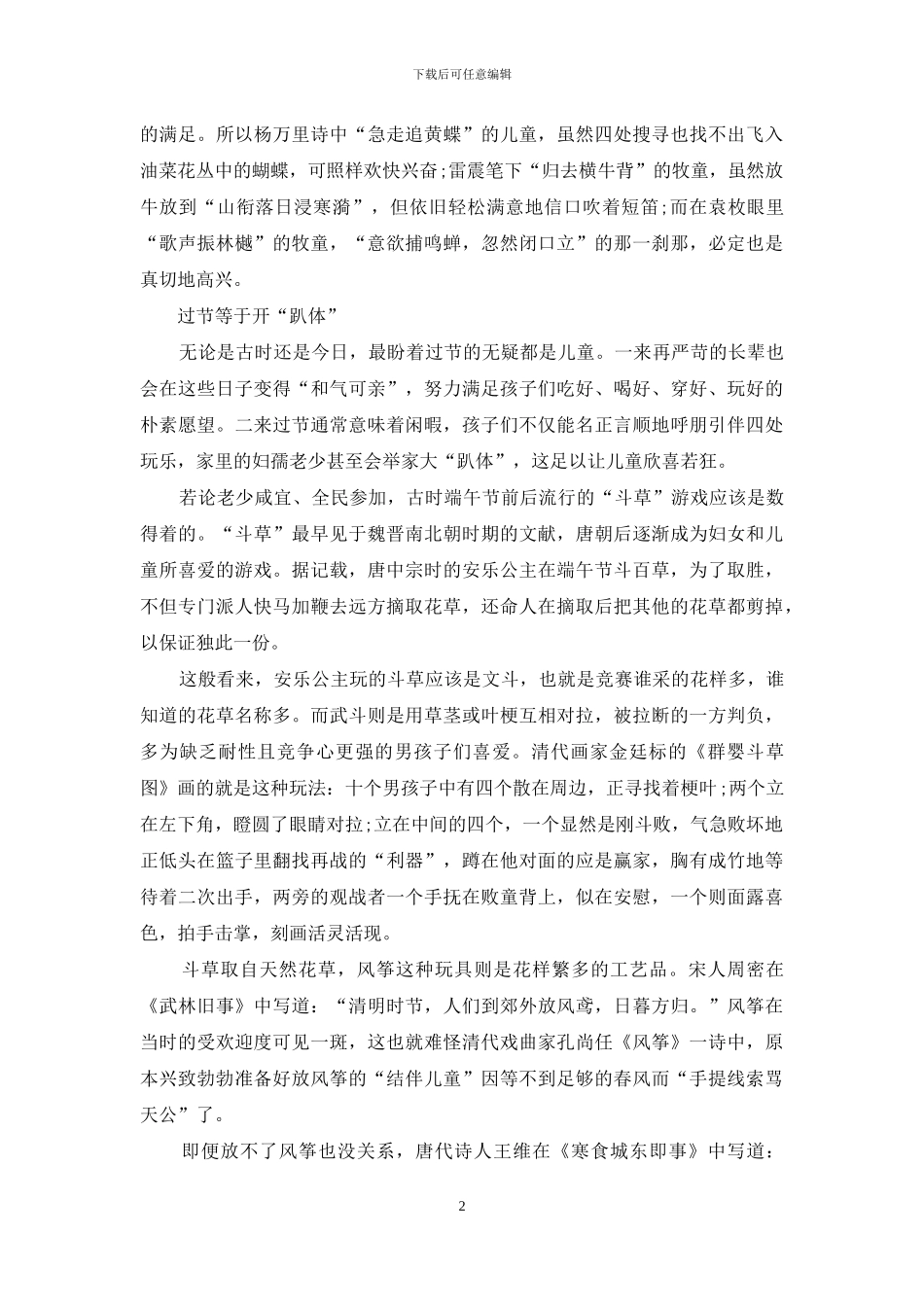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古代儿童的玩乐生活古代儿童的玩乐生活 云海 大自然就是游乐场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四季各有其美,对心无闲事的儿童而言,自然时时都是玩乐的“好时节”,而广袤无垠的天地河山也为他们建构了一个世间最大的游乐场。 蟋蟀,又名蛐蛐、促织、秋虫,用它们相斗取乐,始于唐盛于宋,曾让一代又一代的孩童乐此不疲。北宋画家苏汉臣在一幅《秋庭戏婴图》中描摹的就是三个孩童凑在一起,聚精会神斗蟋蟀的画面。穿红色衣服的儿童手中正轻轻拿着一只蟋蟀草,来逗弄蛐蛐,鼓舞它们奋勇战斗。而南宋诗人叶绍翁在《夜书所见》中也曾写到自己家中几个小孩兴致勃勃地斗蟋蟀,夜深人静了还亮着灯不肯睡,这和今日熬夜打游戏的孩子们又有什么不同? 既然可以因为斗蟋蟀不睡觉,为了钓鱼不理人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唐代诗人胡令能隐居莆田时,某日前往农村访友,路过一条小河时,看到一个“蓬头稚子”侧着身子坐在草丛中,正在聚精会神地釣鱼。因为忘了朋友的具体住处,胡令能决定上前问路,结果“怕得鱼惊不应人”的孩童远远地就招手,等到他走到跟前才附在耳边说出路线。对于以垂钓为乐的儿童,唐代诗人白居易还曾在《观游鱼》中发过感慨:“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 相较而言,白乐天似乎更喜采莲之乐。“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是大和九年(835 年),时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的香山居士,在莲花盛开的某个夏日里游于池边,恰逢一个活泼淘气的小男孩,划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塘采摘白莲花。他兴高采烈地满载着“战利品”而归,却不知掩饰自己“偷窃”的踪迹,在水面的浮萍上留下了一道船儿划过的波痕。 但在孩子们的心中,斗蟋蟀、钓鱼、采莲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精神上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的满足。所以杨万里诗中“急走追黄蝶”的儿童,虽然四处搜寻也找不出飞入油菜花丛中的蝴蝶,可照样欢快兴奋;雷震笔下“归去横牛背”的牧童,虽然放牛放到“山衔落日浸寒漪”,但依旧轻松满意地信口吹着短笛;而在袁枚眼里“歌声振林樾”的牧童,“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的那一刹那,必定也是真切地高兴。 过节等于开“趴体” 无论是古时还是今日,最盼着过节的无疑都是儿童。一来再严苛的长辈也会在这些日子变得“和气可亲”,努力满足孩子们吃好、喝好、穿好、玩好的朴素愿望。二来过节通常意味着闲暇,孩子们不仅能名正言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