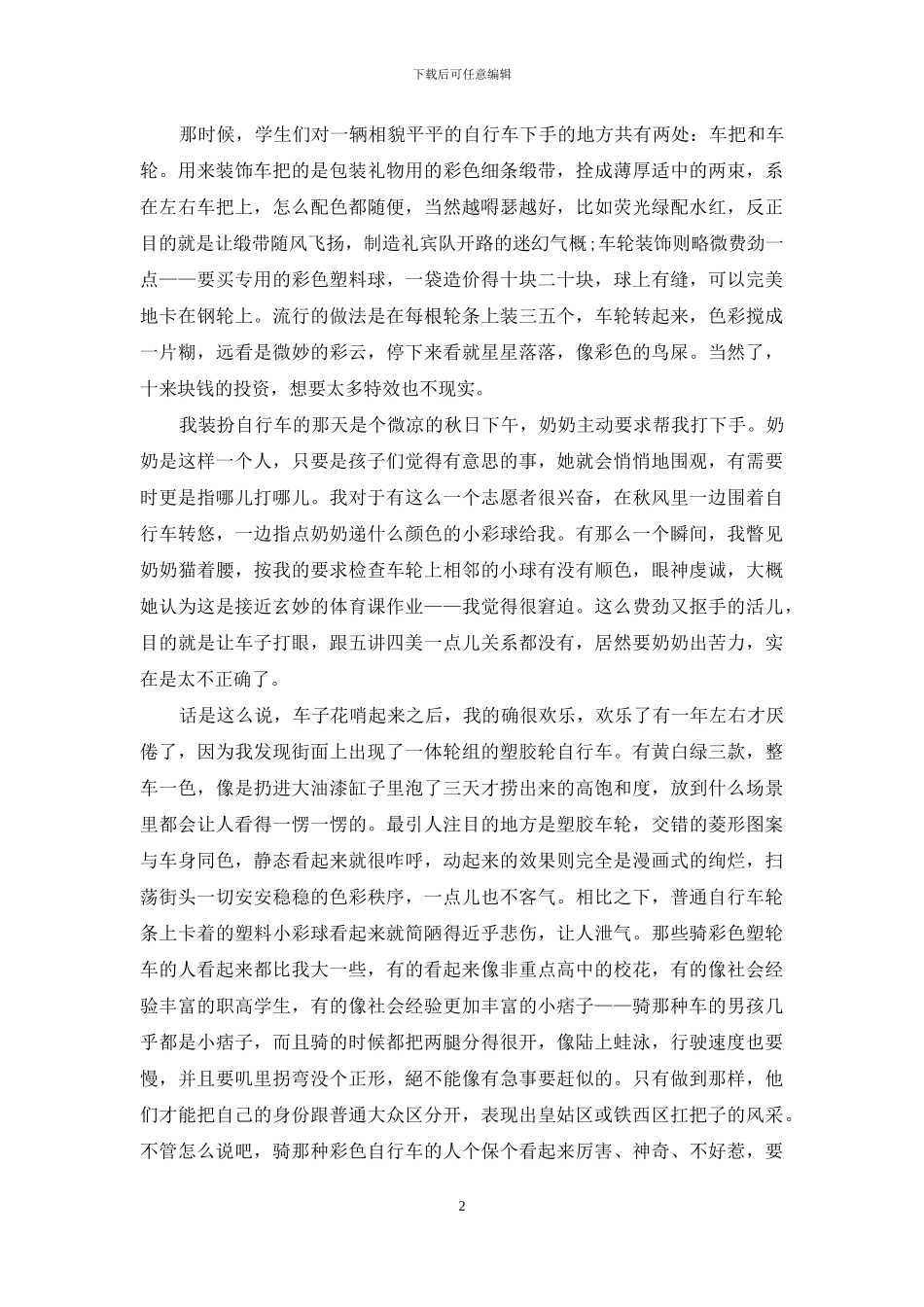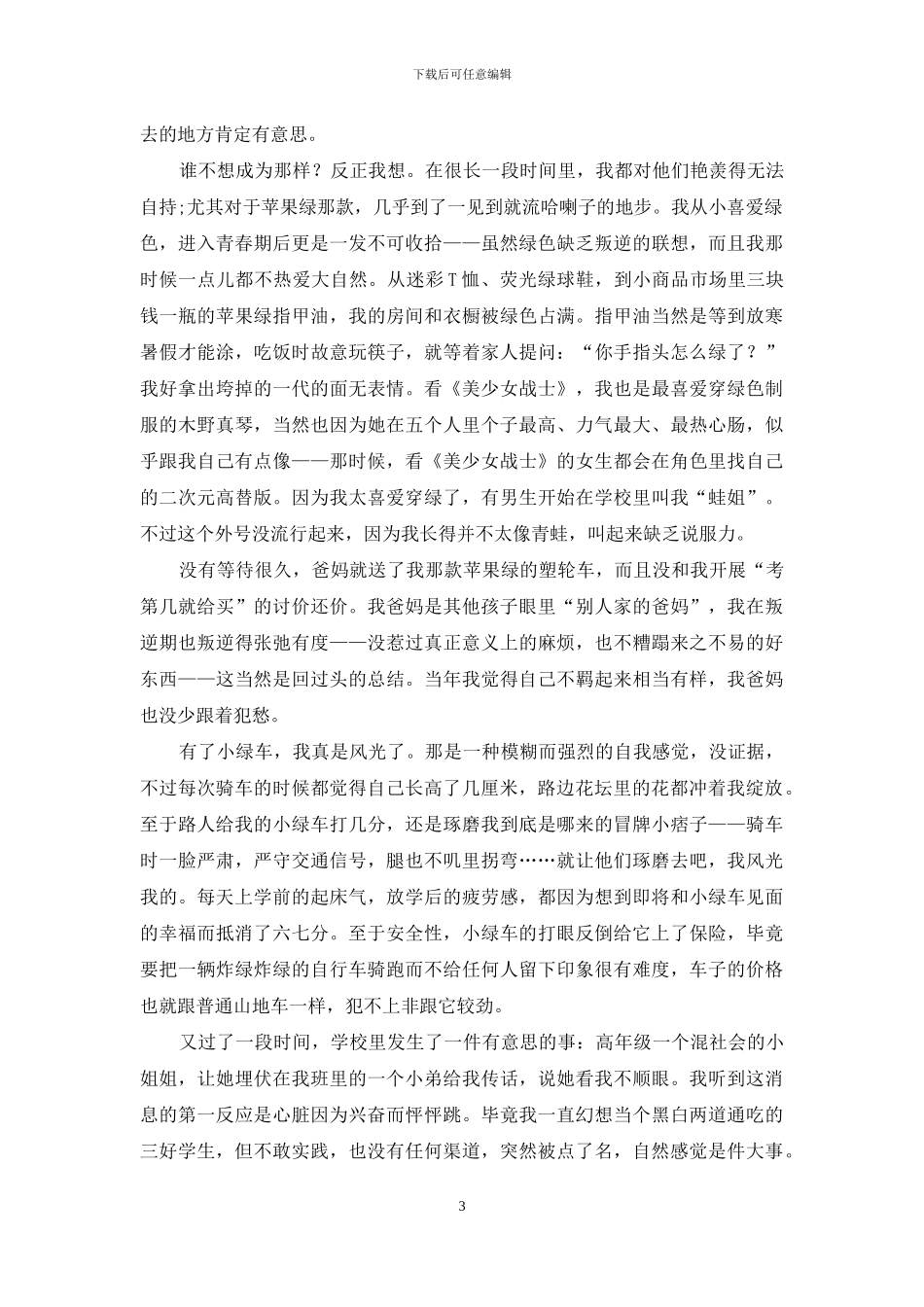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扛把子的小绿车扛把子的小绿车 鲍尔金娜 有了小绿车,我真是风光了。那是一种模糊而强烈的自我感觉,没证据,不过每次骑车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长高了几厘米,路边花坛里的花都冲着我绽放。 小时候在东北骑了一溜烟儿自行车,我始终没听说过“单车”这个词;我们那时候都叫自行车,现在也还叫自行车。尽管单车比自行车的发音大概能省五分之一秒的时间,也更经得起推敲——明明是靠我的腿蹬的车,你怎么好意思叫自行呢? 在上初中以前,对于任何自行车来说我都只是乘客,从没在车子运转的动力学上出过半点力。每天妈妈或爸爸接送我上下学,我就老老实实斜坐在后座上,看街景的幻灯片向右掠过,要不就是与其他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小孩默默对视,用意念刺探他们晚饭吃什么,作业多不多。间或我也换换坐姿,朝反方向跨坐,舒适性不是问题,但盯着后面的骑车人看,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无论清晨或傍晚,那些大人总是眼皮子耷拉着,面颊灰垂,分不出好看赖看不说,我自己心里也觉得,他们虽然不用写作业,但疲乏的样子似乎不是装的。至于那些一边嚼口香糖一边单手扶车把的中学生,我就更不敢看了。我那个年纪的小孩最敬畏的就是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孩,要是被他们给一句“小崽子瞅什么瞅”,那种屈辱可比被老师点名批判要扎得更深。 上初中以后,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深蓝色、26 变速的大众名牌,崭新的一手货。车骑着没毛病——结实、抗造,雨雪天赶去学校也嗖嗖地快,摔过几次也没摔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打眼——成年人才会觉得自行车不打眼是好事,省得挨偷。十几岁的东北小孩,基本的人生理想是出门就要走面儿,要童叟无欺地闪亮;车子可以不好骑,但不能不好看,至少不能太不好看。至于说一辆招人馋的车子下场如何——我在受到高等教育前多少有点宿命论,觉着人不能总琢磨跟命运对着干。 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 那时候,学生们对一辆相貌平平的自行车下手的地方共有两处:车把和车轮。用来装饰车把的是包装礼物用的彩色细条缎带,拴成薄厚适中的两束,系在左右车把上,怎么配色都随便,当然越嘚瑟越好,比如荧光绿配水红,反正目的就是让缎带随风飞扬,制造礼宾队开路的迷幻气概;车轮装饰则略微费劲一点——要买专用的彩色塑料球,一袋造价得十块二十块,球上有缝,可以完美地卡在钢轮上。流行的做法是在每根轮条上装三五个,车轮转起来,色彩搅成一片糊,远看是微妙的彩云,停下来看就星星落落,像彩色的鸟屎。当然了,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