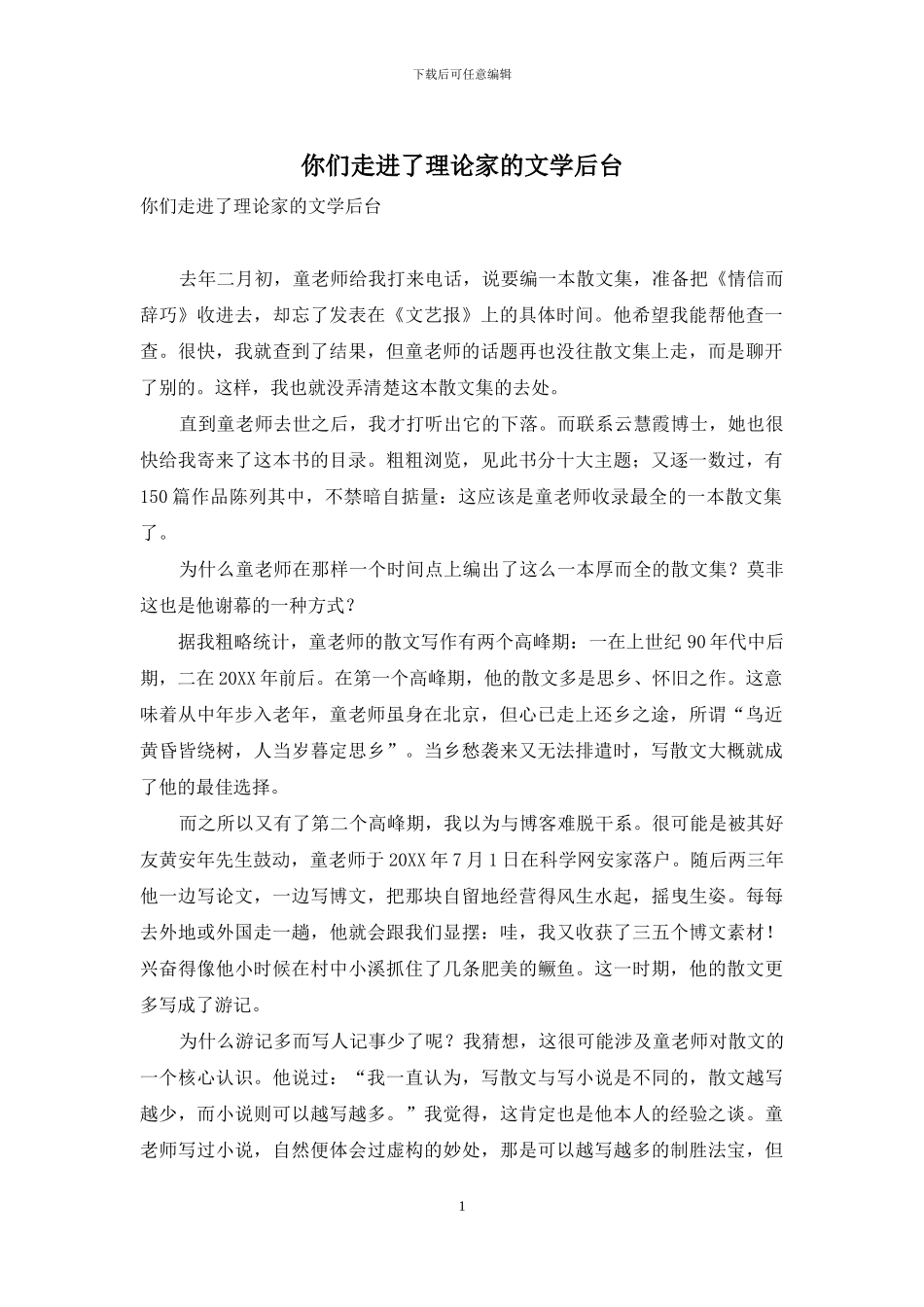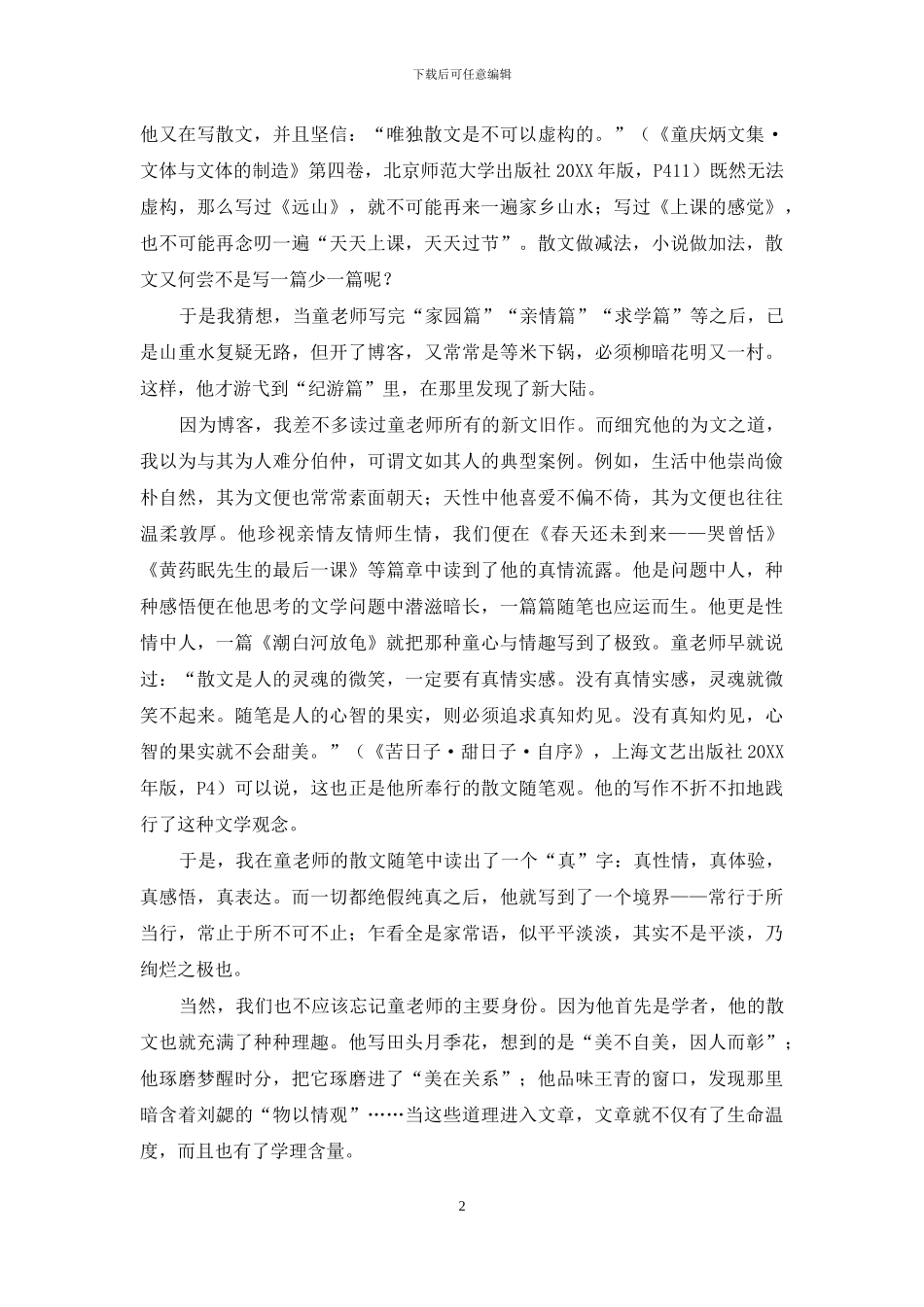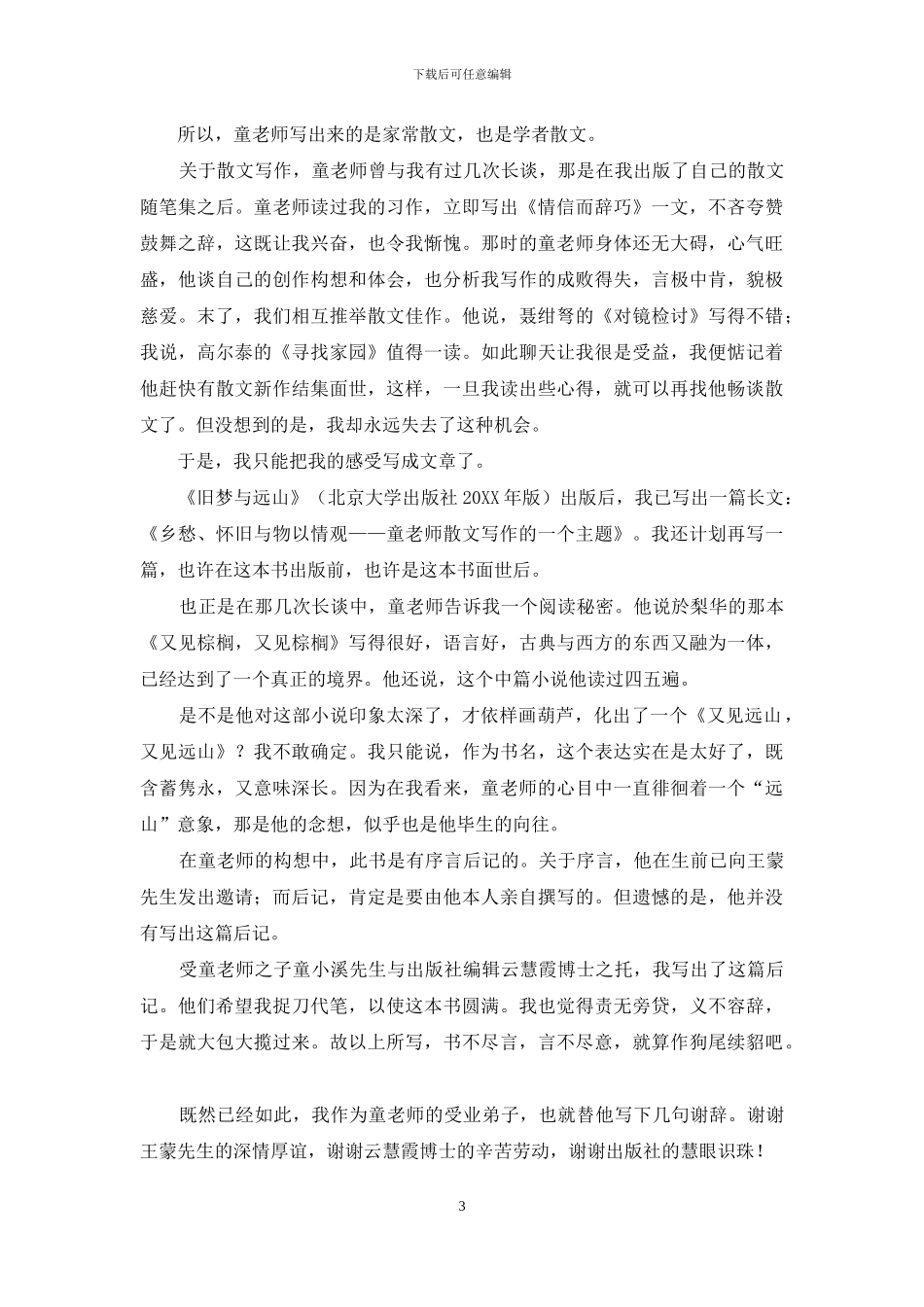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你们走进了理论家的文学后台你们走进了理论家的文学后台 去年二月初,童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要编一本散文集,准备把《情信而辞巧》收进去,却忘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具体时间。他希望我能帮他查一查。很快,我就查到了结果,但童老师的话题再也没往散文集上走,而是聊开了别的。这样,我也就没弄清楚这本散文集的去处。 直到童老师去世之后,我才打听出它的下落。而联系云慧霞博士,她也很快给我寄来了这本书的目录。粗粗浏览,见此书分十大主题;又逐一数过,有150 篇作品陈列其中,不禁暗自掂量:这应该是童老师收录最全的一本散文集了。 为什么童老师在那样一个时间点上编出了这么一本厚而全的散文集?莫非这也是他谢幕的一种方式? 据我粗略统计,童老师的散文写作有两个高峰期:一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二在 20XX 年前后。在第一个高峰期,他的散文多是思乡、怀旧之作。这意味着从中年步入老年,童老师虽身在北京,但心已走上还乡之途,所谓“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当乡愁袭来又无法排遣时,写散文大概就成了他的最佳选择。 而之所以又有了第二个高峰期,我以为与博客难脱干系。很可能是被其好友黄安年先生鼓动,童老师于 20XX 年 7 月 1 日在科学网安家落户。随后两三年他一边写论文,一边写博文,把那块自留地经营得风生水起,摇曳生姿。每每去外地或外国走一趟,他就会跟我们显摆:哇,我又收获了三五个博文素材!兴奋得像他小时候在村中小溪抓住了几条肥美的鳜鱼。这一时期,他的散文更多写成了游记。 为什么游记多而写人记事少了呢?我猜想,这很可能涉及童老师对散文的一个核心认识。他说过:“我一直认为,写散文与写小说是不同的,散文越写越少,而小说则可以越写越多。”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他本人的经验之谈。童老师写过小说,自然便体会过虚构的妙处,那是可以越写越多的制胜法宝,但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他又在写散文,并且坚信:“唯独散文是不可以虚构的。”(《童庆炳文集·文体与文体的制造》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XX 年版,P411)既然无法虚构,那么写过《远山》,就不可能再来一遍家乡山水;写过《上课的感觉》,也不可能再念叨一遍“天天上课,天天过节”。散文做减法,小说做加法,散文又何尝不是写一篇少一篇呢? 于是我猜想,当童老师写完“家园篇”“亲情篇”“求学篇”等之后,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但开了博客,又常常是等米下锅,必须柳暗花明又一村。...